论玻璃幕墙的倒掉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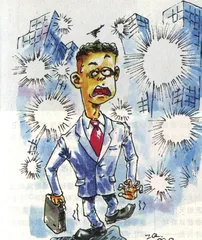
如果选举十大恶俗用语,我一定会推荐“亮丽”。每一次读到这个词,我就想到玻璃幕墙,每一次见到玻璃幕墙,我就想到这个词。
玻璃幕墙在中国的盛行,尤如“亮丽”之成为流行语。自北京长城饭店作为中国第一幢高层玻璃幕墙建筑在1985年问世后,大家都忙着往墙上镶嵌玻璃。据报道,1995年,全国共建成玻璃幕墙面积30万平方米,到1996年升至90万平方米,1997年更激增到170万平方米。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开表达他们对玻璃幕墙的厌恶,因为反射系数可达80%,且超出涂料、瓷砖墙面的反射系数10倍以上的大面积玻璃幕墙,在阳光下所形成的强烈聚光及反光,不仅导致交通事故频仍,而且有损人的视力,破坏造血机能,并导致神经传导中枢的紊乱。
除了对“亮丽”这个词有一种生理性厌恶之外,对于玻璃幕墙本身,我个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意见。我甚至怀疑,赞美和诅咒玻璃幕墙的,很可能是同一伙人。按照当初的共识,玻璃幕墙是进入现代化发达国家的标志;现在变成反对派,理由同样是基于“玻璃幕墙在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已被视为现代文明的隐患,早就以建筑法规明令禁止。对于这种国外已不主张使用的东西,我国更应慎重取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相比之下,报纸上对玻璃幕墙的描述则来得比较由衷:“占地面积11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群楼拔地而起,巨大的玻璃幕墙上映着漫天霞光,暮色初现的长安街车流如梭,华灯齐放。”
都市病比比皆是,玻璃幕墙只是其中之一。对于此事的忧虑,更像是为“我们终于也有了今天”而窃喜。说到忧虑,我最近倒是真的忧了一回——准确地说,应该是为玻璃幕墙感到难过。今年9月16日,热带气旋“约克”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正面袭击香港,面向维多利亚港的一整排的摩天大厦,有400余幅玻璃幕墙(每幅价格为1万港元)被风暴撕裂,光滑如镜的外墙,刹那时出现了一个个面积为四乘六英尺的丑陋的窟窿。满街的玻璃碎片,闪烁、刺眼而且——亮丽。
我本来想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多的掉下来的玻璃幕墙。后来却认为,不如改为“最多的玻璃”更为直接而简洁,更为贴近玻璃幕墙设计者的美学思想。第二天早上起来,电视画面上有一个垃圾桶满街翻滚,播音员说:“大风把垃圾桶吹成了垃圾。”在垃圾桶被台风吹成垃圾的同时,玻璃幕墙也被吹成了玻璃。当这些“亮丽”的神话遭到不可抗力的解构,从天上摔到地上,我们才得以对玻璃本身的意义来做一番审视。
摔下来之前,它的名字是玻璃幕墙;倒掉之后,不再是“幕”和“墙”,无非就是玻璃,一堆不规则的镜面。关于镜子,我手上就有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不失“棒喝性”的无聊程式,这个供Palm Pilot使用的程序声称:它可以将你的Pilot变成一面镜子。启动程序,果然在“镜”中看到自己惊讶的表情。再一想,原来这个神奇的程序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关机指令。因为一关机,Pilot的玻璃罩面也就还原了本来的面目,一面镜子。
我怀疑,自玻璃幕墙在美国出现以来围绕其所发生的绝大部分争执不会比上述Pilot程式更有意义。无论是简洁、明快、繁荣、现代,还是暴戾、冷漠、非人、疏离,从平放的火柴盒到直立而且被贴上玻璃的火柴盒,从包豪斯到我们的房子,从玻璃到幕墙,从幕墙到玻璃,可能都是扯淡。细节的过分营造无疑会影响到实用性,但是对“去掉一切多余东西”的偏执,仅仅就玻璃而言,难道不也造出了另一种多余吗?古典主义可以质问:罗密欧怎么能爬上这些玻璃幕墙?现代主义不妨反诘:他爬到那上面去干什么?收快递吗?建筑的道理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只有一条,折衷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
400块玻璃幕墙倒掉的两天后,“玻璃大师”贝聿铭恰好路经香港(继玻璃柱形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之后,他设计的西单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也恰好在前两天完成)。大师说,要保证玻璃幕墙的安全牢靠,办法是“选择厚度十足的玻璃”。现代主义的全部建筑语言,以这一句最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