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96)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劳乐 赵小帅 傅浩 杜比)
老鼠的儿子
文/图 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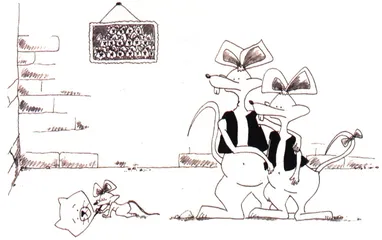
王府井百货大楼改建后闹出了不少新闻,其中之一就是糖果组新设了一个“张秉贵柜台”,站柜台的正是张秉贵的儿子。我原来只知道时传祥的儿子也干环卫,从不知道张秉贵的儿子原来是在百货大楼卖玩具的,这次改建后才被调到糖果组。了解到这点后我有点遗憾,因为我酷爱逛玩具柜台,不喜欢买糖;我宁肯去和张秉贵的儿子聊聊遥控车也懒得去看他表演“一抓准”。
当然,“子承父业”从来不是新鲜事。这也许是因为人们相信那句老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我还知道一个更古老的故事。战国时期有个善于游泳的人,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孩子刚满月时就把婴孩扔进了水里。别人问她为什么,她的回答是:“他的父亲善于游泳,他也应该从小就会。”
艺术领域的世家更多。J.S.巴赫算得上这方面的楷模,他活了65岁,生了18个儿子,活了11个,个个是音乐家。按照当时的编制,巴赫家组成一个小型管弦乐队绰绰有余。
不过,巴赫的儿子中没有成就赶上他的。相比之下,老莫扎特倒比较幸运,他的儿子是公认的天才。但是,W.A.莫扎特自己是神童,对自己儿子的音乐教育倒并不重视。他在发现大儿子缺乏音乐才能后就彻底放弃了努力,小儿子诞生不久他就死了。倒是他在音乐界的朋友费尽心思在他死后把他的小儿子培养成了一个还说得过去的音乐家。莫扎特如果自己在世决不会这么费事,这从他给小儿子取名的态度中就能看出来,当时他是随便借用了自己学生的名字凑合的。
其实,像莫扎特这样的人也许根本不该有子嗣。后来事情的发展似乎也证明了这点,莫扎特的两个儿子一个虽然结了婚,但没有留下孩子,另一个终身未娶。莫扎特家族的这一支就此绝了。
事实上,我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大多数人的职业和他们的父亲没有什么关系,我也很少根据眼前的人推断他父亲的情况。这其中少数例外之一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同事有一个4岁的小儿子,他在不大的时候就有一句名言:“我可厉害了!”我正是由此得出结论:他的爸爸肯定也“可厉害了”。
革命的火花
赵小帅
多年前,我在上大学,校园外有一家小餐馆,我们常去那儿吃炒饼喝啤酒,餐馆老板人称“三哥”,经常跟我们一起聊天。
有一回,“三哥”给我们讲故事,说他以前的一哥们儿,在一家饭店的美发厅里工作,遇到一个美国老太太,美国老太太到中国来是要寻找个“东方爱人”,据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老太太看中了“理发师”,把他带到美国。没过几年,老太太死了,理发师继承了大笔遗产回到北京,至于大笔遗产是多少钱,“三哥”没有讲清楚,就是说有朋友向“理发师”借钱,他一出手就给30万,弄得好多人都找他借钱。
当年我听这故事就当是天方夜谭,因为“三哥”说话水分极大。后来我得知,这故事虽有不同版本,但基本事实并没有太多差错,那位老板酷爱劳斯莱斯,他的名气在今日的北京城里颇为响亮。
当年我是个学生,穷得丁当响,毫无根据地相信自己今后也能赚钱,要是运气好,没准儿能发财。
那之后我听到、看到更多的发财的故事,心里着急得慌,不知道哪天自己能撞上一件好事,慢慢地我知道这机会颇为渺茫,自己只能打工,每个月领工资,年底拿一份奖金,如此而已。
今年夏天,我到北京一座大写字楼找一位在那儿上班的朋友,他给我讲述那座写字楼的历史,说这楼是两个哥们儿的,那两位不知从哪儿扎来大钱,弄起这座写字楼,楼顶三层是老板自己住的,楼里还有私人网球所,是老板自己玩的。
我听了就说:“我去找个镐把你们这楼给刨了吧?”这话当然是句玩笑话,但其中闪烁着革命的火花。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深得民心,谁不希望自己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呢?但要改动一个字说:“让一部分人暴富起来”,这就会让无数人撮火,凭什么你能一夜暴富呢?
富贫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事实。可尊重个人财产的观念在我思想中闪烁出革命火花时真是淡薄。早几年,我时常听到有人议论——从监狱出来的都发财了,语气中颇为愤愤不平,似乎还希望他们能再次成为专政对象。我觉得这种议论真是毫无见识,可反躬自省,革命的火花也不断在头脑中闪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贫富、等贵贱”、“打土豪,分田地”、“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想起这些就会想拿起镐去刨人家的大厦。
(本栏编辑:苗炜)
漂亮的姑娘在外头
傅浩
有一天,查理五世感到做罗马皇帝没意思透了,便宣布退位。不过,在此后漫长的隐居生活中,侍候他的仆人始终保持在150名左右,制定他的食谱一直是朝廷的一项政治任务。他以女人和国家大事为日常消遣。为了得到宗教上的满足,他甚至与修道士一起鞭打自己。但是,查理仍不快乐。他在一次葬礼中发现,这倒可以给他带来不少乐趣,随后便再也不肯放过此等良机。烦恼的是,可能参加的葬礼在数量上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况且,气势也不够恢宏。查理于是为其死去多年的妻子重新治丧一次。这只是牛刀小试。1558年,他假设自己死了,替自己举办了一场葬礼。身穿丧服夹杂在哀悼的队伍中,查理和其他人一道抛泪、痛不欲生,喃喃道:“您老人家走了,我可怎么活呀!”
盖棺论定是查理的快乐,4年前我读到这段历史时,觉得他真够明智的。因为就在参加对自己的悼念活动后两个月,查理真的去世了。此后每当我感到郁闷,便有一种想参加葬礼的冲动。我已老大不小了,身边不时有一些亲朋——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位闭上眼睛前对我说:“务必化悲痛为力量!”——谢世,情况令人丧气,我从未找到过查理的感觉。
我每年总有数次去公墓祭奠,墓地和碑铭的风格,叫人有误入投票选举场所之感。它使我不知所措。这是不对的,他们不应该如此对待我这样一个希望找点快乐的人。玛丽莲·梦露的墓碑上刻着一行字:“37,22,35,R.I.P.”,这是多么令人向往啊,这组数字会使多少女性为之嫉妒。如果让我选择,我将在余光中的诗后加上一句,作为自己的墓志铭:“现在,我在里头,所有漂亮的姑娘在外头。”希望姑娘们喜欢。
公墓作为有限的几种自由公共场所之一,应该加强它的娱乐性。这是允许的,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关于它的出版审查制度。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它办成一个“语言的狂欢地”呢?从前,罗马尼亚有一木匠天生爱为人打制墓碑,他为一名屠夫设计的好像是:“持刀屠猪爱吃肉,肉吃太多命不长。”这类碑文平易近人,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这样的木匠值得尊敬。
钱钟书在某处也津津乐道曾剃头自传墓铭语“不信天,信运气”,说明很可能这是一个普遍的要求。说到钱钟书,就是这么一个有趣的老头,身后之所也同样令人大失所望。他的坟墓本来大可以做成巨型鸡蛋状,上书“内有母鸡”。
聪明老鼠
杜比
《自然》杂志报道,有位科学家通过基因技术弄出来一批聪明的老鼠,这消息让人振奋。因为它预示人类有可能因此越来越聪明。
不过,避孕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那时候的渔民就知道用鱼的肠衣干什么使,这在当时是否预示人口数量会得到控制呢?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人口增长的速度并没有随避孕套的完善而减少。性病吗?也不见得越来越轻。
针对“聪明老鼠”,有人发表高见,说这种技术可能会让有钱人更聪明,让穷人更傻,因为能最先享用新技术的都是有钱人。这种说法让人心慌。两千年前,曹刿论战中说肉食者鄙,吃肉的人有钱的人缺乏智慧,或者说统治阶级缺乏智慧,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实际情况是一两个聪明的穷人骗倒了一部分愚蠢的富人。像卢梭,装疯卖傻成为穷文人混吃混喝的典范,这样的人说肉食者鄙,而大多数穷人相信自己受穷就是因为不够聪明,否则也不会节衣缩食供孩子上学
“聪明老鼠”的实际效用在哪儿呢?专家说,它有助于解决老年痴呆症问题,也就是说,你慢慢变傻了,这可能会得到治疗,你原来就傻,出生前就傻,未必治得好至于能不能把这项技术用于提高婴儿的聪明程度,尚需讨论。
苏东坡说“人生糊涂识字始”,看来,这个聪明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按照常规那样聪明起来。凡是自认为聪明的家伙也未必喜欢给自己怀孕的老婆吃两片药打两针,他应该相信,他的孩子已经够聪明,只有智商不太高的人担心自己的孩子聪明程度不够。
这项技术如果普遍使用,需要这样一个前提:全人类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更聪明。这是非常美好的事。反过来,不好意思的是:全人类都已经变傻了,聪明人越来越少了,所以需要这项技术。
依我个人体会,全人类都变傻了的可能性是有的比如笛卡儿坐标把几何问题与代数问题结合,这是绝对聪明的.而解析几何非常容易理解,上到中学就明白,可到了爱因斯坦,他无疑很聪明,但上了大学也未必整明白什么叫相对论,从这个角度看,全人类变傻了
当然,你可以说爱因斯坦相对论是人类成就的一部分,所以人类是更聪明我同意这说法。问题是,如今的科学越来越被少数人控制,一个人弄出一批耗子,全人类就坐不住,所有的人都要信科学,不管他懂不懂,你要是不信科学,还有人逼着你信,你要是不给你孩子预备两个“聪明大力丸”,自己还要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