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贱伤农,是耶非耶
作者:邢海洋(文 / 邢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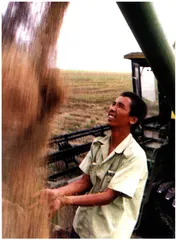
玉米而不是小麦
有资料显示,美国实行休耕的农地面积达2428万公顷,巴西中部有6070万公顷的可耕地尚未得到任何利用。荷兰的一个课题小组的研究认为,理论上全球谷物的最高产量是498.3亿吨,而目前实际产量只有19亿多吨。之所以产生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主要因为中国的进出口状况不稳定,在这粮食多一点就过剩,少一点就饥荒的市场上,不稳定就意味着恐慌。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大多数年份,美国的小麦出口占其产量的一半以上,1988年曾经高达78.09%。玉米出口在20%以上,1988年也曾达到41.1%。这也就构成了美国一方面惧怕富起来的中国吃掉全世界的粮食,另一方面在WTO农产品谈判中立场强硬的基础。而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中粮食价格火箭式增长,到90年代小麦和玉米的价格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短短几年就成为国际上的进口大户。这个时刻,也的确应该考虑是否继续进口下去。
1996年12月中国集市上小麦的价格为每公斤1.65元,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上的价格合人民币1.2元,中国小麦比美国贵37.6%;同期,中国玉米价格每公斤1.45元,比美国高67%。这还远没有达到光辉的顶点,到1998年,美国的玉米比我们这里便宜一半。
比较小麦和玉米的价格的结构性变动就会发现,在国内,玉米价格的上升远大于小麦。改革开放至1996年,玉米价格上涨了5.44倍,而同期小麦价格只上涨了4.77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玉米涨71.7%,小麦涨57.6%,玉米的价格比小麦多上升了25%。而且,这个差距有不断扩大之势。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结构变动,主要原因是玉米是饲料粮,随着饮食结构的变化,消费者对肉类需求的增长远远快于口粮。在包括大米在内的中国三大粮食品种中,玉米的产量与价格的增长幅度都是最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消费者,或者说饲料加工者只要一半的价格就可以买到玉米,那里的牲畜的饲养成本只及我们的一半,消费者得到肉类的价格也就有可能便宜许多。
大谈农民的利益的同时,我们忽视的就是其他人的利益,中国人本身收入少,如果再用比世界上其他角落的人群多花一倍的费用吃饭,恩格尔系数恐怕再难降下来。并且,只有贫困的人口才最在意口粮问题,如果粮价高,伤害的恰恰是这部分人的利益。
靠粮吃饭与农民的贫困问题
中国农民是靠粮吃饭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不是靠粮吃饭的。农民的口粮基本上自给,不管经济上是否合算,农户普遍依靠自己种植而非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口粮。这也就决定了农产品在当地的市场化水平低。如果按农民在国民人口中的比例计算,每年的粮食总产量中至少有3/4的产量是在农户的小院里自我循环的,事实上也基本如此,每年只有1/3的粮食在市场上出售。这个时候,粮价的升跌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并不像想象的严重。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理解近年来农民所遭遇到的现实困境。90年代以来,粮食几乎是涨价最快的生活必需品,粮价高居不下;与此同时,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高粮价并未使农民得到高收入。据报道,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至少15年的消费断层。改革20年,农产品价格大幅提升的同时,农民却依然贫困。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近日透露,1998年,在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33.1%的贡献率中,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的消费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仅15.8%,比1980年24.8%下降了9个百分点。
当城镇居民消费向空调器、摄像机、VCD机、电话、电脑甚至汽车等高档、新一代耐用消费品发展的时候,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性为主的消费水平上。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仍然居高不下,1985年为57.7%,1997年下降为55.1%,12年只下降了2.6个百分点,仅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初期的水平。
农民的贫困有目共睹,这种贫困显然不能全部归咎于粮食价格。有资料显示,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低于美国,粮食生产的收益率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美国的粮食收益率在90年代中基本是负数,要依靠政府的补贴才能弥补亏损,而中国粮食收益率在1991年为89%,1994年进一步上升至108%,如此高的收益水平引起了大规模的通货膨胀。比较两个国家的粮食生产成本的长期上升趋势,就会感到问题的严重。长期以来,美国的粮食生产成本是下降的,中国的却是上升的。上升的成本加上令人咋舌的收益率构成了上去就下不来的价格。在政府确定政策时,农民的贫困与居高不下的农产品价格就成为一对互为表里的因素,阻碍农业的开放。
产业化与农民的出路
粮食生产成本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土地的细碎化分散经营。在我国农村,几乎所有的土地采用的都是平均分配的原则,而且是绝对平均,好、中、坏土地平均分派。据农业专家郭书田计算,我国平均每个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虽只有8.35亩,但分布在9.7个地块上,平均下来每个地块还不到1亩。
土地细碎化对收成的影响是明显的,计算机的模拟显示,土地整合后,玉米产量能够提高17%,小麦和薯类可提高18%。水稻的作用不很明显,只有4%。恰恰是美国占绝对优势的作物最需要规模经营,美国的农民按照种植的规律办事,获得了世界农产品的霸主地位。美国90%的农产品是由年销售额5万美元的农场提供的,占有耕地量37%的小农场的产值仅占10%,众多小农场处于亏损状态下,出路就是被兼并。1935年到1993年,美国农场的数目从681万个减少到206万个,平均规模从1950年的214英亩上升到436英亩。美国政府也一直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限制土地的兼并,但这也没有能阻止经济规律的作用。农场的集约化有着全球的背景,法国农场平均土地规模从1955年的14.75公顷提高到1980年的25.4公顷,德国农场从1949年的7公顷提高到1987年的17.39公顷。
均田制当然也给农民带来了好处,至少每家每户的口粮有了保障。但在大生产的时代,它对农民的束缚也是同样明显的,农民既需要在农业之外寻找收入来源,又得经营土地,结果是产量只有专业化种植的70%到80%。而在其他领域,也竞争不过专业化的生产,腹背受敌。
社会的财富是张不断长大的大饼,当一个新的产业出现的时候,它将由小变大,带着社会财富一起膨胀,人类财富的绝对量增加了,但积聚在传统产业上的财富不会变大。经济的发展规律,就是产业不断升级,人口从过时行业不断转移到新兴行业的过程,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目前,美国的农业人口只有2%,生产的粮食除了供养全美国人口,还大量出口。如果说美国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日本、法国等人口密集的国家也同样选择了请农民走出土地的政策。惟有这样,才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枯萎下去,才是真的为他们着想。
退一步,继续维持农产品的高价政策,则农民得到的价格信号仍旧是打多少粮食可以卖多少粮食,结果是大量过剩,为维护农民的积极性,政府耗尽了宝贵的财政资金。专事中美两国粮价形成机制和波动机制研究的隆国强做了一个对比: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人口不到2%的农民实行补贴财政尚不堪重负,1996年的农业法案中停止了实施价格补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用30%的城镇人口去支持70%的农民的收入,无异于把全体国民拉下水。
授人以金,不若授人以业,这是连古人都懂的道理。
为弱势人群代言?
中美WTO谈判,美方的要求集中于它占绝对优势的小麦、玉米、大米、棉花、大麦和黄豆几类商品。小麦、玉米、大米的配额总和先从250万吨上升到1400万吨,增加6倍;到2005年再增为2200万吨。大麦则取消配额,减低关税。
一经签约后,中国的粮食市场,仅仅对美国一国,就要少去1200万吨,再加上大麦开放进口对主粮、牲畜饲料及制酒作物的市场影响非常巨大。比较中美粮食生产的技术和成本,没有任何人会怀疑开放进口就等于让出市场。据一般的估计,国内粮食市场缩小,将挤出2000万农民。
显然,与农民收入减少相比,大多数学者关心的是农民的出路。2000万剩余劳动力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不仅加重了失业问题和城市工人就业压力,而且,农民与城镇人口,农民与地方政府组织的矛盾将加速恶化。
本质上,这却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而不是把农民当成自己人,当成自己的兄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侯若石认为,不应忽略体制和结构转换所焕发出的巨大能量。“入关”对我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就在于生存问题,而我国生存的最基本现实是地少人多。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改革开放20年,我国的增长模式与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增长主要不是靠投入,而是靠体制转轨,资源再配置,资源从低效益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转化,还有国有企业的资源向其他部门的转移,这种转移占经济增长的95%。加入WTO将再次带来结构的大调整,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村的发展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
落后的生产方式必将结束,也必须结束。再也不是只应满足于吃饭的时候了。现在需要新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