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忙碌的“扩招”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任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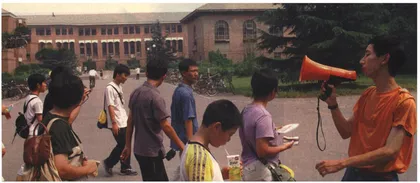
6月的惊喜:触动了基本供需矛盾
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并不起眼,它是紧挨着二校门的一座酷似仓库的灰色建筑。今年高考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是7月12日,这里的电话却早已成为“热线”。7月13日,当北京某报一则“清华大学今年又扩招300人”的消息意外地刊出时,咨询电话更是汹涌而至
在忙乱的电话铃声中,招生办主任吴振一常需要提高说话的音量:“这条消息表述得不够准确。对,清华的确扩招300余名本科生,但在今年6月初国家要求各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之前,学校已把名额纳入到今年的招生计划中了,6月初之后,清华根据现有的招生规模和教学资源状况又作出了扩招300余名第二学士学位学生的决定,本科生并未再增名额。”清华的扩招原来与高考无关,吴振一的解释迅速冷却了咨询者膨胀的热情。
1999年,全国高等教育招生原定规模近230万人,比1998年扩大招生23万人。吴振一提到的“6月初的扩招要求”之所以激起了340万考生2个月以来持续的兴奋,是因为它使得招生规模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33.1万人,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安排22.7万人。这样,我国普通高教今年秋季的招生规模将从去年的108万扩大到156万人,增幅超过44%。此外研究生再增招3900人,成人高等教育安排扩招10万余人,加上电大普通班和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学历文凭考试的招生安排,今年秋季全国高等教育招生的实际总规模将接近270万,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幅度上的增加,都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常情况下最快、最大的。
闻风而动的各大高校在迅速按照要求确定各自的扩招规模之后,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系列的应变措施。清华大学虽然只扩招第二学位学生,但相应的调整也必不可少。一切的紧张都表明,扩招之举深深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供需矛盾。
扩招比例:多少合适?
“学校现在本科在校生人数稳定在12000左右,在校研究生9000左右,这样清华大学的学生总规模到今年秋季约为20000~21000人。目前已经形成本科生与研究生之比约为1.1∶0.8这种构架”,清华大学教务长,工学博士吴敏生教授指出,按照现有的学生规模,再行扩招在硬件方面将遭遇宿舍资源的限制瓶颈,“目前研究生住宿还未达标准,现在新盖的宿舍楼卡着工期在建。清华的校园面积比较大,可以增建宿舍,北大的校园已经挤满,再建只能去校外。在以校园为中心的周边环境增加一些走读生也可能解决一些学生就读,但由于部分教学、实验环节在晚间进行,而北京交通状况不佳,走读受到一定限制。除此之外,学校也在探讨通过远程传播,在离学校较远地区建分校的形式最大限度地满足目前的教育需求。”
作为一个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的中心,清华大学被誉为“大师之园”,3700余名教师中有37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892位教授和1603位副教授。全校建有49个研究所,163个实验室(包括15个国家实验室);核能、微电子、高速信息网是三大综合性研究基地,还建有CIMS等四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藏书250万册的电子化图书馆提供与国际接轨的信息服务;计算机开放实验室配有500多台与Internet互联的微机;还拥有10多个现代化教学实验基地……“清华”二字决定这一切更成为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
90年代初,清华的招生规模一度基本稳定在2000人左右。1996年起,由于学校进行学制改革,对工科各专业实行“本科—硕士研究生统筹培养”的6年贯通计划。考虑到在校生总规模将有相应减少,学校逐年增加了招生的数量,到1999年,把这一数字提升到了2700人。什么才是对于学校的发展前途而言适度和最优的教育规模,这一直是决策层探讨的中心。
7月14日,教育部紧急要所属院校上报下一年招生计划供参考,清华大学在两天之内向发展规划司递交了一个估计数。“明年的招生规模肯定比今年2700人要大,具体数字现在难以确定,要从资源的配比上去测算。”吴敏生同时指出,规模扩大后还必须对学科结构作一定调整。
实际上,教育生产力的核心因素最终是人,软件资源尤其是师资力量的制约才是对高校构成更深层次的束缚的因素。从全国的情况看,到1998年12月,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的平均规模已由1990年的1919人增加到1997年的3051人,其中本科院校的平均规模达到4800多人,而师生比却由1990年的1∶6.3提高到1997年的1∶7.9。
“学校的硬件资源,尤其是宿舍条件的确已经构成一个制约因素,但我注意到清华大学的师生比约为1∶5,与全国的平均规模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这是否说明清华大学还有相当的扩招余地?”记者提出从数字上发现的疑问。
“我们学校的师生比实际上要高得多。清华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教师编制中全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大约占到一半数量,另外有大批教师既搞科研又搞教学,折算下来,全部的教学力量大约在1500人左右,相应的师生比大约是1∶15。”
“这又反而过高了,就我所知,同样是研究型大学,MIT的师生比约为1∶10。”
“那可能是算法不同,很大程度上要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规模比。研究生教育的师生比一般为1∶5、1∶6左右,国外部分高校研究生规模比本科大,总师生比必然降下来,但他们即使到这个规模,本科生培养也多数以上大课的形式。清华要是把本科生研究生规模都算上,我们感觉总体师生比在1∶12到1∶15左右都还算比较合适。”
9月的困惑:投入产出失衡
值得注意,1999年的扩招,教育部直属的44个重点院校的增量不大,有的院校由于办学条件的限制,基本上没有再扩招。恰恰相反的是,地方院校、部委院校和一些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扩招的积极性却普遍较高。对此,吴敏生推测是因为这些学校和专业管理上的自由度相对较大,扩招带来的各种收费在总经费中的增加较为显著。
事实上,高校的收费近年来一直是一个有限制条件的变量。8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校长期实行“统一招生,免费入学,统一分配”的原则。1989年8月,国家物价局、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规定从当年开始,对新入学的本、专科学生实行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制度。4年之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在试点学校实行一个收费标准,不再划分公费生和自费生。当年全国大学在校生所缴学杂费数额约占实际培养费的5%(韩国为13%),自费生所缴费用约占实际培养费的30%。1994年,“并轨”试点的国家教委直属院校每生收费标准为每学年1000至1500元(含学杂费和住宿费)。1996年12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联合颁发了《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原则规定,在现阶段,高等学校每学年收取学生的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
“从拨款机制上讲,国家给每个本科生每年下拨4000元,硕士生7000元,博士生9000元,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教学运行费。如果计入国家对基础建设的投入,比如图书馆、教室、宿舍等其他各种费用,每个本科生的年均教育成本大致估算为12000元。”吴敏生进一步解释,由于作为统计根据的分项不同,各地各部门对此的算法也相应会有差别。
“以本科生为例,清华大学98级的学费2500元加500元宿费,再加上国家拨发的4000元人头费,这与12000元的成本相比还有约5000元缺口,国家的其他拨款能补偿吗?
“补偿不了。教育部前年拨给清华的资金约为1.06亿,实际上这些钱只能满足教师工资册上80%的工资开支。实际上的待遇当然不只这一点,学校还会通过各种合作渠道筹集一部分钱,以内部调剂的方式提高教师待遇。这部分加起来相对国家的拨款比例几乎达到1∶1。这仅仅是教学运行费,不包括盖楼等其他开支。”
如果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那么一个有效的运行机制必然形成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高素质人才作为这种产业的目标产品,那么在教育的成本上必然要有所体现。对于这样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而言,规模的扩张决不仅仅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简单层面上的数量扩张。
“学校老师现在的人均薪酬达到什么水平?”
“准确的账面数字要请教财务,但从工资条可以看到,教授1000多元,副教授800多元,讲师600多元。今后3年,国家对清华、北大,包括南方几所列入国家和政府重点支持的学校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本投入。对清华的首批经费已经到位,学校现在正在做规划,争取在下半年的某一个时候兑现。”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能否透露一点?”
“现在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因为大家都在做。我们主要是通过设置岗位的方式,作为一种津贴支持一些重点岗位,原来的工资基础都还在。你不用说跟国外比,就是香港也要高得多。香港大学一个副教授月薪可达六七万港币,位置再高一点10来万港币,我们现在不可能跟那些标准取齐。”
每增招一个本科生,就目前而言,清华大学只能得到国家拨给的每年4000元“人头费”,再收取为数不多的学费。如果原本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增长无法跟上不断膨胀的教育需求的增长,中国的教育又将面临什么?“教育产业化”在清华园中早已作为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流传着,然而与产业化密不可分的市场机制却还与之保持着距离。“教育投资的机制必须多元化,对此,也许在体制上稍微作一点变更,在政策上稍微增加一点自由度,我们讲了十几年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一个大学的校长会从总体上审视自己的品牌,决不会把它当作简单的商品”,吴敏生说。
9月将至,1999级的新生将要走进清华园。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自己的学费比上届学生多出了500元。而实质上,等他们走出校门,各自将要开始成为怎样优秀的人物,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周期才见分晓。 升学考试大学扩招清华研究生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