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抱你吗?妈妈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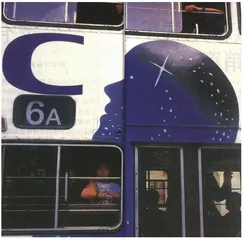
“母教”运动的推动者?
34岁的王东华致力于把自己当作中国“母教”运动的推动者,但他在北京推广活动的第一站便遭到了挫折。与会者的兴趣集中在对他所倡导的观点——“女性最大的成才是做个好母亲”的尖锐批判,以及偶尔触发的另一个话题上——卖淫女被收容后的改造问题。对后者的热情使整个会议的大半时间都在跑题。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新经济周刊》的主编刘欣事后说:“王东华的观点最可能不被两类人认同,一是学者,二是知识女性,而我们的研讨会恰恰由这两类人组成。”
发生在1999年7月14日民政部院内“母教问题”研讨会上的冷落与尴尬,让以为发现了母亲问题便找到了中华民族振兴之道的王东华有点始料未及,他眉头紧蹙一言不发地记录下不同的声音。这个曾于6年前在深圳首次文稿竞拍中以《新大学人》率先成交的人物,一直致力于人才学的研究,他从“天才是如何造就的”问题进入早期教育领域,发现所有伟大人物的成长都与他们父母的培养方式密切相关,于是,1994年王东华辞去公职,埋首女性与母性关系的研究,并于今年7月向社会推出他的厚达千页的论著——《发现母亲》。
在由学者和知识女性构成的研讨会上,王东华的“发现”被视为“男性中心论”的旧态故萌,学者们明确表示,“母亲的伟大毋庸置疑,但把个人成才的核心责任归结于母亲有失偏颇”,他们尤其不能接受“伪劣产品的本质在于伪劣母亲”之说。作家韩静霆说:“伪劣产品的制作者、影响者未必是母亲。环境是一个强大的改造人、塑造人的机器,母亲在其中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并非极致,否则这简直就是‘女性祸水论’。”北京师范大学年轻的教育学家郑新蓉更是情绪激动,她提醒道:“我们的社会真正缺乏的是,没有人把女人当作人来谈,而只是把她们放在女性、母性的角色上横加要求!”
王东华对以上声音同样不能认可,“他们曲解了我的意思。”他在奔忙于上海、沈阳各大城市推销“发现”的间隙,回答了记者就他的论著是否有老调重谈之嫌的质疑:“这是我的原创性观点,不是在出卖女性,而是非常彻底地尊重女性,我认为女性真正的平等,是对她所从事的家庭劳动、特别是生育劳动的价值承认。社会的发展把家庭的本质暴露出来,它可以代替家庭外在的简单职能——吃喝穿衣,但育儿不可替代,这是家庭的核心职能,是很人性的事情,必须要由母亲来完成。”王东华焦虑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扮演着一种“亲生的后娘”的角色,“她们要么放弃自己的母性职责,要么根本不懂如何当母亲”。
身为母亲
据零点调查公司在京沪粤三地所做的调查显示,93.5%的18岁至45岁的受访者有再“充电”的愿望,而已经或正在“充电”的人占到了62.6%。对于女性而言,近1/3的人认为她们是迫于社会压力而必须再学习的。成人希望获得继续教育的迫切心愿,进一步把他们的孩子推向请人代劳的境地。近两年,大批涌现的公立寄宿制小学,与全托幼儿园一样出现爆棚局面。以今年暑期招生为例,北京市中关村小学(寄宿部),招生名额已由原定的600人达到800人左右;而六一幼儿园在原有18个班的基础上再添的7个小班,现已然满员。
舍得为孩子们花钱,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事务调查所提供的资料表明,收入在4000元以上的家庭,为孩子物质需求的支出占到收入的72.2%。仅孩子入学一项的支出,家长们的负担便已不轻松。目前,好一点的寄宿小学,赞助费需一次性交七八万元,普通一些的也在三四万元左右,这其中还不包括学费和寄宿费。但家长们仍觉得,“寄宿制让孩子学会了独立,让家长拥有了做事的时间。”
大多数父母们都将以加倍努力地工作、挣更多的钱、送孩子进更好的学校视作最佳模式。事实上,区别于传统育儿观念的年轻母亲们正用一种更具竞争性的方式,来取得事业和家庭的平衡。中央电视台著名化妆师邵京京在5年前事业处于高峰时有了女儿秋秋的,尽管非常喜爱女儿,家中也请了保姆,她仍在女儿3岁时入了全托,“她必须要接受这种教育,这是她的成长过程,目前的社会决定我不可能在家教育她。孩子刚开始认知社会,她需要的是一个色彩世界里长大,而不是呆在一个鸽子笼一样的地方。幼儿园的集体生活是一种正规教育,让她学会怎样和小朋友相处,将来进入这个处处需要合作的社会人就不会太独,我甚至愿意她吃些苦”。
“孩子跟大人在一块玩不快乐,因为你再怎么理解她,思维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她总在你的意志里走。”邵京京说,入托前,她跟女儿作了一番谈话,“秋秋,小朋友就跟要小朋友一起,跟大人玩多没意思啊。妈妈也不能整天陪着你,妈妈还有自己的事业呢,没有这些,妈妈也不能让你过得这么开心……”事实证明,秋秋从幼儿园回来后,自己洗澡洗脸,有了很强的自我生活能力,“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并不一定好,她越早独立对她越好,我是指能力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女儿又很亲我,因为每次回来我都要抱她,做肌肤亲抚,这说明女儿对母亲的要求也很原始,就是一种依靠。”
“像我们这一代人,都面临着做事和养孩子如何协调的问题。作为现代女性,最重要的是积极生活、不断完善自身,这种生活态度本身给女儿的影响就很重要。我看不起对孩子说‘我这辈子是完了,就全靠你了’的母亲,看似她牺牲自己为家庭奉献了全部,其实这做法过于自私,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负担自己的命运?我也不给孩子钱,因为我已经给了孩子最大的财富,我特别自信我的教育令她长大了只会比我更强。有时工作外出,我会带上女儿,让她一起看这个社会,看我的工作。一问我女儿长大做什么,她张嘴就说当化妆师,她特别以我为自豪。我想这是因为我很独立。你那么成功,那么能干,你给予了孩子所需的一切,你通过她能找到自信。她分享你的成功感,你分享她的稚嫩。要始终记住一点,你活好才能教育好子女。”
母亲们的去向
近期,国家沉重的就业压力触发了部分经济学者们的新思路。最有代表性的,是以北京视野咨询中心的钟朋荣教授在《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中提出的“男人上岗、女人回家”的建议。钟教授一厢情愿地提出了“家务劳动按值定价”说,即请一个能提供同样家庭服务的高级保姆所需支付的工资水平,乃为妇女承担家务所应获得的货币收入……钟教授与王东华的不谋而合之处似乎在于:与其辛苦地在外挣钱,不如节约成本、专心于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提议在六七月的《中国妇女报》上引起了激烈讨论。响应者多为下岗女工,而社会竞争力强的知识女性对此大为反感,她们认为,现实既没提供让女人回去的可能,女人们也早已回不去了。与一位9月临产的孕妇讨论起此话题时,她说:“顶多半年,我肯定还得回公司做。公司就相当于我们的另一个孩子,我和丈夫一起奋斗,在同一个环境里我才能更好地体会他的心境,这几乎是我们婚姻稳定的基础。”这位准妈妈说她不想因为孩子而失去丈夫,“我曾经在家里呆过两年,那两年里我变得很不自信,整个人都跟社会脱节、视野狭窄,做一个只带孩子的母亲,我很怕有一天我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专家们认为,在独生子女的政策给中国妇女和家庭生育关系造成重大变化的今天,家庭生活中并不需要长达几十年的主妇,“对于女性而言,最重要的是,加强生育保障的社会体系,同时女性自身要改变观念,做好阶段性就业的准备。”但他们也强调说,“年龄过小并不宜送去寄宿,因为孩子最初的社会认知是来自父母的。”近年来美国心理学家们论证,决定一个人情商的不是学校,是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对于那些既望子成龙又望己成龙的家长们来说,深思熟虑、有急有缓的安排自己的发展和孩子们的成长是很重要的。
王东华通过大量调查后发现,幼儿期不在妈妈身边长大的孩子,很难跟别人建立稳固的亲密感和安全感,“缺乏亲密感的人,在感情的表达上是有障碍的,这会影响他一生的幸福。”据新近一项在中学生里题为“最受你尊敬的人是谁?”的调查,日本学生的回答是父亲,其次是母亲;美国学生说是父亲、迈克尔·乔丹、母亲;中国学生的回答令人心寒,他们的母亲被排在了第10位,父亲在第11位。这个信号是否可以让中国的父母们更多地思考,在为孩子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什么才是最本质的东西?
学者赵文洋的育儿思路或许对我们有所启发。她是一位坚持自己带孩子的母亲,“带孩子是个能力问题,我们分工合作,严格按科学育儿的方式调节女儿的饮食、行为习惯,她不生病,特别健康,我们带着非常省心,两个人的事业一点没耽误。”她与众不同的方式是,一星期只有几天让女儿呆在幼儿园里,“过早地强调集体生活,孩子的天性就会被损伤,我们希望她最初的发展更个性一些、更自然。”赵文洋尤其反对整托,“我不想让她体验我曾经有过的感受。从小在整托长大,老觉得自己跟怪物似的,跟父母感觉特生疏,找不到依赖感,别人可以很容易地说出自己的需求,可我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因为没有表达的习惯,到现在这还是我内心某个角落的缺憾。”赵文洋最后告诉记者,等女儿长大一些,再送她去寄宿学校,“因为只有来自社会、家庭各方的影响,一个孩子的成长才是全面的。” 幼儿园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