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机会还是陷阱
作者:王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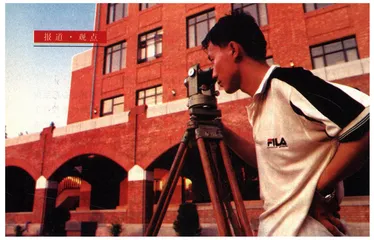
坐落在清华大学红色校区的理学院,由关肇邺设计(娄林伟 摄)

被学生们戏称为“白区”的东门外,建筑馆的设计至今已无人勇于承认(娄林伟 摄)
走向市场,寻找生存的更好方式
近期,让清华人上下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的事情是关于教育投资——别误会,不是教育产业上市,而是国家将在今后三年中以3、6、9的方式,完成对清华一所院校的教育经费投入,这个数字是18亿元。
多少年来,教育的投入都捉襟见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个投入的增长幅度应与国家财政收入、国民经济发展基本持平,起码不应低于3%,而我们只有1%左右——该比率只是印度的1/5。国家在1999年6月的教育大会上声明,到2002年,对教育的投入将以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速度达到4%的目标。20世纪最后一年的巨大决心,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见识。但无论如何,在其承诺兑现之前,18亿元至少给了一流学府一个绝好的希望:安心教研,免受创收之苦。
建筑学院是清华大学的创收大户。1992年至1994年房地产开发的狂热,令建筑师一下成为各人才市场排名前列的热门职业,几年间,急剧涌现的建筑院校在总量上竟达到70多所。人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对清华来说,不啻是天赐良机,事实证明,在各大城市的设计院趋于饱和的今天,清华的毕业生每人背后仍有着七八个单位等着接收。清华的牌子给了更多人游走市场的信心,至今,建筑学院每年创收稳定地保持在800万至1000万元之间。
现实的窘况也注定了他们非此路不走。有些数字可说明问题:1997年,清华对建筑学院教学经费的投入是17.6万元,而这个数字不过比1990年多出0.7万,实际上仅此一项的支出就有66.6万元。个人同样是窘迫的。无论年轻年长,教师的工资都在千元左近徘徊,建筑学院学工部部长邓卫告诉记者:“一个教师如果不参加生产实践,根本连教学都无法维持。搞西方建筑理论的人,就应该到国外去看,不看就是纸上谈兵,充当传声筒,但参观考察费又从哪出?学生也一样,画图需要电脑,就得跟着老师做工程,分一些钱。”
钱来了,另一些东西也来了
“教学、科研、生产”的传统口号在现实面前实现了灵活变通。大量的实习、课题研究以真枪实战的方式上演,仅1997年,建筑学院吸收研究生参与的生产项目就有近80项之多。名正言顺的创收,为建筑学院盖起了一幢耗资800万元的建筑馆,同时也给了个人借创收名义挣几十万身家的机会。
但串演着老师和老板角色的人们,亦辛苦异常。知情者私下告知:“建筑设计是个无法由个人独立承担的行业,所以人员的成本就很大。加之私人没有资格接工程,作为清华的教师,在学校、系里、教研组提取层层管理费之后,一项耗时挺长的工程,个人最后也不过挣其中的20%。想多挣钱怎么办?只能是不论水平高低有活就接。”
没有时间备课,要保证课堂教学,只有一种可能,便是沿用以往的内容。一位89级本科毕业的清华老师说:“我们现在讲规划设计,地段分析的案例用的还是我上学时的,没一点改变。”更令人尴尬的还不仅于此,据94级的一位学生形容,由于老师不会电脑画图,对学生的依赖已有本末倒置之嫌,“最重要的是,你起码要做到他们只是你的一根笔,而不是脑子。”
大量的实践反倒造成了业务能力的滑坡,清华将为此付出代价。据悉,建筑学院45岁以下的教授不仅是清华各系中最少的,在全国各著名建筑院系中,人数也是最少——只有两人。忙碌的老师开不出给研究生的课题,“群体不读书”曾一度是老师们羞于承认的现实……现在,梁思成先生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为清华的传统学术优势已濒临丧失的危险;而能够像吴良镛先生那般提出“广义建筑学”、“人居建筑学”震动世界的学科巨鼎,也难见新人。如果建筑学院的国际声誉,只凭吴先生的老本,也过于危险——吴老先生毕竟年逾80。
学生的状态也不乐观。清华人将他们参与实践的渠道作了几种归纳:一是白色渠道,即正常的教学实践;一是灰色渠道,指导老师领着得意门生干私活;再有一种便是黑色渠道,有活动能力的学生,偷偷接活。为了更快的做活,学生们被分配成一个个细部的零件,在建筑流程中,获得些支离破碎的实践经验。没完没了地画图和没完没了地打电子游戏构成了他们生活的画面。
改变,在悄悄地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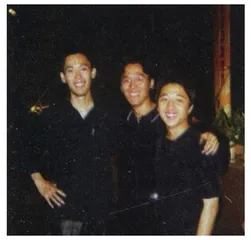
赵亮(中)和他的竞赛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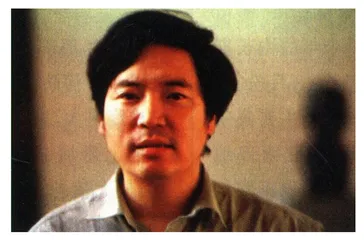
34岁的副院长朱文一(娄林伟 摄)
1999年6月,在第20届国际建筑大会上,清华建筑学院一年级研究生赵亮荣获“国际建筑专业学生设计一等奖”。和赵亮一起坐在清华校园中一处简易的遮阳棚下喝饮料时,他指着头顶上的棚子突然发问,“此处你认为是building还是architecture?大部分人会说这是building,但简单的东西就是building吗?这儿放上几张桌子,人们就可以在此喝茶,前面是个停车场,它们在一起构成了什么?不想明白这个问题,你看什么方面的建筑书?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我相信我的很多老师都弄不明白建筑究竟是什么,可是他们甚至连想都不想。”赵亮说,“在清华建筑学院目前的体系里,我没法学到我想学的东西。”
真正对赵亮产生影响的有两件事。1997年1月开始,赵亮跟随从美国来的台湾建筑师易介中在清华北门外的小平房里做了8个月的活,这段经历让赵亮掌握了一种全新的方法,“清华建筑系过去从来不做模型的。拿二维的设计图想三维的建筑物,多累啊,也不容易对啊。传统的古典建筑画个立面可以知道后面的东西,现代建筑行吗?从那时起,我常常抱着一个巨大的模型跑到系里交设计作业。”此后,清华开始了模型制作的教学要求。
另一件事发生在长春,赵亮为一个大老板做活。那天,他们面对一个大湖,背靠一座青山站着,老板说,“赵亮,你看对面那两个小山包,我要从那儿开一条运河。”赵亮觉得很羞愧,“这话应该是我说的,可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那天我特激动,这才应该是建筑师的气魄,不要整天想着你在食堂里吃的三毛钱的馒头。这个细节改变了我很多,它让我深刻地体会挣钱的美妙过程。”
单纯的学习与教学早已失去了它的现实性,人们无力拒绝商业化。商业的力量,注定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行为方式,你无法了解个体的“独立思想”、“质疑精神”究竟属于谁,但有效地考虑商业与学术的关系,对于清华这类高等学府却至关重要。《注册建筑师概论》是清华的新设课程,从过多强调技术因素的基础教学,转向职业精神的教育,正是清华尊重市场的一个信号。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朱文一谈起清华学生时,说:“我们的学生学习观念很被动,交给的事情可以踏实、严谨地完成,但对事情本身不发问;而西方学生可能在一接触事情时就会有一百多个问号。我们的教学过于强调设计程序,结果学生画图能力强,动手能力和操作性却比较差,而且见识的太少,怎样用材料都不知道。”因此,校方加强其开放式办学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让学生较早地在正式课程中就进入设计院做建筑职业实习。据说,学生很是欢迎。
然而,真正的改革应针对老师自身。学生们戏称,4/5师出同门的清华建筑学院的老师们,是在“用昨天的知识教今天的学生做明天的事”。“老用一锅油炸油饼,那油饼能好吃吗?”反思者诘问道,“如果我是老师,我会知道我的学生的知识比一桶水多,我好歹给他们一缸水吧。”
好在清醒而自省的老师总是不乏其人。拥有注册建筑师资格的吕舟老师,1999年承担的工程分别是关于三峡淹没区和阳县地方的文物保护研究,他告诉记者:“老师可以不去做工程,但他必须向学生证明他是能做的,否则对于教建筑的老师来说,太不可思议。我教外国建筑史,但是排除文化隔阂不说,目前的研究条件,也让我永远不可能在这个领域达到世界一流。我注意到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时,文物保护的适应性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我的研究方向就是以这个为主。”像只做学校场馆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关肇邺一样,有选择地实践,让吕舟在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前,获得了大量的研究课题,他说,“我做工程很有限,因为人进入一种忙碌状态,是没有时间思考的。其实闲暇是种非常奢侈的需求,在金钱和思考面前,我更需要后者。在清华,面对这么优秀的学生,做老师是很有压力的。”
暑假临近之际,教育管理者们正在对教职员工定岗定编,巨额的经费投入,将使老师在一种更从容、更丰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教学、研究。在享受年薪可能高达三四万元的待遇的同时,院方对于老师科研成果的要求,也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老师们做何进退? 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