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上的爵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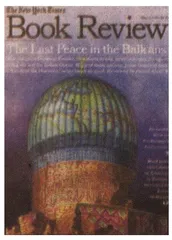
作为人们生活日程的提前准备,6月6日的《纽约时报书评》已然推出“夏日读物”专辑,乃至无暇顾及如今榜上有名的新作,使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书籍,反倒缺乏介绍资料了。
现在我们介绍一部《地平线上的爵爷》(Lords of the Norizons),或许有助于大家了解一下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沿革。
该书的副标题是《奥斯曼帝国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作者杰森·古德文(Jason Goodwin)是一位颇有天赋的英国记者和游记作家。他在这部352页的著作中,一方面写出亲身游历的观感,一方面介绍了当地的简明历史,并对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加以反思,让人们感到那逝去的幽灵时时还在巴尔干半岛上盘旋。
奥斯曼帝国的伟业的起源具有边缘地带的简单和模糊的特色。被唐朝逐出中国版图的西突厥一支,在欧亚大平原上游牧了一个世纪之后,在9世纪时期开始崛起。这个早已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土耳其部族不停地向西扩展:1290年建立奥斯曼帝国,不久便在奥斯曼一世(1258~1326,1299起任苏丹)率领下进据小亚细亚半岛,并于1326年定都丝绸之路西端的布尔萨;1345年,他们跨海来到巴尔干半岛,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1456年占领雅典,并于1459、1462~1466、1468、1481先后将塞尔维亚、波西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纳入帝国版图。16世纪时继续扩展,并在苏莱曼一世(1495?~1566)苏丹时期(1520~1566)达到鼎盛:其领土东至黑海和波斯湾,北抵布达佩斯,西达阿尔及尔,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包括了现今的36个国家。初看起来,这该是一部征服和屈从的可怕故事,但实情并非如此。土耳其人创造了被历史学家称作“合作结构”的统治方略,与同期的西班牙人在新大陆所采取的灭绝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野蛮手段截然不同。
奥斯曼帝国是个多元化的世界:“虽然这是个公认为土耳其人统治的帝国,但其大多数显要和军官以及其横扫三洲的军队,都是巴尔干的奴隶。其礼仪是拜占庭的,举止是波斯的,财富是埃及的,字母是阿拉伯的(按:后于1928年才采用修改过的拉丁字母)……而其最出色的水手都是希腊人,最精明的商人则是亚美尼亚人。”希腊世界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征服,但希腊人善于见风使舵,他们在奥斯曼的秩序下调整着自己。
其实这种迁就是双方的,而且早已开始。早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将君士坦丁堡置于其统治之下并宣布定都于该地之时,就对东正教提供了保护。他自命为凯撒们的继承人,于1454年1月在圣徒教堂为学识渊博的修士乔治·斯考拉里奥斯加冕为东正教君士坦丁堡教区的最高级主教简纳狄乌斯二世,并照拜占庭皇帝的做法,授予他权杖。塞尔维亚人也是一样,一方面不与奥斯曼人及伊斯兰教冲撞,与土耳其统治者相安无事,一方面则寻路进入帝国的朝廷和军队。至于作为塞尔维亚历史的分水岭、发生在普里什蒂纳城郊的青鸟田野上的1389年的塞土科索沃之战,实际上是19世纪浪漫的民族主义者的事后看法和人为之作。
这样一种牧歌式的民族和睦的帝国毕竟过于庞大,过于复杂,使其统治者难于招架,帝国也就注定不可能长盛不衰。虽然没有确切的日期和固定的事件,但在16世纪接近结束时,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败。回想起来,由新大陆的银锭大量涌入而触发的通货膨胀和价格革命动摇了王国的稳定。首先殃及的是靠租金和固定收入生活的人,这一现象是不知不觉之间发生的,最终导致了封锁边境。随后便波及国家雇员。在1640至1656年间,挣薪金的官员从6万人增加到了10万人。于是,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之间开始了争夺地中海海上霸权的战争。威尼斯则关注着自身的贸易利益,静作壁上观。命运自有其狡猾之处,诚如作者所总结的:“威尼斯、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本身,这三个地中海强国不久都消亡了,其意义十分深远,其枯竭的信号悄然跨越整个地中海世界。”
劫掠之类的行径此刻正虎视眈眈地谋求从曾经在战争中发过横财的王国手中挤轧出战利品。随后,这个多彩的帝国的各民族开始“挤作一团来确保安全”。民族主义进入了奥斯曼的世界,这股力量是帝国难以承受的。诗人们借助来自欧洲的民族主义之风大肆鼓吹,古希腊学者梦想着恢复希腊的天地(绝不能使之湮没在异族异教的大殿中!),俄罗斯也试图在圣索菲亚教堂中恢复对天主的崇拜,帝国境内的希腊人和斯拉夫人都不安于原来的生活了。
就在这时,19世纪的后半叶,各城镇都建立起了钟楼,大多出于皇家建筑师、亚美尼亚人巴里安家族之手。这些位于清真寺外或广场上的钟楼的阵阵钟声震撼了奥斯曼帝国——早先的爵爷们悠闲自得,本来是不去过问时间的。这钟声使他们感到困惑,似是在为帝国送葬。随着境内各民族的纷纷独立和连续两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及1913),奥斯曼帝国龟缩到了小亚细亚半岛,并终于在1922年被共和制所取代。至此绵延600余年的大帝国才寿终正寝。
是思想被打败了吗?——法国大学出版社的盛衰
法国大学出版社系列丛书《我知道什么?》已连续出版25年。其策划人雅克·贾卡尔上大学时就萌发了出这套书的念头,当年让他日夜流连的,正是巴黎大学广场和圣米歇尔大街街口的大学出版社书店。今日的年轻学子恐怕还梦想着,将来应邀为《我知道什么?》写上一册两册之时,大概也就是功成名就之日吧。他们该失望了——5月底,法国大学出版社书店关门停业;有传言说原址今秋将变成鞋店重新开张。
法国大学出版社——法国出版界的招牌、法国学术成就的展览橱窗、世界级学者作家信得过的精神居所——财政吃紧已颇有些时日。“我们的书向全世界发问”一度是它近乎狂言的广告词,可这几年,《我知道什么?》每册销量锐减。按出版业的惯常做法,法国大学出版社以增加书目来挽回销售下降,从1990年的658种增加到1998年的1098种。事实证明这不是解决之道。到1998年底,出版社赤字超过500万法郎。出版社已经把印厂附近的地卖了,加上文化部拨的400万“救济款”,大窟窿还是填不满。
好歹麾下还有哲学作家孔德-斯蓬维尔可供安慰,他一本《大德微言》去年出版没几个月就卖出了50万册。他是出版社目前最宝贝的作家,也是读者的至爱,出版社经常收到读者寄给他的自制果酱、香槟酒和手织围巾。
可是,一夫怎能挽大厦于将倾?出版社发出的救急令是改章程。1921年创办至今,法国大学出版社一直以“高校自愿、联合协作”的方式运行,公开宣布“搞出版不是为了大把挣钱”;5月初,它变成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正继续催它改组,60余人将被解雇,伽里玛出版社出了20%的资金——1000万法郎,法国大学出版社各个发行、销售网点从今往后就归到伽里玛一子公司的门下了。
有人说,法国大学出版社把自己卖了,放弃“高校自愿、联合协作”的方针就是自毁内力。也有人瞧不上“怀旧的感伤”,《图书周刊》说这“呜乎哀哉”听来就像中世纪抄书匠面对古登堡印刷机的感叹。
五六十年代,法国人文科学一片繁华图景,其中多少经典笔墨得赐于大学出版社,大批传奇作者如萨特、德里达、福柯和德吕兹造就了大学出版社的辉煌。现如今,她却陷入困境,策划人雅克·贾卡尔乐观地说:“以前,法国大学出版社是个小姑娘,大家一起爱护她;现在她嫁给了伽里玛,好归宿莫过于此。说不定她还会遇到几个好情人呢。”
《新观察家》就法国大学出版社易姓一事提出了另外的问题——“是思想被打败了吗?”在它看来,“学术出版业的衰落,或许喻示人文科学的繁华也将落尽?以后还会不会有人读哲学、社会学,读精神分析学、史学和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