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技术:高技术的历史错位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敦豪快递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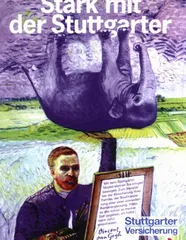
斯图加特保险公司
达·芬奇、牛顿、卓别林……历史上的艺术和科学大师都被高科技企业拿来充当广告形象。以未来为导向的高技术拼命向过去寻根。然而,他们是高技术的合适的文化英雄吗?
“微软”在中国推出“维纳斯计划”,旨在引发电视上网的浪潮。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项崭新的高技术事业用的却是古典包装。
高技术一向与未来联系在一起,高技术乌托邦是现今媒介永不疲倦的一个话题。高技术的鼓吹者对过去嗤之以鼻,如奈斯比特所说:在农业社会里,人们在时间观念是向过去看;工业社会的时间倾向性是注意现在;而在信息社会里,人们的时间倾向性是将来。
然而,这种对于未来的信仰不过是表面现象。高技术鼓吹者不愿意承认,信仰背后隐藏着一种对未来模棱两可的态度,对现状的万般焦虑,乃至向过去寻根的绝望心情。抱住过去,为的是寻求思想上的合法性,即便因此篡改历史也在所不惜。
这可以从高技术产品的广告中清晰地看出来。无论是印刷广告,还是电视广告,高技术企业大量使用历史人物推销其产品。它们力图造成一种怀旧感,然而由于历史人物的错位,这种怀旧感往往是虚假的。
达·芬奇
施乐公司在其产品广告中动用了达·芬奇(1452~1519)。他固然是一位设计与发明的先驱,但他与高技术能有多大关联呢?广告把这位天才打扮成一个企业的忠实雇员,他热情地拥抱复印机、传真机、激光打印机和电脑等所有办公室新科技。广告告诉我们说,这些高技术设备将令达·芬奇设计得更完善、发明得更多,甚至画得更好。但“施乐”的广告有时又把达·芬奇描绘成一个穿越时空的旅行者,面对现代化的办公室困惑不已。一句“施乐令你天才尽显”的广告语,赞颂的是高科技硬件和软件,却对卓尔不群的独行侠构成了一种讽刺,这种独行侠在现代高科技公司里一天都待不下去(至少他无法成为“施乐团队”中的一员)。这样的广告语把达·芬奇的才能排挤到了第二位,而占据第一位的是达·芬奇所叫卖的那些高技术设备。
也许是巧合,IBM公司在80年代初期赞助过一次关于达·芬奇的艺术巡展,该巡展出现在好几所大学的艺术博物馆内。展出的不仅有这位文艺复兴巨人的画作,还有他构思的一些发明,如坦克、降落伞、直升机、汽车和用桨轮推进的船等的设计原型。巡展的主旨是要告诉人们,在我们的时代就像在达·芬奇的时代一样,雅文化与高技术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如同当时一家报纸所说的,若是达·芬奇活到今天,他会欣然成为一位电子媒介艺术家(假如他不为施乐工作的话),把电视屏幕当作他的画板,以按钮和计算机键盘为画笔和涂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巡展恰好表现了相反的意思。本意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反差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与我们的时代不同,达·芬奇的时代宽容并鼓励人们从事多样化的活动;而且,尽管达·芬奇的过人才能无可置疑,很难说他在那个时代里是独特的和惟一的。把他在绘画、雕塑、设计、建筑和工程技术上多方面的成就归结于他的天才是走入了一种误区:他之所以多才多艺,正是因为在文复兴时期还不存在我们今天已习以为常的专业分工,那时技术与文化之间并没有巨大的鸿沟等待人们去跨越。文艺复兴时代成为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并不是偶然的。
达·芬奇肯定会同“施乐”或是IBM这样的大公司中的保守气氛格格不入。这些公司的企业文化也绝不会容许他享有文艺复兴时期那种相对的独立性。尽管如此,企业赞助商们仍然下意识地期望类似达·芬奇的创造性天才会重新出现,把人们从现有的技术和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而企业界也能找到容纳他们的办法。我记得一家笔记本电脑厂商曾将自己出品的两款电脑命名为“莫奈”和“莫扎特”,无疑是想利用人们对天才的崇拜来推销产品,但厂商显然忘记了艺术家身处高技术产业的那种错位。
像达·芬奇一样才能超群的人偶尔也确实出现过,但他们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并不相似。IBM巡展与“施乐”广告无意中传送了这样的讯息:靠现在无法挽回过去。“施乐”的一位经理说得好:“脱离上下文来谈论技术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高技术必须向别处去寻找它的文化英雄。
米开朗琪罗对达·芬奇
高技术把自己标榜为文艺复兴的一种遗产,这种“假”遗产的幽灵很快就缠上了这一行业。1992年3月6日,一种被命名为“米开朗琪罗”的计算机病毒袭击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大约500万台个人计算机。当天是这位文艺复兴巨人517周年诞辰。而让人好笑的是,有一家叫做“达·芬奇系统公司”的专门生产电子邮件软件的企业也遭受了该病毒的重创。此后每年的这个时候,艺术大师和人文主义者米开朗琪罗都不得不同知识毁灭者米开朗琪罗搏斗一番。
牛顿、丘吉尔与卓别林式流浪汉
高技术广告打出的不仅仅是艺术家的招牌,还有科学家。掌上电脑目前非常风行,它的开山之作是苹果公司的“牛顿”,尽管该产品现在已遭受停产的噩运。“牛顿”的命名当然与那位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相关,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据说源于牛顿对苹果落地的观察。不过,苹果激发万有引力定律的传说很可能是牛顿本人杜撰的巧妙故事,为的是不让对手抢到这一伟大发现的首功。无论怎样,牛顿的科学发现与“牛顿”掌上电脑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可能惟一的关联是,该种掌上电脑配置了“智能代理人”软件,能够自动对信息加以组织——也就是说,两个“牛顿”都异常聪明。但就像“施乐”广告中的达·芬奇形象一样,牛顿的创新才能和智力被与他同名的高技术产品逼下了皇位。
与此相比,美国贝尔南方公司利用拉尔夫·本奇(联合国创始人之一,获1950年诺贝尔和平奖)、温斯顿·丘吉尔和阿尔伯特·施韦策(德国神学家,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推销自己的形象,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上述三个人都是多面手:本奇是运动员、大学教授、作家、政治家和谈判专家;丘吉尔是战地记者、作家、画家和世界级领袖;施韦策是哲学家、医生、管风琴家、作家和人文主义者,他们似乎能够向普通人传递这样一个信息:“贝尔南方”在其所期待的所有方面都是领先企业,无论是电讯、信息服务还是移动通信。这种把“美国最受尊敬的电讯公司”同三位对技术不抱幻想、彼此间也没多大关联的名人生拉硬扯到一块的做法,表明高技术企业借助历史造势的手段已达到了恶劣的地步。而且,我们要再问一遍那个老问题:这些意志坚定、才能卓越的历史人物能够同保守的企业文化亲密融合吗?
也许,最令人不安的高技术广告是IBM动用卓别林的流浪汉形象制作的PC广告。这一广告形象帮助IBM在1981年推出了它的个人计算机,并在1991年用以庆祝IBM PC业发展10周年。该广告巧妙地利用了人们普遍恐惧现代技术会引发混乱的心理——如同卓别林在他1936年的那部经典影片《摩登时代》中所表现的一样——转而展现个人计算机人性的一面,它将流浪汉从前那种狼狈不堪、低效而可悲的生活转化成了秩序井然、高效而快乐的生活。不论广告的背景是家居、办公室、面包房还是帽子店,结局总是欢乐的大团圆,广告语则称个人计算机为“摩登时代的工具”。在推销产品的同时,广告一改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公司的非人性化形象,把IBM刻画成一个充满温情的公司。这种做法根本歪曲了卓别林对现代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批判主张,在卓别林的眼里,大公司恰恰是造成社会异化的现代技术的始作俑者。《摩登时代》最终寻求的是对现代技术和工业社会的逃避。在它的喜剧性背后隐含着一个严肃的主题:人类无法掌握现代化的机器。就像美国60年代反物质至上的歌曲今日被用来在电视上推销豪华汽车、有价证券和其他奢侈品一样,IBM的广告扭曲了过去,创造了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假的怀旧感。
挥之不去的恐惧
分析了这一大堆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种非常可能的情况是,高技术公司及其广告制作者对历史的准确性根本不在乎,他们故意歪曲利用历史人物来推销产品,只要产品能卖得出去。或者,这些公司及其广告制作者也有可能不知道自己在曲解历史,反而认为他们做的是推广历史的工作。更加糟糕的是,他们可能真诚地相信,他们广告中的历史人物如果真的目睹了今日的高技术,一定会满怀欣喜地加以接受;卓别林可能会真的被个人计算机解放出来,变成一位心满意足的企业家。
可以判定,高技术在充满激情地拥抱现在和未来之时,并不能放弃过去。在高技术鼓吹者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害怕明日的世界可能无法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乌托邦。没有人反对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舒适、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富强的技术进步,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不断怀念旧日的美好生活。高技术产业拼命地向过去寻根,拼命地同过去建立紧密的联系,实际上是表明它对未来缺乏自信。 ibm牛顿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