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霸气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君梅)


“那是一种权利的傲慢”,香港《亚洲周刊》杂志主编邱立本先生在获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狂轰滥炸南联盟40多天后公然向中国驻南大使馆投下3枚导弹后说。
“傲慢”这个词借用到这篇关于时装之都的文章显然是合适的。只是用在美国时装身上,要换一个词——“霸气”。换句话说,美国时装不配用“傲慢”这个词。他们凭什么傲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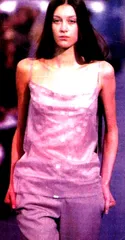
’99法国女装流行趋势
法国高级时装,固守“文化的傲慢”?
早在一战前后,秉承优雅传统的法国时装就已经十分成熟了。二战期间,法国时装界被迫停止他们的艺术创作。这时的美国尚没有一位能和欧洲设计师等量齐名的时装设计师,甚至可以说没有“高级时装”这一概念。美国人能做的至多是趁战争的硝烟远离自己的本土、趁战争期间人们的“实用主义”心态发展成衣制造业。
巴黎和纽约的这种力量对比在二战后更悬殊。法国时装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克里斯汀·迪奥带来了被美国媒体称为“新风貌”的女装;夏奈尔复出。之后,皮尔·卡丹、伊夫·圣·洛朗等年轻设计师相继在巴黎时装舞台闪亮登场……美国仍没有自己的时装品牌。就连今天颇让美国人自豪的时尚媒体——美国杂志《时尚》、《哈泼斯杂谈》、时装日报《WWD》,以及《纽约时报》的时装评论版也都是在对法国时装的报道中成熟起来的——在对那些不断变化的线条和裙子长度的惊叹中学习时尚。
今天,法国作为世界时装之都的地位正受到挑战。后工业化社会对时装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进入电脑与信息的时代后,全球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市场。这个大众化的市场冲击了高级时装的地位——法国为高级时装这件“令人陶醉的艺术品”付出了代价。几时甚至上百个工时手工缝制的高级时装在全世界的消费者只有大约两千人;法国每年的时装与香水出口约100亿法郎,其中高级时装占3亿~4亿法郎,而其投资却为4亿~5亿法郎。可以说法国的高级时装是在“赔本赚吆喝”。
傲慢的法国时装不得不向市场作适当的妥协。法国工业部在90年代初推出的改革方案包括“淡化高级时装和高级成衣界限”、“扩大高级设计师协会的会员”、“认可高级时装名牌的最终决定权在政府工业部门而不在时装行会”等措施。就在这时候,巴黎的对手出现了,有迹象表明,伦敦、东京、纽约正在成长为新的时装之都。在竞争中砥砺品位对世界时装来说本是好事。
但纽约的动向非比寻常。
超级大国的时装梦
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产品的年零售额是60亿美元,在美国《时尚》杂志的全球时装设计师销售业绩排行榜上名列第一。他的成功秘诀是“产品延伸策略”——名字随处可见,从牛仔裤、马球装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涂料。他还与“锐步”(Reebok)携手制造运动鞋。难怪美国媒体得意地宣称:“流行品位已不再高高在上,为追赶全球行销的脚步,现在,夏奈尔(Chanel)、阿玛尼(Armani)、普拉达(Prada)必须和支配大众媒体的品牌Nike、可口可乐、迪斯尼、苹果电脑竞争。想要在流行工业保有一席之地的设计师,竞争的惟一方式是将产品多样化,并尽可能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产品上。”
排在同一榜单第二位的是年零售额44亿美元的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这位在全球青少年中有着很高知名度的设计师不仅捧红了著名的瘦模特凯特·莫斯,还倡导了一股抹杀性别的“中性风”。其产品由低档上升至中档,但在很多消费者心中它是名牌——凭借的是美国式的广告策略,即“让自己的每一个举措都成为国际事件”。

KCD是现时美国声誉最佳的公关公司。其创始人为美国著名时尚杂志《Vogue》及《纽约时报》的三位时装编辑。他们善于为各类牌子宣传确立视觉形象
Ed Filipowski(左)曾任记者,Julie Mannion(右)原是广告监制。二人都在80年代中期加入公司
纽约的女设计师唐娜·卡兰(Donna Karan)也非常得意,她的14亿的年零售额超过许多法国、意大利名牌,位居第5。更让她得意的是,几乎可以说,自从她创造“DKNY”(“唐娜·卡兰与纽约”的缩写)以来,时装界掀起了一股高级时装纷纷推出运动风格的“二线品牌”的风气。“美国运动装”(American Sportswear),这的确是1998年以来被设计师和媒体频繁提到的一个流行语汇。
经济上的胜利使得美国人轻松地把自己的审美趣味(或者说“生活习惯”)搬上了高级时装舞台。意大利的阿玛尼用缎子裁制连帽上衣;比阿玛尼更老的牌子“瑟瑞提1881”(Cerruti 1881,其创始人曾教授过阿玛尼有关纺织品的知识)把上衣扎进松紧带裙子里。最让美国人骄傲的要数设计师亚历山大·麦克奎恩,这个美籍毛头小伙居然成了法国高级时装纪凡希(Givenchy)的首席设计师,不仅把这个被称为“优雅花园”的老牌子搞得惊世骇俗,还穿着印有“Nike”显著标识的T恤衫登台谢幕。
其他一些欧洲名牌如古奇(Gucci),在启用年轻的美籍设计师(Tom Ford)后,人们也很容易看到品牌的风格变化。
美国媒体更加膨胀了:“自从年轻的美籍设计师攻占法国人引以为傲的、拥有百多年悠久历史的高级时装屋,彻底以美式风格颠覆欧洲时尚的‘生态圈’。人们不得不承认,自大的巴黎、灵黠的伦敦这回都得跟在向来被视为次文化的美式流行身后……就像好莱坞的美国梦,没有不可能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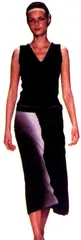

’99伦敦女装趋势
忙着赶制赚钱的衣服的美国成衣设计师们以往都是“单干”,没有组织,没有像法国高级设计师那样每年两次的豪华展示会。现在有了一个叫“7th on Sixth”的组织帮助他们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公园里搭帐篷进行每年两次的时装发布会。在那些临时搭起的帐篷里,美国设计师跟欧洲设计师打起了“时间差”。欧洲设计师通常是在每年的4月发布次年秋冬季的流行趋势,10月发布次年春夏的流行趋势。1998年9月,美国设计师赫尔穆特·朗(Helmut Lang)率先发布了1999春夏最新款式,唐娜·卡兰、卡尔文·克莱恩、尼科尔·米勒等人积极响应。一位设计师称,这样捷足先登可摆脱抄袭巴黎的嫌疑,给消费者和媒体一个先入为主的冲击力,同时也为这之后的制作生产赢得更多的时间。纽约时装展的主办机构称,美国设计师的秋冬季时装发布会也将比欧洲提前两个月举行。

推广纽约时装的幕后强人Fern Mallis,她令纽约成为全球关注的时装信息发布站。她说:“巴黎和米兰都有组织完善的设计师工会,相比之下,美国的设计师简直是孤军作战,所以我组成了‘Seventh on Sixth’这个组织,把大家团结起来”

’99纽约春装流行趋势

’99米兰春装流行趋势
美国设计师比欧洲设计师更清楚,虽说销售数字不像设计风格那样能摆上舞台给设计师带来瞬间的风光,但在这场商业气氛浓厚的时尚竞赛里,订单比掌声重要。
还是那个赫尔穆特·朗,他索性连传统的时装发布会也不做了,代之以光盘,通过互联网传给全世界。

’99米兰春装流行趋势
下世纪,到哪里去找法国式的优雅?
法国的茹威先生把美国时装的成功归结为“采取‘求方路线’”,而在欧洲,尤其是法国设计师眼里,时装从来都是典型的“供方产品”。“法国设计师总是思考它的设计性、艺术性而不是过多地征求市场的意见。时装不是普通的消费产品,除了使用价值还有个性需求。个性也不是摧毁经典和传统这么简单。”茹威先生目前在位于苏州的中法时装培训中心教授市场学,并担任该中心副主任。
现在的消费者真那么需要“个性”吗?
早在50年代初,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将一向量身订做的时装业引向成衣后,美国《时尚》杂志即预言:女性害怕穿着相同款式服饰的心态将会一扫而光。该杂志将时装潮流和另一项大量生产的商品汽车做了比较。“有人会因为外观相同这个因素而拒绝购买某款汽车吗?肯定不会。相反,他们还会认为这种一致性是品质的保证。”
半个世纪后,这种求同的消费心态在“后工业化时代”受到了质疑。但它又有了新的存在的理由——世界经济一体化。没有历史,其文化也一直被认为是“次文化”的美国终于找到了最佳时机——仰仗其超级大国的经济技术势力,强行推广其文化和生活方式。“世界化”几乎成了“美国化”的代名词,法国时装不能再无视美国时装,就像法国电影不能无视“好莱坞”,法国的“大磨房”不能无视“麦当劳”,因为“麦当劳”已经开到你的家门口了。美国早已经向全世界显示了它“经济的霸气”。现在,它又在做着另一个美国梦。
“分析影响时装的宏观因素,‘世界化’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正面影响是加快了世界文化的交流,西方设计师已经从东方的中国、日本、印度和非洲大陆找灵感,东方设计师的设计制作也明显糅合了西方的元素。但是‘世界化’的负面影响是值得警惕的——一种雷同的趋势。
“美国的经济发达,它也试图把它的生活模式输出。美国的着装方式正试图同化世界时装业。大家都知道他们穿衣简单、随便,如果全世界都穿成这种风格(现在在青少年中已有这种趋势),时装的艺术和创造成份减少,世界文化也就减少了它的丰富性。欧洲的设计师对此有思考。”纪勒明先生就“青少年着装美国化”的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当时是1998年冬,他即将结束中法时装培训中心的工作返回巴黎,在下一个时装季出任伊夫·圣·洛朗的助手,应中国时装设计师协会之邀在北京与中国媒体进行交流。这位法国色彩委员会主席、年轻的高级时装设计师穿了一身裁剪精良的咖啡色天鹅绒西服,领口露出草绿色衬衫——这是1999~2000年春夏流行色卡上出现的颜色。这样的色彩与他打理得非常艺术的金色头发合在一起,让人体会到了那种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法国式的傲慢与优雅。(1999年春夏国际女装集锦由中国纺织科技信息研究所《国际纺织流行趋势》提供。纪勒明图片由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提供) 纽约时装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