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世界中,艺术家何为?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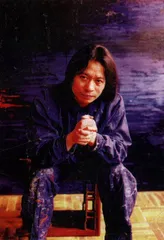
米丘

米丘的综合材料作品,《远》,飞翔的翅膀几乎是米丘作品的象征性符号。他的AnTeeh主张也旨在探索技术与梦幻人性的协调
米丘在上海几乎成了神话般的人物。作为建筑师他参与过24座历史名城的重建规划等国家建设项目,作为艺术家旅欧8年,除了艺术创造,他创立了庞大的“欧中文化交流计划”。回国后,他完成了一系列城市环境设计,并且形成了一个关于艺术和技术的新概念——ArTech,由此联络了一个艺术加技术的群体深入地推进着上海的环境建设。
问:把Art和Techno以一个词的方式连在一起的特殊用意基于什么考虑?
米丘:如果从最早的艺术说起,是技术产生的概念,包括形态、色彩理解、材料的选用,只能是那样用的,用什么样的红色是因为有那样的矿物质,对人体的理解,对房屋的理解,对生产对收获的理解等等,都是由技术产生的。那时给我们留下的所有东西,今天我们都认为是艺术品。再进一步来看,到了达·芬奇时代,对骨架的分析对肌肉的分析在医学的发展中都提出了一连串的推进,科学家也提出了关于光的很多分析,也有了技术能力在矿物质中提取更多的颜色,所有这些技术的发展加上宗教的理解才产生了所谓的宗教艺术。当时的艺术家具有更广的环境的概念,他能把文化、技术放到他的建筑里。米开朗琪罗不仅仅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力学家、化学家和颜料专家,整体来说,他的艺术也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人文环境中形成的。我们熟知的悉尼歌剧院本来设计的是由不规则的曲面构成的,后来是因为技术的局限改为一个椭圆的曲面,就是取椭圆的一段,完全是受当时材料技术的限制。如果是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原来的方案是绝对可以成立的。
这都说明技术给艺术提供了可能性。今天我提出ArTech的概念,就是想在今天我们的高科技的前提下,在我们的材料无限发展的前提下,我们的艺术是否也应该与其有一个协调的关系,更高度的绝对化的感性跟高度的绝对化的技术相配合。我绝对相信,如果在2000年以前秦始皇建造了一架飞机放到今天,我们肯定说它是艺术品。Art是很感性的,非现实的,非时代的,Techno是历史的,社会化的,现实的,伦理的,这两者放到一起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也与今天的社会观念是吻合的。我现在做的和后面就要做的都是基于这个考虑,是想验证这个东西。包括我们的建筑观念、城市的概念、产品概念、舞台的形式、服装的概念确实都在走这条路,想把技术更多地加入艺术成分,如果放在ArTech这个概念下,就很有意思了。其实是一个运动,我这也许有些夸张,但客观上如此。
问:18世纪艺术就获得了独立性,艺术家和观众也都习惯于艺术的独立,并且人需要艺术提供的感性力量,你作为艺术家提出这样的概念是否认为艺术出了问题?
米丘:我提出这个概念不是否认目前的艺术努力和创造,所有艺术家做的全是对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缺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很多系统化的操作。艺术家应该更走向绝对的感性,这是对艺术的要求,同时也应该接受今天我们的技术成就和社会状态,如果有了这些具体的东西,就不需要去争论很多大而空的问题了。技术专家和艺术家各自独立干各自的,就会使城市的空间品质降低,艺术的作用范围不能扩大。波依斯是绝对感性的艺术家,到六七十年代已经吸引了一大批民众。那个时候看到卡塞尔是一个工业城市,他做了一个装置弄了7000块石头,然后又在这些石头旁种了7000棵树,确实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那当然这个城市政治家也欢迎,民众也欢迎。这是最早提出的文化和环境和绿化的结合,因此也得到了绿色和平组织的帮助。
在社会发展中做说明事情总有一些规则相伴随,比如,书法,我说应该叫“法书”,按照一定的“法”来书,如果没有这个“法”,就叫涂墨了。可是上海一下子有3000栋大楼出来,没有一个在理论上有推广意义或对后代有影响的完整概念出来。这3000多栋大楼中只有三四栋被世界建筑界接受的,这其中二三栋是海外设计的。
ArTech是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联合起来的艺术行动。面对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重新审视人类生存的意义。人类幸福是我们生存的目的,为了是技术还是艺术都是为了这个。城市就是有一大堆庞然大物堆在那儿,艺术应该去调整它。ArTech 就是要来考虑人、自然和技术的关系,以人类感性来平衡高度技术。上海要搞一些环境的改善,这对艺术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问:你在上海宁寿大厦的环境设计中是否是这样操作的?
米丘:那是上海人寿保险总部大楼,楼高100多米,质量是很高的,这个建筑的前面有一个牌坊,是四明公所的牌坊,也叫宁波会馆,在人民路858号,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业主和设计方一直在找一个方案,解决大楼和这个牌坊的协调关系,最终委托给我和天华公司。

宁寿大厦环境艺术
一个城市的建筑不能跟人没有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链上,不考虑这些不行。大楼的底层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我就把底层空间和牌坊加上周围2000多平方米的空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这个牌坊挡在大楼前,本来他们都要打掉它了,现在我们要把它留下,但也不能挡在大楼前,就把它平移26米。这可能是国内第二座被完整平移的古建筑(另一个是上海的天文塔)。在新建筑和牌坊之间设计安放一块大玻璃,18米长,2.4米高,厚是10厘米左右,在技术上是国内从来没做过的,在国外也没做过。下面用光导纤维朝上打,效果是玻璃本身成了一个发光体。在新建筑里面设计了一个倒挂的玻璃方尖碑。这花了我多长时间?最大的精力都用在使它成立的技术研究上。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慢慢才形成的这个概念。在设计香港新机场的环境那个项目时就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机场很漂亮,不锈钢,大玻璃,是英国建筑师做的,是绝对理性的。我在设计候机厅的环境时就在考虑如何把跟它有关的材料、形式更艺术化,更感性化。它的技术已经存在了,我就是加入了感性的部分。
后来在上海一些朋友参与进来一起工作,这个概念就比较完整了。有了这个概念几乎从古典主义的到今天的东西中都能看到艺术和技术的关系,它确实反射在社会中,也给社会新的启示,因为有了米开朗琪罗人们才那样想象天使。在国外工作那么多年,更多的不是艺术的教育,理性是对我最大的启示。反回来看,就感到我们对“品质”“质量”没有追求,就是艺术品本身也是缺少质量要求的。虽然骂的人很多,没有建议提出。任何东西都是要有规则的,歌剧有规则,布鲁斯也有规则,并没有说它的规则存在后它的艺术性就减弱了,没有嘛。在今天提这个概念,其实是为了生活的质量,艺术是生活质量的一部分。让工程师和设计师参与进来,艺术会变得特别有生命力,也是为了在技术中重新考虑生活质量的问题,让技术和我们的梦幻和我们的情感结合起来,让我们的艺术在技术中呈现出来。两者表现结合,不然就像你提到的全国的房子都贴瓷砖,悉尼歌剧院也贴大瓷砖,它是为了反射海上阳光的倒影,与它那种飞翔的形式是一致的。我们的房子贴瓷砖也有技术上的考虑,功能上也有理由,但完全没有形式的考虑。
问:像海德格尔质疑现代社会诗人何为,这是你的艺术家之作为吗?
米丘:我现在的工作就完全围绕着这个概念,这样就很明确自己在干什么了。克利斯托为包装德国国会大厦的计划与政府对话、为此做准备用了24年的时间,做这个事情他从来不改变的,这种经验我想是有价值的,是最值得我们推崇的。还有就是跟民众的对话,他的作品影响人家,人家也影响了他,大家是公平的。 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