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明信片:蝴蝶的诞生
作者:娜斯(文 / 娜斯)
4月份现代艺术馆与林肯中心电影协会合办的“新导演、新电影”电影节我选看了3部电影,一部是伊朗的《蝴蝶的诞生》(Birth of a Butterfly),一部是中国的《小武》,另一部是葡萄牙与其原殖民地南美岛屿Case Verde的有关足球的一个故事。
自从看了第一部伊朗电影《在橄榄树下》,用英文的说法,就是被“hook”上了。我为它们感动,为它们坦诚的人性,为那些干枯背景中的亮丽的色彩点缀,为它们简单而又生动的形式。甚至片头字幕那些神奇的书写方式,也让我为惊叹其美。并不是我看过的每部伊朗电影都让我满意,但多数让我觉得有意思。《蝴蝶的诞生》有意思之处是,它是一部讲宗教的电影。无论东方西方,古代艺术与宗教的联系多多,在当代电影中也有,但更多是解构性的。前阵看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鳗鱼》,那里面很有些佛教的意念,但《蝴蝶的诞生》是直截了当的关于信仰。因为方式少见,看起来更别感独具风味。它是三段互相独立的宗教寓言。第一段,《诞生》(The Birth);第二段,《道路》(The Path);第三段,《蝴蝶》。
在《诞生》中,小男孩的妈妈在难产,继父心烦意乱,小男孩跟他不共戴天,一番冲突之后,小男孩的叔叔把他接到葡萄园。小男孩和他的妹妹在那里嬉玩。继父来看兄妹俩,继父此时却对他们显示挚爱。小男孩仍不予理睬。但是,小男孩慢慢觉悟,妈妈死了虽然大人没告诉他。他自己跑回村子,家家挂着黑色的灵幛。最后一个镜头:继父坐在门槛上痛哭,小男孩抚摸了他的头。
在《道路》中,主角也是一个男孩。他的腿有点瘸。他要去朝圣——为自己的腿,也为祖母的病。在闪亮的星空下,他睡着了,早上醒来,祖母乘的拖拉机已经离开。小男孩决心已定,他走着去。在泉水边,他遇见一位陌生老者(故事以这位老者的画外音展开)。老者给了他一个盛了泉水的水瓶和一根铁条,说是给朝圣者的,自己便躺下睡觉。小男孩提着水瓶和铁条走啊走,竟赶上了奶奶那拨人的拖拉机——拖拉机的一根铁条断了。不用说,小男孩的铁条正是他们需要的。现在开了车继续赶路,傍晚,因为中途耽误,大伙得休息一夜。小男孩一意要赶到圣堂,他自己继续前行。到达了那所庙堂,地上一个人睡着,是谁?——当然是那老者。最后一个镜头:小男孩向老者递上那壶圣泉的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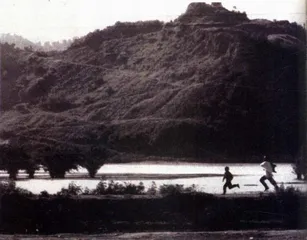
《蝴蝶的诞生》剧照
第三段,《蝴蝶》。一个“知识青年”——权且用中国说法,总而言之——来到一个偏僻乡村任小学教师。对其动机,影片没有多说,但暗示其对原来生活的某种幻灭感。谁知,无意之间,他被这里的乡亲视为“圣者”,因为他遇到一个村民哭天抢地——他的牛丢了。老师说,去找吧,不会丢的,就从这边开始;他又见一村民在哭儿子出门在外几年未归,他说,会回来的,你的儿子会回来的;与村长走过小桥,他看到河水,说可能会发水吧,村长说不会,多少年没发过水了。结果,牛真找回来了,儿子也回来了,河水也真的涨了。晚上,他被敲醒了——院子里黑压压一片村民,要他为他们祈祷,祈祷河水退去。他当然是大吃一惊,他那些话都是无意之中应验的,他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可是,第二天,村里的人都不再理他了,因为他的拒绝。村长说,他不肯替村民祈祷,不光是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信仰,而是因为他怕,他怕祈祷不灵验。青年老师被迫拖入了信仰,或非信仰危机中。他的班上有个学生,整天玩蝴蝶,带着一个蝴蝶瓶来上课,经常把教室搞得蝴蝶翩飞,同时,读起《古兰经》,他比谁都读得流畅,好听。河水涨了之后,他得绕道,上课来晚了。老师说,你天天追蝴蝶,你也该像蝴蝶那样飞过来啊。结果,第二天,他真的没迟到,后来,他又飞跑来找老师,说爸爸病了,拉他去帮忙,这次老师没有拒绝,他跟着小孩飞跑,跑到河边,他摔了一跤,待他抬头,小男孩真的从河水上已跑过去了——河水在小男孩脚下退去。他却不能,谦卑地站在齐腰的河水中。最后一个镜头:他伏首一望,看见一只蝴蝶停落在他肩头。
稍微熟悉一点点西方宗教故事的人,都会看到这里的很多熟悉语汇,比如《诞生》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创世记》伊甸园一段,只不过让小男孩小女孩失乐园的是妈妈的死。《道路》,拍得最好的一段,是朝圣故事,古典文学中这种故事也很多,这里的好处是平淡的惊喜,自然天成。最后一段,老师站在河水中,是受洗的形象,但是那只蝴蝶却又来得意外。3段的最后,都是西方叫“epiphany”(显圣)中国叫“顿悟”的东西,信望爱的经受检验。
你可以毫不理会它的宗教背景,它们也可以只是3段非常好看的电影故事。影片在伊朗西北部山区拍摄,景色荒芜却又有惊人之美,点缀其间的色彩——绿洲、盆花、地毯,格外夺目。风景、色彩、人、寓言和现实,交和在一起。你会想起古老的故事,可是又可以是现在的事,它其实是有很多缺点的电影,尤其是多处音乐画蛇添足。但缺点并不掩盖它有意思的地方。
新现实主义曾经被冠于战后意大利电影,今日的伊朗电影的某些侧面也经常为影人将之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相连。我是看了意大利导演罗塞里尼的一部关于渔民生活的电影后才意识到当年英格丽·褒曼的举动之不凡——以好莱坞一流红星的身份跟罗塞里尼这个新现实主义导演结合,还在他的影片里跟非职业演员的渔民配戏(那被找来做男主角的渔民听说要与好莱坞女神英格丽·褒曼演戏,其反应可想而知)。
但是新实主义并不能代表意大利电影的全貌,而今日的伊朗电影,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渊源也只是其一个方面。伊朗电影有意思之处正在于,它并未拘泥于某种主义或意念,并不是把自己局限在所谓“艺术电影”的框框里,而是随意而为,所以每每令人感到一种原创性的活力。比如我以前提到过的《戈拜》,导演的初衷是受命拍摄伊朗某少数民族地毯编织的纪录片,但是结果变成了个故事片。但是其中仍有很多纪录片的成分,由职业演员出演的主线故事串连。有一场发生在小学教室里的段落,主人公的叔叔教小学生颜色的词汇,他的手指指天空,说那是蓝,镜头变成天空和他的手指——也变成了蓝色。他拿着一束黄色的花指向草原——那是黄色,镜头成为草原,他的手也一样变成黄色……现实、想象、生活的奇妙,这里又有些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但应该说这是伊朗的魔幻现实主义,前者迷离,后者清新。
同一导演又拍过以伊朗电影发展史为题的电影,被称为“致伊朗电影的情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电影并非真空发展,好莱坞电影、印度电影、欧洲电影,都曾有过一席之地。其中令人难忘的一场戏是国王坐在人力抬举的席位上被前呼后拥着看露天电影,银幕上,一个老太太在纫针,纫啊,纫啊,纫啊,底下的人都睡着了,老太太的针还没纫进去,国王受不了了,派卫士去帮忙。卫士走上台,走进银幕,谢天谢地,终于帮老太太把线穿进去了。可是,他再要从银幕上下来的时候。电断了,他下不来了!
这个好玩的段落里,那个老太太纫针纫不完的场面让我觉得是跟某种以现实主义为名折磨观众的“艺术电影”开玩笑。而我喜欢这个玩笑。但是在《橄榄树下》里,有一个拍电影的场面讲其中的非职业演员一场简单的戏怎么也搞不对,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我又觉得兴味无穷,最后一场大远景的镜头,漫长无比,只有两个小人影在动,可是又是很震的一场,乏味与不乏味,区别何在?谁都知道蝴蝶是怎样诞生的,可是在一只蝴蝶飞起来的时刻,你还是不得不感到一种奇妙。

《小武》招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