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芭比那样生活?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君梅)

“不仅是个玩具娃娃,她是美国社会的一个象征。”——芭比娃娃厂商的“大言不惭”刺伤了一些美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交流》杂志主编劳拉·理查森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很少留意低级趣味的事物,大概也不会留意一个长发披肩、胸部高耸的娃娃。”
但这些微词并不能阻止芭比娃娃和其他“低级趣味”的事物一同进入美国短暂的历史。1976年,在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时,芭比凭着美国人封的“世纪娃娃”的头衔在特制的“时代密封舱”里占了一席之地,只待该国300周年国庆密封舱开启时再重放光彩。
1999年3月,芭比娃娃以新的形象——“个人定制芭比”出现在互连网上,以庆祝自己的40华诞,并表明自己在业已到来的“硅纪元”仍不落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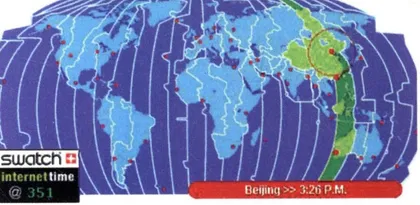
打篮球的芭比
没有绯闻但有争议的“人物”
这真是个有趣的巧合——芭比和玛丽莲·梦露是“同乡”,都诞生在阳光明媚的美国南加州。1959年,芭比穿着性感的黑白条纹泳装在美国玩具大展上首次亮相。商家却不希望芭比像其他“女明星”那样绯闻不断。
这个目标消费群为中产阶级的娃娃有一整套典型美国中产阶级式的、清白“简历”——她是白人,全名芭比·米利森特·罗伯茨(Barbie Millicent Roberts),生于1959年3月9日,母亲是玛格丽特·罗伯茨。她就读于常春藤高级中学,17岁毕业,有几个“男朋友”(都是马特尔公司的产品)。
芭比的确没有绯闻。但她在这40年里不断受到指责。这些指责反映了40年来,人们审美和价值标准乃至“世界观”的变化。
芭比的三围
直到90年代,对芭比的指责仍在继续。
“妈妈,为什么不给我买个芭比?”
“因为我讨厌芭比。她教给小女孩们惟一最要紧的是长个又高又瘦的身材,胸脯要高高的,衣裳要多多的。所以我说她不是个好榜样。”

想不到芭比也爱玩游戏听音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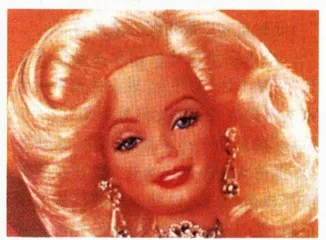
“怎么样,我像梦露吗?”
安娜·昆德伦女士把她和女儿的这段对话写进了一篇题为《我讨厌芭比》的文章,1994年刊登在《纽约时报》。
芭比的“三围”是争论的焦点。在芭比之前,没有一个娃娃像她那样具有成人色彩。她的“三围”如果按真人折算,是一串不可思议的数字:胸围102厘米、腰围46厘米、臀围82厘米。按照这个标准挑选时装模特全世界不知有几人能当选。在芭比的三围被左翼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拿来说事儿的时候,生产商对芭比的曲线做了“合理解释”:芭比只有真人的1/60大小,为了使她在穿上真人使用的布料做成的裙子后仍然窈窕,她的腰就被处理得细了一些,腰细了胸脯自然就显得突出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够诚恳。
“芭比娃娃之母”——那个创建了日后著名的马特尔玩具公司的女商人鲁斯·汉德勒曾坚持这样的观点:“我构思芭比时认为,小女孩应该跟胸部丰满的娃娃一起玩,这对她的自尊心有很大的益处。”

“你可以通过计算机与我交流”
芭比1959年一问世,女孩子们就把她们原来抱在怀里的娃娃扔到了一边。表情狡猾的芭比击败了拥有甜蜜的圆脸、丰满的腰身和小鹿般眼睛的娃娃“雷夫朗小姐”。后者出自以名人为原型生产娃娃的意中人公司(以罗斯福总统的小名命名的“泰迪熊”就是该公司的产品)。“雷夫朗小姐”的原型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女模特,公众熟悉广告上她那甜美的笑,却不知其真名——50年代的女模特还不能靠自己的名字成为“名人”。“雷夫朗小姐”出现在美国人对女性美的看法即将发生变化的前夕,她那种“古典美”在今天的女孩看来太胖了。以“少女时装娃娃”为卖点被促销的芭比似乎嗅觉灵敏地预感到了未来的潮流。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芭比推动新标准的确立——80年代末冒出的“超级名模”身上都有芭比的味道,而著名的克劳迪亚·希弗简直就是芭比的真人版。希弗也因为这一点而占尽风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位模特名字的前缀是“芭比娃娃”。
她究竟是谁?
针对芭比的另一个争议来自这个少女娃娃飘忽不定的身份。在《我讨厌芭比》这篇文章里,作者对芭比——一个娃娃,做出刻薄的评价:“芭比像吸血鬼德拉库拉(记者注:德拉库拉是罗马尼亚民间传说中的王子,生前是英雄,战死后为爱情而阴魂不散。英国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了这个世界著名的吸血鬼),惯于乔装打扮,总把真实面貌掩盖起来,忽而是外科医生,忽而是宇航员,忽而又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从1959年出世以来,她始终是‘窈窕淑女’的典范。”
芭比诞生之初,像50年代西方描述的女性那样,是一个正在摆脱战争阴影积极向往美好生活的女郎。有专门的服装设计师为她制作时装。第一批时装表达了对欧洲的崇拜——“缤纷巴黎”、“罗马假期”等。第二批时装就“非常美国”了,名为“忙碌的女孩”的系列是这样的形象:芭比身穿红色麻制套装,手中挽着一个装满草图的公文包,这是“时装设计师芭比”。除了工作,芭比也很会美国式的享受——在“迷醉之夜”、“聚光灯下的独唱”系列,人们看到了穿着丝绸裙子、天鹅绒紧身衣,戴兔毛披肩、玫瑰花,拿麦克风的芭比。
一些评论家刚刚给芭比“独立自主的女性象征”的赞誉,反面的意见就迎面扑来。60年代晚期,美国女权运动兴起后,芭比遭到的批评尤为猛烈。一些女权主义者在抵制1968年的“美国小姐”选美活动的同时,顺便指责起芭比娃娃,她们甚至反对小女孩玩所有的玩具娃娃,认为这会强化既成的社会偏见和“陋习”,使女性永远处于无权状态,只能依附于男性,让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挤了她们可能在商界、科学界、艺术界和政界一试身手的机会。“左翼”人士更是把芭比娃娃说成是女性最糟糕的典型——头脑空虚的泄欲工具。

“我来自美国”
最让“芭比之母”伤心的恐怕是遭到自己儿女的反对——他们正是芭比及第一个男友的原型。女儿巴巴拉对母亲以她为原型做同名娃娃芭比甚为不满。儿子科恩(Ken Carson)的名字也被安给了芭比娃娃的第一个男友。科恩长大后在拉丁美洲从事医学研究(你现在上互连网就能看到,最新的芭比产品目录上有两个穿“白大褂”的芭比男友——Ken和Tommy医生)。真的科恩医生反对芭比娃娃不是因为自己被“克隆”、被放在芭比附属物的地位,而是他发现,在有色人种看来,芭比娃娃是自轻自贱的象征。
“我们小女孩无所不能!”
这句响亮的口号是80年代芭比娃娃的广告语。在成年人借着一个娃娃唇枪舌剑地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小女孩们却在与芭比娃娃的比较中学习在现代社会做一个不落伍的女人的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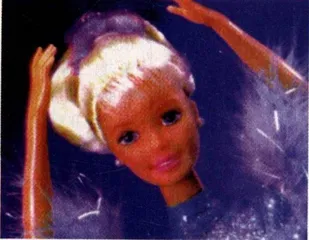
“时尚、漂亮使我成为时尚的先锋”
60年代初一本名为《性与单身女郎》的书在美国畅销。小女孩身边的芭比与潮流很合拍——自食其力、身材窈窕、独自远行、总有美妙的邂逅、新潮大胆有点自私但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芭比想成为谁就能成为谁——只要换一套衣服。尽管生产商为芭比和她的第一个男友设计了结婚礼服。但芭比至今“未婚”——玩具商不希望她陷入“婚姻的羁绊”。她应该永远是快乐的单身女郎,随时准备为各种机会出击。小孩子们显然对此不大理解,他们“强烈希望”芭比有孩子。1963年,生产商让芭比当临时保姆照看别人的孩子,一套五彩的玩具房子作为附属品热销。
在成为意识形态领域颇有争议的“人物”后,在越战引起的政治对立后,芭比“躲进小楼”,从她的服装上你只能看到纺织品,看不到她的社会角色。
70年代后,芭比以时尚先锋的姿态积极倡导时髦的生活方式。70年代响应来自英国的反性别打扮——男孩穿丝绒衬衫、蓄长发,女孩穿喇叭裤、剪短发。“芭比”们自己也一定说不清这是性别觉醒还是性别模糊。

“我一直是单身,但我也有婚纱”
80年代芭比在新的享乐风气中成了“雅皮”——她享受阳光、冲浪的快感,坚持运动、特别在意自己的身材。1984年推出的“好身材芭比”身着紧身的健身衣,脚踝上套护圈,足蹬运动鞋,她还拥有一张“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卡”。1985年,“白天到夜晚”系列首次将芭比娃娃定位成“职业女性”。她的公文包里有一张信用卡、一张名片、一份报纸和一台计算机。如果不是照顾小女孩的审美趣味,相信芭比会穿更具权威感的深蓝色套服而不是粉红色的。她那套衣服裁剪精良,正面是正规的上班服,翻过来是闪光的晚礼服。
90年代的芭比娃娃还是工作着的单身女郎,她的脸型变得圆了一些,腰围变粗了一些——这不是因为芭比“人到中年”发福了,恰恰相反,这反倒说明她年轻(现在穿低腰裤子、不系腰带更不穿束身内衣的女孩们肯定没有“郝思嘉”那样的细腰了)。芭比是不是高胸脯也不重要了——1997年美国《哈泼时尚》(亦译做《集市》)杂志在评价当年的流行现象时说:“与低胸连衣裙最相配的是平胸。”
个人定制芭比的出现更是迎合了时代“尽显个性”的呼声。现在的消费者也许根本不知道当年芭比娃娃那份“白人中产阶级”的简历——对商家来说,这最好不过。多种肤色的芭比娃娃显然不会再像从前那样遭到白人以外的一些民族的强烈抵制。是的,除了皮肤的颜色,世界各地的新人类越来越一致了(眼晴和头发的颜色?今天的新人类可以通过戴隐形眼镜和“即喷即染”玩改变眼睛、头发颜色的游戏)。芭比放下昔日的明星派头,在“我的设计”的标签下变成了“你自己”或者你的邻居。电脑和互联网加快了芭比作为“亲善大使”的步伐。
芭比真是“亲善大使”?还是又一瓶卡尔文·克莱恩的香水,又一个麦当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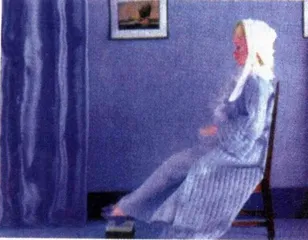
“这次我走进了惠斯勒的画中,并且扮作他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