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速度的代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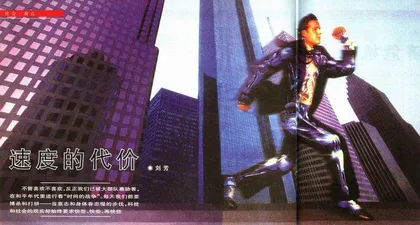
对人做修改,还是减速?
首次尝试超音速飞行的飞机遭遇过致命障碍——加速产生巨大的气压,大得几乎要把机翼折断。科学家们的解决办法是改进飞机设计,薄的、后掠型的机翼和流线型机身由此发明。
超越声障是物理问题,其原理却可解释社会生活中压力的来源和性质。日常生活的速度一天比一天快,人这架“飞机”遭遇的压力也一天比一天大,迟早有一天会超出它原先设计的承受力。到那时,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我们失控,要么飞机解体。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减速。可是,如果我们已经不能减速,或者我们自己选择了不减速,剩下的答案就只能是改造我们原先的设计,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新的速度。
“调整自身结构”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两片后掠机翼就可使飞机超越声障,可我们人又不是机器,我们有哪些部分可供修改吗?再说,如果压力不单是你我个中滋味,全社会都有同感,那叫社会怎样修改自身以适应新的速度呢?
提问的是美国作家斯蒂芬·伯特曼。他认为,人类对速度所做的调整将会改变生存的本质;快的社会,与过去不同的不光是速度,还有价值;压力本身不足以改变文明,怎样面对压力才是未来文明的决定因素。
伯特曼的新作《超速文化——人类为速度付出的代价》似乎就是他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从书名就可看出,伯特曼不太喜欢速度。他给“超速文化”开的方子也很简单——迅速、全面的减速。
陀螺越转越快,人越来越晕
1970年,未来学家艾尔文·托夫勒觉得美国社会得了一种病,他称之为“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照他的说法,当一个人被迫“在过短的时间内面对过多的变化”时,他的生理和心理就会陷入一种受冲击状态,简言之,“未来的冲击”。
托夫勒认为,科技和社会变化的速度已经快到了人们无法适应的地步。面对早熟的未来,大部分人难免“晕菜”,“除非人类学会控制个人和社会生活的速度,否则,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崩溃”。
《未来的冲击》问世30年来,社会变化的速度不但没有被“控制”,反而越来越快。旧科技革新,更新的技术问世,如今电子网络已使全球文化变成了整个儿的系统,目前对付速度的最好办法就是跟上它。
第一台文字处理器1970年才出现;第一张硅片1971年才问世;第一台个人电脑1975年才诞生;即便是1985年,100户美国人中有计算机的也只有8户;可是不到两年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1994年时,每3户美国人就有1家有电脑。与此同时,计算机的处理速度还在以每年55%的速度增长,电子邮件和因特网的诞生更是速度领域的革命性因素。
科技成果的合力之下,美国这只巨大陀螺越转越快。伯特曼声称此时人类的“飞机”正逼近“声障”,所以他呼吁减速,理由是社会对电子信息和娱乐的依赖性越强,我们每天的生活就越得跟上光速一般快的步伐,谁叫我们的经济和情绪都已经连在那个网上了呢。而且速度带来的惬意远不足以抵销它带给人类的巨大压力。
作家引用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证明这压力何等巨大。1986年一次调查表明,每3个美国人就有1个说他每天都感到有压力,每10个美国人就有6个说自己一星期之内有一到两次感到“压力巨大”。到1994年,每10个美国人就有两个说自己几乎天天都感到“压力巨大”。
另外,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家约翰·罗宾逊也发现,人们普遍越来越“赶时间”:1965年,25%的调查对象说他们每天都忙不过来;197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32%;1992年,宾州研究者乔弗里·戈德贝调查发现这个数字又提高到38%。最奇怪的是,调查表明,小镇里的人和大城市居民一样,都觉得自己忙,而且都说自己不仅工作忙,休息的时候也忙不过来!
过去5年里,美国关于压力问题的论文出了400篇,书籍出了900本,可见“压力”是个多么流行的话题,人们对此是多么无奈。
基于以上数据,伯特曼得出结论,“不管喜欢不喜欢,反正我们已被大部队裹胁着,在和平年代里进行‘时间的战争’。每天我们都要搏杀和打拼——当意志和身体眷恋慢的步伐,科技和社会的现实却始终要求快些、再快些。”
巴黎国防建筑学校的哲学教师蒂埃里帕科与伯特曼的看法不谋而合。他在法国《科学与生活》杂志中撰文指出:“城市问题将给人类造成很大危害,因为人类必须跟上城市的发展。城市是一个极为自由放任的所在,这里的竞争是无情的。”
科学家进行的各种观察可以证明这一点:越是大城市,生活节奏越快。爱尔兰科学家在进行了一项研究后指出,行人走路的速度也因城市的大小而有所不同:在爱尔兰戈尔韦这个有2.9万居民的小镇,行人走路的速度是每秒1.25米;而在都柏林这个68万人口的城市,行人走路的速度是每秒1.56米。
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环境实验室主任加布里埃尔·莫泽也说:“城市生活经常使人体防御系统处于戒备状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心理压力过大’。”《科学与生活》杂志甚至认为城市对人类造成的第一大伤害是城市生活的快节奏。
即时力量下的变色龙
速度已经成为现实,要跟上速度就必须“抓住现在”。可伯特曼觉得,“当‘现在’变成权威,一切就会被它吞噬。短期替代了长期,瞬间替代了永久,感觉替代了记忆,冲动替代了思索”。
像其他许多怀旧作家一样,法国作家菲利普·德莱姆的作品也流露着对速度的不满。他的散文小册子《第一口啤酒及其他微小快乐》连续畅销了60个星期,至今仍在榜上。书中内容其实非常简单,无非是小时候(也就是速度不可同日而语的时候)老派生活的种种细节如何美妙,比如清晨去买第一炉羊角面包,星期天中午家人坐在一起剥豌豆。
许多书评从中引申出关于速度的讨论。现如今,一切似乎都被“即时的力量(power of now)”改变了,即时的观念使社会流动,使万物缩短。那些需要漫长时间才能发展起来的技能和美德,比如心智成熟,深远的人际关系,精致的活儿,探求生命真谛等等,无形之中就被忽视了。
美国《未来学家》在总结即时力量时说:“它把人变成了变色龙,其颜色和状态随背景迅速变化,在时空间迅速切换定格,不断改变身体和大脑状态,它除了一个‘人造’的现在,别无长物。”
按照伯特曼的逻辑,现代社会的所有现象都能用“即时力量”来解释,从家庭解体、青少年早熟、老年人被社会抛弃,到快餐文化兴起、犯罪率升高,全是因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患上了速度病,都想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多。
作为社会批评家,伯特曼的著作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书评写道:“如果你总是没时间读书,那么,请你读读这本书。坐下来,慢慢地,细细地,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读后请与你生活中的人和你爱的人讨论。社会的脉搏正在危险地加速,请用伯特曼的手指帮你们诊断。”
如果你总是没时间读书,伯特曼这本书恐怕你也不会有时间读:伯特曼倒是对此悖论早有预料,他书中写明呼吁减速只是个人看法,因为“各种中间因素(个人的或社会的因素),都会使超高速的危害性影响发生变化。如果个人驾驭局面的意识强一些,危害源的威胁性就变得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