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真实,忘记真实:《回家过年》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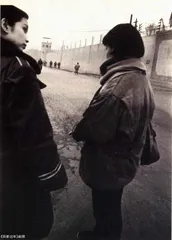
《回家过年》剧照
诺基亚手机在1998年最末一期的《时代》周刊上登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广告。一个年轻的中国电影导演端坐在录音棚里,他说:“……我的电影在中国很少能见到。我等了很多年,经过大量的努力之后,我的新片子终于能和大众见面了。当只有外国观众能看我的影片时,好在它还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对中国艺术、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理解。世界通过我的电影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
广告的立意在于最后一句话,而张元真正得意的是前面一句话——他终于可以和中国的观众进行沟通了。这位36岁的导演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他是新一代导演中拍片最多(同时也是违规拍片最多),在国内上映影片比例最小,在国外获奖最多,也最为西方媒体关注的一个。今年1月下旬,他的新片《回家过年》在天津封镜,他回到北京开始后期工作,而此间不少发行公司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
17年前,于正高和陶爱荣——一对各带一个女儿的再婚夫妇,经常为家里的小事拌嘴。于正高放在窗台上的5元钱不见了,二人都怀疑是对方的女儿拿了,大吵其架之后,提出搜身。拿了钱的于小琴很害怕,把钱偷偷放到陶兰的枕头底下,结果大家搜出了钱,母亲大骂陶兰。上学的路上,陶兰为自己辩解,于小琴说:“谁会信你?”陶兰气急之下,抄起路旁的一根扁担打向于小琴。于小琴死了。母亲害怕女儿给枪毙,让她给父亲跪下,父亲捶胸顿足,“是我杀了小琴,我为什么要娶你妈呀?”母亲哭了:“我害死了小琴,又害死了陶兰。”
17年后,在狱中表现良好的陶兰,按监狱法规定被允许回家过年。但没有人来接她,一位年轻的女狱警陈洁决定先送她回家,再回自己家。父亲、母亲和陶兰尴尬地坐在一处,父亲起身回屋。母亲把女儿拉过去,给父亲跪下,就像17年前一样。父亲劝女儿起来,让她们出去,说自己想安静一会儿……
问:怎么挖掘到这样一个故事的?它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答:整个构思起源于一个专题片,几个犯人在监狱门口,和家人见面的几个画面。我通过司法部门的安排,采访了不少监狱。当然,每个犯人都会有一个故事,这些边缘人的经历比外界的人要复杂。先请朱文和宁岱编剧,后来又请余华做了比较大的改动。
《回家过年》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人生悲剧,目前中国好像很流行喜剧,我希望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个人生悲剧,能给观众带来一些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和对往事的回忆。17年前,一个孩子被家庭推了出去,而今天,这个成年人如何回到自己的家里,她的母亲和父亲又是如何接受这个女儿的。这里面既有着一种非常扭曲的关系,但又包含着在极度状态下的人文关怀。
问:故事有一条单纯的线索,但剧情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是不是它仍像你以前的影片一样,用了很多纪实性的手法。不是编织故事,而是对准你要讲的家庭关系,比如角色说话也罢,不说话也罢,你认为这就是你想要的戏,而不管观众是否会觉得闷?
答:对于我来说,一切外加的东西都是多余的,故事对我来说应是完整的,像一个好的雕塑,从山上滚下来不会摔碎。没有任何噱头,没有讨好谁的地方。如果看这个家庭就去看这个家庭。
对我来说,有些商业片反而会显得很闷。因为我从中看不到生活的质感,看不到时间的流逝,看不到人与人之间流动的气氛,而我希望即使是框起来的画面,它也是生活。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电影越来越明显的商业化倾向?
答:现在的商业化更多只是一种炒作,我们的商业片还远不如好莱坞——尽管我并不欣赏好莱坞——不单指技术,比如好莱坞商业片的剧作至少都有很扎实的人物关系。不能老是比较轻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多作者化的东西。即便是好莱坞,也不只我们所引进的商业大片,它也有各种形态的电影。而这些电影对它的主流电影都起到一种推动作用,使它们更新换代。比如昆廷的片子当时看来很另类,今天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了。
问:国内观众一直看不到你的电影,那么在你心中,你的电影是拍给谁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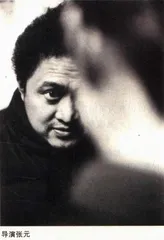
导演张元
答:过去我不知道台下坐的是谁。我的电影只能是拍给自己,拍给朋友,拍给欣赏我的人看的。这次面对国内的观众,所以我想(故事)感情要更饱满,更吸引大多数人。
问:这对你一直以来坚持的独立制片和作者电影的形态会有什么影响?
答:这部片子由“多种喜讯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400万资金基本上都不属于商业投资,我既是导演又是制片人。我不会放弃独立制片的方式和精神。我始终是在用我的电影去说话,说我看到的这个社会和我的想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个记者。
问:你最近拍摄了一个关于李阳“疯狂英语”的纪录片,听起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选题,你关注的是什么?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疯迷于学习英语,疯迷于集体地大声喊叫英语吗?
答:有趣就在于这个故事非常的荒诞。学英语用集体大声喊叫的疯狂方式,大家一起舞蹈;最大声、快速的方式。当然我最关注的除了这个学习方法,还有李阳这个疯狂的人,他的人生之路——一个过去非常自卑胆小的孩子是怎么成为这样一个不要脸的人;这个人的传奇故事同样使我深思。
问:你一直在拍纪录片,而且你非常强调纪录片的意义,纪录片在中国的缺失,那么纪录片究竟对你有何影响?就是真实吗?
答:主要是使我的作品保持了一种纪录本性,我认为这也是电影最本质的一个特征。其实我不只做故事片和纪录片,我还做话剧,做MTV,我尝试各种表现方式,但我希望我是在记录这个社会。我觉得我的拍片过程就是一个得到真实、忘记真实的过程——追求真实是我的一贯坚持,但忘我才会有真我,得到和忘记同样重要。
问:从刚才《回家过年》的片断来看,它和《儿子》的影片形态似乎更接近一些,在《回家过年》中你有意做了哪些探索呢?
答:在《回家过年》中,我更着重于时间的跨度,我描述一个家庭的故事,人性的脆弱之处,人如何被环境压倒,濒于崩溃之地,而人性又是如何复苏的。在我以前的电影中,我一直采用一种非常客观的视角,离观众比较远,比较冷;现在我希望这个故事能够直达观众。
问:这也许会有点矛盾,需要你用影片来阐释。拍摄中的难点在哪儿?
答:这部戏很悲切,也有很多激情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这次我用的全部是专业演员,我和演员的关系变得紧张而默契。
问:你是如何激发她们的?
答:我只能一遍遍地讲剧本。拍最后一场戏——父亲最终走出自己的房门,来到母女的房间,父女在一起的时候,三个人都流下了眼泪——当时所有在现场的人都被她们感动了。……这个镜头拍了很多条(次),每次都是这样。 父亲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