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与排行榜:从《更多的东西》到《盲人的恐吓》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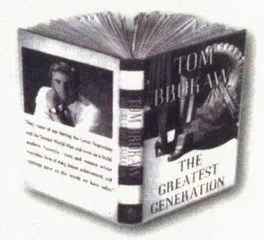
由于版面安排的原因,本栏目对非虚构作品排名榜及介绍自1998年第22期一直中断着。所幸,昙花一现的作品被略掉并不可惜,而真正的佳作必然依旧在榜,于读者只是信息迟到罢了。这里需要补充的只有萨拉·班·布莱思纳奇(Sarah Ban Breathnach)的《更多的东西》,该书忠告妇女要找到她们“真正的自我”,并尽量加以利用。
20世纪即将过去,因此回顾本世纪的著作纷纷问世。这一百年对全世界无疑有许多重大事件,然而对美国要以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震动最大。那10多年的时间堪称把美国划分成了两个时代。因此,《最伟大的一代》荣登榜首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作者汤姆·布罗柯是NBC(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主持人,1984年奉派前往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地区,为拍摄D.日(即二战中诺曼底登陆日)40周年的纪录片做准备。“当我和美国老兵走在海滩上时……我大为感动并深深感激他们所做的一切。”于是这次常规使命便成了他“一次生命转折的经历”,由此产生了写作本书的使命感。
30年代中成人的那一代如今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不但在战争中做出了奉献,而且战后又在各个领域里取得了新成就。当年美国为“孤立主义”所笼罩,囿于中产阶级一己之私的反对参战势力甚嚣尘上,二战的老兵首先都要冲破这道障碍,能够迈出家园国门已是非常之举。
战场上的牺牲自不待言,书中记叙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雷蒙德·柯雷新婚数月即奔赴前战,1944年6月牺牲于法国,年仅22岁。他的遗孀达芙妮再婚后生有子女,但她始终保存着一本叫作《永远失去的爱》的纪念册,里面有一页她写给他的十四行诗,他牺牲时那页纸就揣在胸口,上面沾满了他那致命的伤口中流出的血。那首诗中写道:“当你回到家中又属于我时,亲爱的,我可能已不再年轻貌美……”这50年的怀念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啊!
书中对参战部队中的种族主义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一位陆军妇女队成员玛莎·塞特尔·帕特尼至今愤愤不平地回忆说,当年在德梅因地区的战俘营中的德国军官应邀到要塞的驻军军官俱乐部消遣,而美军中的黑人军官却不得入内。
在提及那一代人的默默奉献精神时,作者提出,他们很多人都是带着终身残疾在战后又做出新贡献的,但他们从没有像越战老兵那样吵吵嚷嚷。“他们对他们为自己、为家庭和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有一种普遍的自豪感,但从不要求别人注意他们的奉献。”“他们虽然为他们取得的成就自豪,却绝少谈论他们的经历,即使在他们之间。”因此,作者能够四处奔波,采访乃至记下那么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为读者留下了难得的资料,此功确不可没。
《盲人的恐吓》一书对美苏两国在冷战期间潜艇间谍活动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进行了研究。作者谢丽·桑塔格为《全国法律杂志》(The National Law Journal)报道政府和国际事务,克里斯托弗·德鲁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在和退役的潜水艇官兵的交谈中听到了首次披露的间谍活动。后来又在安妮特·劳伦斯·德鲁和一位大胆的俄国同行的帮助下研究了前苏联一方的相关材料,才两相参照地写出了本书。
1953年上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现难以从他的情报头子那里获得棘手的高级战略情报,而他在欧洲战场任盟军最高司令时这样的情报却唾手可得。这说明俄国人比德国人在密码通讯上更加小心。他之后的美国总统当然也有同感。小詹姆斯·E·布莱德雷1966年时担任海军情报局水下作战处长,他灵机一动,为什么不对俄国人认为不可能窃听的电话电缆传输系统窃听呢?他想起儿时在密西西比河上看到的标志牌“电缆横越,切勿抛锚”,便推测俄国海岸也会有类似的警告牌竖在设有水底电话缆线处。于是1971年美国的核潜艇“比目鱼”号便把潜望镜伸出水面,悄悄潜入西伯利亚海岸证实布莱德雷的预想。潜水员把有史以来最大的电话窃听夹连到了鄂霍茨克海床的电缆上,有关苏联海军部署和军事演习的有用情报便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华盛顿。假如俄国准备好第一次核打击的话,这条窃听线就能提供关键的警告。这条最大的情报来源线足足使用了10年,直到1980年一个叫罗纳德·佩尔顿的美国人把这一秘密出卖给俄国人为止。
该书还插入了不少个人的惊险经历,使这部全面论述冷战时期美苏水下情报战的作品增加了故事性。在柴油动力潜艇时代,潜艇被迫时时浮出水面以补充氧气,这就带来了容易被发现并遭击沉的危险;核潜艇虽然可以一次潜伏数月之久,但艇员所忍受的不见阳光的生活也是难以想象的。至于1968年美苏各自发生的潜艇沉没事件,损失就更加惨重了。
校园里的野鸭
法国有份政治评论刊物名为《绑鸭报》,专评名人要人,言论非常大胆,可报社成员还总觉得话说不痛快,所以自嘲为被绑的鸭。
新年之初,《新观察家》周刊书评提到了一群不受捆绑的鸭,指的是学生办的刊物。法国大学生近年来办的杂志越来越多,从艺术到政治什么都涉及。这些刊物一改复印小册子的面目,都是电脑设计的卡通封面,也不再沿街叫卖,发行都在因特网上进行。
《迷宫》、《外围》、《唐·吉诃德》和《那又怎么样?》被《新观察家》周刊选作新学生刊物的代表。《迷宫》的编辑和撰稿人来自不同学校不同的系,他们集中探讨电影研究和诗歌翻译等非常专业的话题;《外围》的政治色彩浓重,以思考大学教育的意义为办刊宗旨;《唐·吉诃德》更注重现实生活,经常就某些看似很“酷”的社会现象提出问题,比如,在性用品商店,你寻找的是快感工具吗?当你找到了工具,你得到的还是你的快感吗?《那又怎么样?》是爵士乐杂志,《提词的人》是戏剧评论,这两份艺术刊物都很看重没名气的音乐家和作家,给他们发言和亮相的机会。
在成熟刊物眼中,学生办刊人是一群“幼兽”。可这些野鸭子叫得相当响亮。《那又怎么样?》和《外围》每期能售出2000份和8000份,《唐·吉诃德》更号称有30000份的发行量。它在两年之内做到30000份,今年5月的计划是达到50000份。
据《新观察家》报道,学生刊物从术给自己冠上“校园”二字,它们都当自己是企业来经营。《迷宫》杂志社的部门设置跟公司一样:编辑、印刷、销售、管理、校方联络处、媒体联络处等等。它们也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出版方面:《提词的人》设有戏剧奖,《外围》经常组织公众论坛。
操办文化刊物和文化事业让学生们获得职业经验,法国电影界目前最好的杂志《首映》有一位主笔评论员以前就在学生刊物《第7种艺术》做过9年。学生刊物的命运也取决于主要编辑的去留。这些热闹的学生刊物中,只有《提词的人》每年更新编辑部,其他刊物“临难”时的选择都很简单:放弃。当然也有少数刊物被毕业的学生带出校园继续办,《新观察家》说它们往往会失去校园的生猛味儿,“仿佛野鸭变成了家鸭”。
(刘芳) 唐·吉诃德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