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8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赵小帅 施武 赵爽 杜比)
花卷与蒜苗
文 赵小帅 图 王焱
在生活中我得到过许多劝诫,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我姥爷告诉我的一种方法论。那时候我上整托幼儿园,一周6天呆在幼儿园里,每到周日才能被父母接回家,因此,我一周要在幼儿园里吃十几顿饭。幼儿园老师教育我们不许浪费粮食,吃馒头、花卷时要吃完一个举手示意老师再上台领下一个。实际上我不记得有谁曾浪费过粮食,倒记得常常是举手示意后发现装馒头的笸箩已经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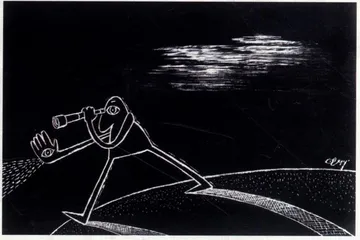
我姥爷教给我的方法论至为重要,他说,你上去第一次领花卷时要挑一个小的,第二次去领时还要挑一个小的,这样你能比较快地吃完两个花卷,第三次去领花卷时就要挑一个大的,慢慢吃,这样你就能吃饱,反过来,你一个大的先吃,第二次还吃大的,那么你就没机会吃第三个花卷,因为在你啃两个大花卷时别人已经捷足先登了。
我不记得这方法是否保证我在幼儿园时顿顿能吃到3个花卷,但我铭记在心的是这方法是劳动人民的智慧,虽然它没有考虑到我吃两个小花卷时别人是否已经把大花卷全都抢走了,这需要一个数学模型,初等数学就够了。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你可能对我的身世有个判断,不错,我出生于平民家庭,吃不好饭的记忆很深刻。下面我要讲另一件事,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世界观。
有一次,我父亲的一个老同学到我家做客,中午一起吃饭。那天我买了两毛钱的肉和一斤蒜苗,做了个肉炒蒜苗,这道菜我们家一般是过年才能吃到,所以那天在饭桌上我表现得相当不理智,不仅抢着吃蒜苗,而且嘴中念念有词,说这蒜苗真好吃,要是天天能吃就好了。
如你所料,那天客人走了之后,我父亲把我教训了一顿,说我不懂规矩等等。我对于方法论接受较快,世界观则需要慢慢形成。我后来总结我父亲的意思,那就是即使你没吃过蒜苗,当着别人也要做出 一副你吃过的样子,这涉及别人如何看待你,你要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的问题,我相信这是一种世界观。
如今,花卷和蒜苗都不是什么稀罕物了,但吃饭依旧是个大问题,这里所说的“吃饭问题”是广义上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混碗饭吃”,怎样才能混碗饭吃呢?那就要做出一副你吃过蒜苗的样子给人家看,伸手拿过来一个小花卷,同时眼睛紧盯着那个大花卷。
春儿,你好吗?
施武
人无完人,这个事实我知道,之所以还不至于为这世界为自己感到悲观,因为我还知道人各有所长的道理。幼儿园老师早就讲过骆驼和小羊的故事,《巴黎圣母院》里还有心地善良的卡西莫多。
所以我们要看乔丹打篮球,要读苏格拉底跟人辩论的篇章。苏格拉底尽管聪明过人,但有一点他没掰清楚。他在论证自己应该参加选美时说,他有大翻鼻孔便于呼吸,他有大厚嘴唇便于接吻,外凸的眼睛便于观物。也许这只是笑话编排他。按他的智慧他不该这么苛求观众如果他有道理,也太功利主义地对待人这张脸了。
另一种苛求观众的做法是让身体有残疾的人上台跳舞或上运动场赛球。其说辞众所周知,表现残疾人自强不息,身残志不残的精神。我偶然在电视里看到过几次,总是很难接受,锁住频道多看几眼以后就觉得那说辞有点离谱。人各有所长,所以理应发挥展示的是长处。至于短处,你有我也有,犯不着非叫乔丹去跟苏格拉底辩论,辩输了,再说你看乔丹虽然没苏格拉底聪明,但他志不短;或者让卡西莫多去参加选美,然后说他虽不够美,但有自尊。这不是自尊,是不够有自知。至少是不好看,没准还有点残酷。当然这类比赛设定的是乔丹和“乔丹”辩论,卡西莫多和“卡西莫多”比美,可这比出的结果并不说明什么。
更令我不解的是,很多电视镜头对准了一个患先天愚型的残疾人。他本是出于善意在个商场前学学模特猫步走场,出于本性学着指挥大师挥舞指挥棒应该让他安宁地度过他不幸的生活。让电视来扩大他的观众群,也许他对这效果不能自省,可是拍摄者不该毫无感觉吧。我如果是这孩子他妈,我不让拍。
要说身残志不残,我觉得霍金的努力更有说明力,他身体病残了,他就不跟身体较劲了,他跟脑子较劲。还有我小时候住的地方有一个在工艺美术厂工作的男孩子,他几乎不能走路,驼背,但是他在那个厂是有名的好手艺。那个工厂专做牛骨雕刻,学徒时先学素描,他比谁都画得勤,后来他的活儿比谁都做得好,他也跟邻居孩子一起玩空竹,他在朋友结婚打家具时,帮人家雕了一个“红色娘子军”的吴青华。我记得他的小名叫春儿,不知他现在怎样了。
阉猫
赵爽
我小时候干过一件蠢事。当时我正上小学,家住平房,房后的窗户对着一片半荒的空场。附近的猫都很喜欢到那里去玩儿,我也喜欢趴在窗户上看它们。有一次我发现有两只猫摆出了一幅奇怪的剑拔弩张的架势。我以前见过两只猫相互恐吓的阵式,但并不是这种样子。正好我那时在写什么“科学小论文”,我就把那天看到的一切作为猫与猫之间发生冲突时的一种体态语言写了进去。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当年我很不好意思地看了半天猫的私房事。
类似的蠢事我还干过一件。那也是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的猫一到某几个月份就整天扒着纱门闹着要到院子里去。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闹春”,反倒是在交给老师的一篇很传统的描写春天的作文里对小猫也如何被春天的红花绿草吸引大抒了一番情。
后来我毕竟长大了,对猫的方方面面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其中也包括“阉猫”这档事。我第一次知道这个词时的印象并不好。那时我有一个同事家里养了三四只猫,因此常常会多出一窝窝小猫。那天我去他家问他妈现在是否有多余的小猫给我,他妈妈的回答是:“没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我把它们都骟了。”随后是“哈哈哈哈”一串大笑。我知道这个同学的妈妈是校医院的外科医生,我并不怀疑她的手艺,但我还是觉得她那种笑声很像个巫婆。
后来“阉猫”这个词我见得越来越多了。其中一次是在一本新近出版的宠物周历上。本周历的印刷与装帧都很精美,从头到尾在强调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文字间还穿插了不少类似温馨情调的小插图。在讲述养猫知识的一章中,继介绍完如何照料、喂养你的小猫咪后,编者甚至没有忘记提醒你到一定时候要及时阉猫。在一幅表现一群活蹦乱跳的小猫咪的漫画上方,编者还保证“阉过的小猫咪将更加健康、可爱、活泼”。此后不久,我又在街边看到了一块招牌上方写着“小动物健康保护”,下方以同样大的字号写着“阉猫”。
我对猫的健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总是在感情上不太接受得了这种事。如今我更怀疑小学时另一个同学家里的一只大母猫。按照人类的道德标准,这只老母猫很“不要脸”:它天天在外面闲逛,一旦回家肯定是肚子大了;下完一窝小猫,身体恢复后它就又出去闲逛,直到下一次又大着肚子回来。不过我们当时都很喜欢这只母猫,因为它能提供给我们一群虽然不纯种,但是够可爱的小猫。相比之下,如今的猫咪真是可怜:本来外出活动的机会就少,出去一趟还未必有什么结果。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想法是否有理。当然,我承认我从来不是一个很会善待猫的人。前后曾经有6只猫与我朝夕相处,结果每一只都被我欺侮过。不过,我也始终为一点自豪:我们家从未对任何一只猫动过其他手脚。
(本栏编辑:苗炜)
怎样做一个高雅的人
文 杜比 图 王焱
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格调》,作者是个美国人。他讲述了美国各阶层人士的生活特征,比如中产阶级穿衣服整洁而贫民阶层喜欢穿名牌;比如中产阶级最爱看《国家地理》杂志而贫民阶层的家里老摆着《读者文摘》合订本;比如上等阶层总是开一辆半老不新的雪佛兰而下等人士不管开什么车都喜欢在车里挂上一大堆小饰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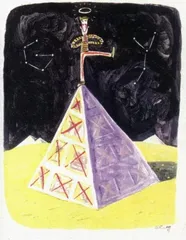
尽管这本书讲的是美国人,可我读过之后忍不住要和自己的生活对照一下,因为这本书叫《格调》,这里面包藏祸心,英文书名中Class,应是阶层的意思,翻译过来却成了格调。一个人生活在什么阶层是挺难改变的,但一个人要是没有格调就比较麻烦。我这人生活虽然粗鄙,但却一直没有放弃做个高雅人士的梦想。
对照的第一步还好,我家里没有《读者文摘》杂志,这表明我不是平民阶层。第二步就有问题,书里说,下层人士总把电视机放在房间显著的位置,没事儿就爱看电视,而我家的电视的确就处在显著位置,我按书中上等阶层人士的做法把我家的电视扔在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并决心以后尽量不看电视。书中说,上等阶层有游艇,下等阶层爱打保龄球,我庆幸自己绝少打保龄球,体育锻炼方式是慢跑。可书中说,下等阶层总爱穿名牌标识醒目的衣服,还爱戴棒球帽,坏了,这正是我慢跑时的标准打扮。
这样的对照略显无聊,因为我要是买一辆汽车的话绝难做到买一辆二手车,给人一副上等阶层的感觉,倒是宁愿来一辆张扬的“宝马”,哪怕被说成是暴发户。这样对照的结论是:下层人士永远仰慕上层生活。
以我的经验来看,以美国标尺来对照我们的生活,这玩艺儿有绝大的影响力。我有一朋友抽烟。我们劝他,抽烟有肺气肿肺癌的危险,他不听,不戒烟。我们再劝,抽烟影响性生活,他不听,不戒烟。再后来我们说,美国人很少抽烟,美国穷人才抽烟,他听了立刻把烟戒掉。一个人可以不管自己的肺和性生活,却不能不管美国,后来这孙子听说美国富人抽雪茄就又抽上雪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