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7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翁树杰 周树平 周正 刘吉 黄福满 陈文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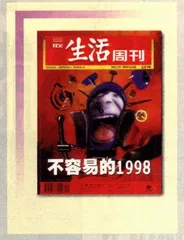
据我所知,贵刊是第一次这么全面地作年终回顾。我想说的是,各类报刊形形色色的回顾,都是以时代进程、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坐标,见不到以老百姓在年度内的生活作为回顾的起点。贵刊也没能例外。
北京 翁树杰
再谈大学特困生
贵刊第76期的《读者来信》栏里有一篇关于大学特困生的文章。文中作者提醒大家不要被特困生的眼泪所蒙蔽,即“看问题不能表面化”。并且列出了一二三,作了“深入分析”。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的普通大学生,我想就文中观点表达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原文的作者在“第一”里说“超生是产生大学特困生的重要原因”。这一点也许我不能反对。但你想怎么着呢?超生是谁造成的?总不是大学特困生吧!既然说原因,我也很想谈一下一个很根本的原因: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的重视不够。我们是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社会主义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老大哥”,对工业的偏重也算是学到的一手了吧。美国的农业每创收1美元,国家花在上面的投资是3美元。我国农业创造的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而国家对农业的投资仅及其产值的3%。
第二,作者在“第二”里说“既然特困,是否一定要上大学?”我不知道作者对中国农村了解多少,更不知道他哪里得来的这个“一定”。我们班上有30个人,来自农村的只有6个。把这个比例与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比例比较一下,我想那位作者就不会认为是这帮乡巴佬在厚着脸皮往他们的安乐窝里挤了。毕竟,农民进城除了给人家盖房子,看孩子,上学也不犯法吧。
第三,作者在“第三”里,很鄙夷地置一句:“上大学不交费?”我怀疑是否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像是黄世仁到了杨白劳家里,看见了老头儿没有办法盖上的空米缸,翻着白眼儿,擦着鼻孔:“你敢不交租?”
如今,一些话题常被打着各自的主意和旗号的人“炒”歪了。被“炒”的往往就成了耍猴人手中谋生的工具,电视台的贩灾义演成了商家广告大战的舞台。临了,权作广告费的赈灾款竟可以赖着不交。大学特困生不可避免地也成了一只猴子,在一声声鞭子的炸响中胆战心惊地上下乱窜。当然,这一点上不宜多谈,免得引起大多数真正想帮助这些“动物”的人的误会。
我没有该文作者的才华和笔锋,只是感性地从一个大学生的视角表达一下我对原文的不满。希望大家说话之前要多了解些实际情况。
北京物资学院96211班 周树平
“数字化”时代
山东泰安河西村村委大院新设“孝心榜”,为督促子女行孝,该榜条例清楚,各户子女行孝的每月赡养费用罗列其上。据说效果明显,泰安市准备大力推广。
我顿觉大开眼界,原来孝与不孝是可以用赡养费额之高低来作明确衡量的!因为该村还以行孝费额划分孝顺之等级,这的确是个“数字化”的时代了。
我不禁突发奇想,建议河西村委再设一块“爱心榜”,同样罗列内容不同的费用——为父母者为子女所费钱数,不知是否也能引起轰动,倘若效者云集,不妨依次类推忠心者忠诚如何所费几许,榜上排名,准保按爱国程度可以依次排至第12亿名,秩序井然,数字为证。“忠孝与否榜上看,有心无钱莫上来。”
据此,像那些穷乡僻壤只能“酸溜溜”每天为老母亲倒上一盆洗脚水的子女一律靠边站,洗脚水几钱一盆?你给钱了么?小山沟的穷教师天天喊破了喉咙也没有用,希望工程有你捐的款吗?
这些榜要真立起来,定将成为我们新的国粹,所谓“时代金钱化,人情数字化”只要吆喝一声“将榜来,取前三名!”——多省事!
南京察哈尔路37号 周正
亏本诉讼不值
读者高河垣在北京中安天平图书中心(以下简称图书中心)购买了一本《走向法庭》,回去一看,发现该书严重缺页,就乘公交车到图书中心要求退书并赔偿因退书往返乘车而花费的1元钱交通费。图书中心同意退书而拒赔1元钱的交通费,为此,高河垣起诉到法院。
看到这里,颇使人欣慰:经过20多年的法制建设,法律观念深入人心,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成了人们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并且通过诉讼,能体现社会正义与公平,实现法律的社会效益。
可后续报道却不那么令人轻松:高河垣在一审诉讼期间花费了住宿费、交通费807元;因图书中心不服上诉,二审诉讼期间又花费住宿费、交通费412元。最后的判决还没有下来,可为了这1元钱的争议,高河垣仅住宿费、交通费就有1219元,还未包括误工等其他损失。而图书中心、审理该案的两级法院的投入也不会在高河垣之下。这不由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法律的经济效益上。
效益的获得,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必需的。但效益的最大化,要求人们以较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知识等)的耗费。这个案件的实际“产出”是1元钱,可诉讼成本(双方当事人及法院为解决这一争议的投入)仅一方当事人所投入的就在1219元以上。这样严重失衡的投入产出比,我想是任何一个人所不愿看到的。
这类忽视经济效益的法律(包括诉讼),即使有一定的社会效益,其效益也是值得怀疑的,毕竟产出的无效使得巨大的投入变得毫无意义。对这类事件大加宣扬,牺牲实际效益以换取社会效益的做法对民众有太多的误导作用,说到底它有愚民的趋势。
西南师大经济政法学院 刘吉
广场鸽的死亡
北京当代商城门前的广场鸽被人一朝之间毒死大半,市民们群情激昂,一群鸽子成了市民良心的见证。
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的脑子马上就联想到曾经看过的一个香港电影录像:演员午马扮演的一个老人生活在伦敦,开了一个粤菜餐馆。粤菜里有一道名菜就是烧乳鸽,我不知道“乳鸽”指的是什么鸽子,但是电影里午马每天提着鸟笼来到一个有鸽子飞翔的广场,打开鸟笼,等着鸽子走进去进食就把鸟笼关上一走了之,回头端上来的就是一盘油光闪亮的乳鸽。
毒死当代商城广场鸽的坏人没有午马那么实际,他(她)也许想泄一下私愤,或者仅仅是为了看到一片死鸽子躺在广场上的残酷场面。我敢打赌别人为死鸽子难过的时候,凶手一定站在旁边悄悄地看着。
我还听说前些年一次从北京出发的信鸽竞翔大赛一开始,一群“猎人”就扛着猎枪等在京郊某地展开了一次射击大赛。这个传闻就跟午马的电影一样,更多的是对生活或人性的幽默。
对于“当代”的广场鸽,我想说的是:很难保证在一群新添进的鸽子又飞翔在商场的高楼与人群之间的时候,我还会想起这些死去的鸽子。我们突然从一群死去的鸽子身上发现自己对一些美好的东西还存有良心,而这股良心也像鸽子的死亡一样显得突然,有点意外。
北京魏公村 黄福满
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先生死了,告别我们的方式和他的遗愿一样简约。
我从书柜中翻出大学时候买的一本《管锥编》,试图从里面找出点什么。但像我在读中文系时的情况一样,以我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很难从中读懂更多的东西,这一点我觉得有些对不起钱先生。
大学里我就读的中文系在古汉语小学研究上是全国有名的。上《说文解字》课的时候,老师说他的老师陆宗达先生研究了一辈子《说文》,有一次竟然为了忘记某个解释在《说文》的具体页码而急得直敲自己的脑袋。虽然作为一个学过古汉语的学生我是一个不肖弟子,但听完老师的叙述,依然对陆先生充满敬畏。当时陆先生也已离开人世。
现在我所在的城市是一个经济特区,我从事的职业也与先生们苦做学问大相径庭,钱先生的去世让我想起了当年在课堂上老师讲过的那段故事。钱先生、陆先生研究的内容、做事的方式对我现在的生活不会产生更多的影响,也许这是时代的变化吧。
一代人一代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永远都会被提起的话题,我成年之后走进了自己的生活,有机会我想自己会读一遍《写在人生边上》,看一回《围城》电视剧。
深圳蛇口 陈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