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软件的失乐园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胡泳)
Linux与freeware
Internet现在堪称酷中之酷,但网络上最酷的人名归谁属呢?先别往比尔·盖茨那儿想!《福布斯》最近对网民的一次调查披露,网络上的头号偶像是28岁的芬兰小伙里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紧随其后的是45岁的美国人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季军则被万维网的发明人、43岁的蒂姆·伯纳斯一李(Tim Berners-Lee)夺走。盖茨也算挤入了前10名,不过位居第七。百万富翁们虽然万贯缠身,但在酷的刻度上却似乎比黑客和技术天才们差了不止一个等级。“网景”的马克·安迪森和“太阳”的斯科特·麦克尼里只占了第九、第十把交椅。
网民对冠、亚、季军的鉴定如下:
托瓦兹,Linux操作系统的发明者:他发明了一种比“微软”的任何产品都好上一万倍的免费操作系统。难道还需要再说更多的话吗?
斯托尔曼,自由软件基金会创始人:没有他的共产主义理想,网络上的公益事业将没有立足之地。他的自由软件(freeware)概念领先了这个时代整整15年……
伯纳斯—李:这位梦想家把信息的力量带给了全世界。当我们为早期电子商务的新大亨们欢呼时,可曾忘记新媒介的创始人?
似乎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句老话。同为哈佛学生的斯托尔曼和盖茨在70年代初几乎同时涉足计算机软件业,盖茨的故事后来尽人皆知,全球首富的金冠光耀世界,而斯托尔曼却像一个孤独的、不合时宜的斗士,其自由软件的梦想似乎注定要湮没在命运的尘埃中。斯托尔曼自称是麻省理工学院黑客神话的直系继承人,他至今难忘当年在人工智能实验室里通宵达旦地操作计算机的情景。一群才华出众的学生对解决难题充满了由衷的热爱,擅长抓住瞬间的思想尽情地发挥。那是无忧无虑的伊甸园时代。堕落(斯托尔曼称之为“污染”)始于1981年,一家叫做Symbolics的公司雇走了实验室的大部分黑客,他们不再创造自由软件,而是制作商业秘密,将其藏于深闺,待价而沽。
在离斯托尔曼心爱的实验室不远的地方,盖茨和他的伙伴保罗·艾伦利用哈佛的计算机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牛郎星”设计了操作系统。有人将其拷贝散发给众多的电脑发烧友,这在当时软件共享的气氛中是十分正常的——程序员喜欢互相“借用”软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盗版”这个词。但盖茨的想法却与众不同,他写了一封广泛传播的“致软件爱好者的公开信”,要求发烧友们停止盗用软件,这样软件设计者才能赢利,只有获得赢利,才能生产更好的软件。“谁能从事专业工作而不计图报呢?”
企业家盖茨想不到的是,有人能。盖茨最终在个人计算机领域大获全胜,但斯托尔曼也没有不战而降。1984年,他开始致力于开发一种与Unix系统兼容的名为GNU的免费软件,这种软件的部分内容对Linux的运行起了关键作用。在推出GNU的同时,斯托尔曼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以推广自由软件。
什么是自由软件?它不仅仅意味着自由分享,而且更重要的是,任何程序员都可以对它进行自由的改动和完善,因为它的源代码是开放的。商业软件通常总是以二进制数字——即1和0——的形式发放,微处理器识别起来毫无困难,但即使是最高明的程序员也无法读懂。你得花钱购买软件,有时也可以免费下载,而无论是哪种方式你得到的都只是1和0。开放源代码软件(OSS)与此不同。源代码披露了程序写作者所下的指令,其他人因之得以了解写作者如何编码,并洞察他/她的真实意图。商业软件的源代码是严格保密的,要靠其带来滚滚财源;而自由软件的宗旨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奉献自己的思想,每个人的贡献必须公开源代码,允许其他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工作。这样,软件可以集中多人的智慧,从而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Linux正是一种自由软件。它是软件开发史上的奇迹,由托瓦兹一个用户发展到现在的750万用户;众多软件高手不断为之添砖加瓦,数年之间,软件已由1万行代码扩展到150万行,成为一个光芒四射的伟大产品。
因特网十大排行

3月的时候,“网景”公布了它的网络浏览器的源代码,这表明主流厂商开始认可自由软件背后的指导思想(当然这也预示着“网景”放弃了在浏览器市场上与“微软”一决雌雄的打算),即软件开发要以公开源代码为手段吸引尽可能多的开发者参与软件的查错与改进。“网景”公布源代码后仅数小时,几位澳大利亚程序员就为浏览器添加了一种加密功能,用以保障网络交易的安全性。在接下来的两周中,其他修补健议从世界各地如潮水般涌来。不到一个月,浏览器的一个新版本就出现在网上,等着用户下载。如果“网景”按照传统方式斥巨资、组人马开发新版本,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获得同样的成果吗?大约很难。
典型的商业软件的新版本通常都是一年一发布,“微软”的视窗是3年一发布。但像Linux这样的开放源代码软件常常每个月都能在网上得到更新。随着网络的扩展和应用的多样化,能够不断改正错误、适应变化的软件将不仅仅给用户带来方便,而且会成为用户的第一要求。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英特尔”与“网景”联手,共同投资Red Hat软件公司,它的主要产品正是Linux。各色软件开发商,甚至包括“微软”,都纷纷表示要支持Linux。Linux风潮也进入了国内。四通公司、华胜公司、中网公司都推出了基于Linux的服务器和应用系统。中国软件协会自由软件分会也宣告成立,并创建了中国自由软件库的网上站点。在主流之外徘徊了几年的Linux已迅速成为电脑行业的新宠。自由软件的思想借此势头也开始深入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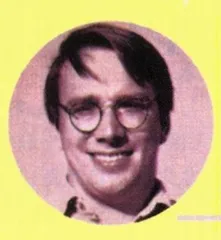
托瓦兹:Linux操作系统的发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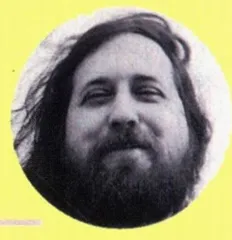
斯托尔曼:自由软件基金会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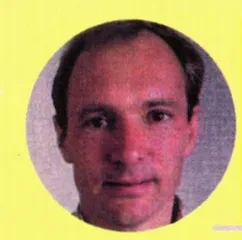
伯纳斯—李:梦想把信息的力量带给全世界
The Hack
托瓦兹和斯托尔曼尽管声名鹊起,却买不起4000万美元的房子。有些厂商认识到Linux的商业应用前景,试图将其予以商业化,而斯托尔曼则怒斥这样的厂商为自由软件的寄生虫。那么,到底什么是托瓦兹们工作的动力呢?托瓦兹自称他为软件编程中的“艺术因素”着迷。你可以在一周内学会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然后除了等待系统失灵或瘫痪以外就无事可做了;Linux的带劲之处在于:一周仅仅是个入门,随后你的野心和创造力可以任意驰骋。
不过,似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激发着自由软件精神:自由软件已变成了某种智力上的奥林匹克竞赛,世界上的顶尖编程高手在此激烈角逐——不是为了争夺风险投资,而是为了成就软件上的技术飞跃,行话叫做“The Hack”。它是黑客文化中的圣杯。
什么可以称为“The Hack”?它似乎生而具有某种神秘色彩。说明解释它的最好例子是约翰·德雷普即“嘎吱嘎吱船长”(Captain Crunch)的故事。德雷普是一名擅长盗打电话的电话飞客(电话飞客正是今日电脑黑客的前身),他偶然发现以Captain Crunch 为名的麦片盒中附赠的哨子(这是为了鼓励消费者购买而特设的奖品)有一种神奇的本领:把它对着电话听筒吹,哨子的音调会使中心电话线路自动接出一根长途线,因为这个音调的频率是2600赫兹,与60~70年代电话交换系统本身的信号声频完全相同。德雷普靠吹哨盗打电话数年,他最有名的把戏是“环球电话”。他在加利福尼亚的一间屋子中安装了两部电话。利用一枚哨子和他对国际长途电话线路编码的丰富知识,他拿起第一部电话拨打第二部电话,通话线路自加利福尼亚开始,辗转经过东京、印度、希腊、比勒陀尼亚、伦敦、纽约,又回到加利福尼亚。这样,他对着第一部电话讲话,20秒钟后却在第二部电话中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Hack”。第一,它用异常简单的办法获得了令人惊叹的结果。第二,同样重要的是,德雷普并非偶然遇到好运气。他能够发现哨子的功用是因为他已积累了有关电话系统的大量知识。这是他的把戏成为“Hack”的关键所在。第三,黑客活动需要的知识完全是通过非正式的途径获得的,并且以牺牲一个庞大系统的利益为代价。
黑客对于“The Hack”的沉迷外人难以想象。让我们来听听另外一个故事。今年4月,IBM以其万金之尊不惜低声下气向名不见经传的“Apache小组”求欢。该小组是一个由20位程序员组成的松散联盟,说它松散还有点高估了它:小组成员从帕洛阿尔托到慕尼黑分散在世界各地,既没有形成公司实体,又不受任何合同约束。但这些人开发出来的软件却可以作为IBM电子商务软件的基石。IBM 所孜孜以求的伙伴关系听起来非常奇怪:合作过程中不牵涉到任何钱的事情。与一个没有法人身份的共同体签定一份不计金钱的许可证协议……IBM老于世故的律师们惶惑了:“难道我们在与一个网作交易?”不错,而且这一网站规定了交易条件:软件的源代码——即律师们被雇来全力保护的知识产权——必须对网上所有人开放。不管IBM是否喜欢,它都得接受这样的条件。20位程序员还不太情愿把软件交给IBM。怎样才能向他们表达IBM公司的诚意呢?最终,这个巨人拿出了Apache小组唯一感兴趣的“硬通货”:The Hack。IBM的程序员们发现了让Apache的软件在“微软”的NT系统上运行得更快的方法。他们提出向Apache 小组传授这一方法,并保证在将来分享类似的发现。Apache的黑客们于是欣然与IBM达成协议。黑客常挂嘴边的说法是,他们不需要为了得到法拉利而去编程,驱使黑客向前的,是推动技术发展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感觉。
年轻的托瓦兹像所有风华正茂的黑客一样,喜欢谈论黑客活动的艺术性。艺术家占有媒介,但也往往被媒介所占有,无疑,在这个意义上,黑客是可以称为艺术家的。但年长的斯托尔曼则似乎拥有一些更富于哲学意味的想法。他在《GNU 宣言》中写道:长远来看,自由软件将是迈向一个新的世界的一步,在这个世界里将不再有匮乏,人们不必仅仅为了谋生而努力工作。他们将花费一定的时间从事必要的工作,此后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编程。“我们已经极大地削减了社会提高实际生产力所需的工作量,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转化为工人的闲暇,因为有效率的活动必须伴以许多无效率的活动。它是官僚主义和反竞争的产物。自由软件将会在软件生产领域极大地减少这些内耗。为了把科技生产力转化为更多的闲暇,我们必须推广自由软件。”
但是,Linux代表的自由软件能继续坚持自由精神与商业环境对抗吗?自由软件变酷之日,也许就是它变俗之时。在《机器的灵魂》一书中,特雷西·基德讲述了一群公司年轻人如何忘我地设计并建造了一种新型计算机的故事。书名中“灵魂”一词的选用别有深意。在制造机器的日日夜夜里,这些年轻人几乎过着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所有世俗的杂念一概抛弃,自我意识和个人图报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任何位置。然而,当机器最终“上市”后,他们的奉献一文不值。
公司著名的销售队伍被带到这种新型计算机前。在展示会行将结束时,销售经理起立向他的下属训话。“人们的动力何在?”他问,随即自己回答说:“动力在于自我意识和金钱需要。”现在游戏完全不同了。显然,机器已不再属于它的创造者。 程序员网景黑客文化linux服务器ibm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