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米之炊:台湾电影的困境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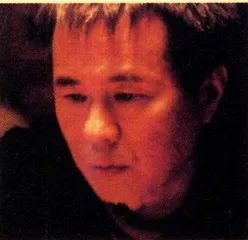
台湾导演候孝贤
台湾导演蔡明亮的新片《洞》,在10月份的芝加哥电影节上赢得头奖,然而这部影片在台湾的影院里却几乎看不到。短短几天放映之后,它就被《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好莱坞重磅炸弹所取代。而《洞》是今年参加戛纳影展仅有的两部亚洲电影之一(另一部是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海上花》)。这位曾在威尼斯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获得过大奖(《爱情万岁》和《河流》)的新锐导演当然有理由抱怨说,他在台湾的影迷肯定比那些放映商所想象的要多。
随着逐渐增高的制片费和越来越少的投资者,台湾导演真正担忧的是能否为下一部影片找到资金。80年代以来,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赢得了国际声誉,台湾当局意识到这也是提高台湾知名度的一种方式,于是由“新闻局”设立了专项的“国片辅导金”。而今年作为第9个年头,数额达1.2亿元台币(360万美元)的辅导金,竟对几近半数的台湾影片都产生了影响。蔡明亮的《洞》得到了1000万台币,另外的1800万来自一个法国电视台。侯孝贤的大制作、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海上花》,也从中得到了1000万台币。
“问题在于日本人或欧洲人是否对你有信心,”侯孝贤说,“正是因为这两个市场我还能继续做电影。”日本最大的制片公司东宝公司为《海上花》投资7000万台币。而影片的最终预算至少在1亿台币以上,侯以自己的房子作抵押来取得更多的贷款,他还欠着影片男主角、香港影帝梁朝伟一笔薪水。这部描述上个世纪上海青楼生活的影片,在台湾上映两周,只得到了400万台币的票房,海外放映的压力无疑变得非常巨大。
这几位导演对台湾电影的前景十分担忧,但他们并不想按有的批评指出的那样,制作一些本地观众爱看的电影。他们认为,造成目前情形的原因在于好莱坞的入侵和放映网的唯利是图。比如说,低质量的电影院是年轻一代不爱看电影的主要原因。80年代以来,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等片生动描写了台湾乡村生活和台湾历史,不仅在国际影坛受人瞩目,也吸引了一批坚定的本地观众(但他们现在年纪渐长,不看电影了)。“现在你要做一部大制作,你必须有一批大明星。而我正在走一条孤独的道路。我知道票房不可能好,但我不可能改变我的风格。”
《海滩的一天》、《恐怖分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独立时代》、《麻将》……另一位有国际声誉的大导演,以审视台湾现代社会的知性导演著称的杨德昌,也承认他早已放弃关注台湾市场。原因之一在当地的发行公司,“他们掌握着片源,你没法和他竞争。他们有时出于尊敬放一下你的片子,但我们被骗好多次了(指在放映档期、收入分配等问题上)”。杨是少数不花官方钱的台湾导演之一,他依靠自己的商业头脑,“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只靠编故事是没法生存的。每拍一部电影都要趟一条新路子来找钱”。
令人奇怪的是,不只艺术电影在受苦受难,所有华语电影(包括香港的动作片)在台湾都没有好收入。朱延平(《异域》),台湾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现在正为电视台拍片。去年在台湾,华语电影的票房收入只占总票房收入2亿台币的9%,仅在5年前它还占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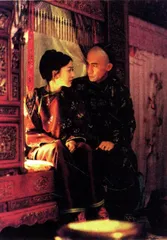
侯孝贤今年的大制作《海上花》主要由日本投资
事实上,台湾电影正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打击:观众不爱看本土电影,投资方也不支持本土电影。台湾最大的制片公司——中央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资深人士说:“我们处在一个糟透了的环境。台湾有足够的钱,但这些资方不了解电影业,他们总是急于在短期内收回投资。如果你告诉他们这个电影能在欧洲赚点钱,他们会问为什么他们要为此投资。”台湾电影的经济萧条始于80年代初期,一部普通故事片的制作费是2000万台币(60万美金),而此前20年的费用是3000万~5000万台币。尽管如此,也尽管票房只能收回一小部分,但通过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的发行播映,这些费用最终总能收回。
商业上的繁荣期在70年代,那时台湾年产电影100部以上,多是言情片和政治宣传性的故事片。但在80年代初香港动作片纷纷涌入占领市场,80年代末不再限制资金流通时,台湾资金就先后涌入了香港和内地。最大的打击当然来自90年代的好莱坞,它使美国的投资、制作方和台湾的发行、放映商大赚其钱,而电影、电影人和观众都受到各自不同的损害。如今台湾年产电影20~30部,并且情形越来越糟——台湾电影已越来越依赖于“辅导金”。而1999年,台湾当局将从近百个投标剧本中仅选择12个导演,每人赞助500万或1000万台币。
似乎自由贸易使得全世界的本土电影都陷入危机。套用一句话,台湾电影的危机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而现在终至无人能解之境,是好莱坞、本地企业、电影人、官方、媒体,包括观众共同“努力”的结果。 台湾香港海上花侯孝贤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