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和现代药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君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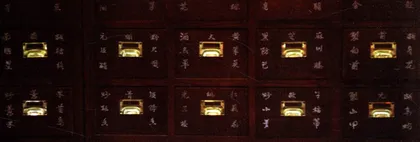
连创可贴都做得这么漂亮
如果时间、地点合适,李欣和他那个贴了新式创可贴的脚指头肯定会引领一股潮流。午饭后,李先生照例去他所在的北京欣诚咨询公司附近的一家体育馆游泳。出来的时候情况有点不妙——他的脚趾被泳池底部“不明硬物”划伤了。他拖着受伤的脚进了办公室,掏出刚从药店买来的创可贴。在开放办公地点脱鞋和袜子是很难为情的,更难为情的是还被女同事看见了:“啊,好性感的脚指头!如果夏天,如果是在某个度假胜地,如果穿着沙滩鞋,你会非常引人注目!”李欣这才明白,女同事夸张的赞美原来多半是送给那个创可贴的——那上面印满了“西红柿娃娃”。30岁的李欣已过了关注“卡通创可贴”和“即时贴刺青”谁更潮谁更酷的年龄。不过,他还是赞叹:“现在连创可贴都做得这么漂亮!”

同事不停地在王旭面前打喷嚏擤鼻涕,还坚定地说不吃感冒药——那里面有让人嗜睡的成分,而现在“青联”换届工作正进行到节骨眼上……共青团北京市宣武区委书记,29岁的王旭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盒“白加黑感冒片”让同事试试。经验告诉王:感冒没有立竿见影的特效药,他之所以把它买来作为备用药,完全是由于让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广告:“白天吃白片无嗜睡,夜晚吃黑片睡得香。”直到此刻,面对那个执意要带病工作的同事,王旭也没找到比广告语更有力的话。
即食面、快餐、速溶咖啡、罐装乌龙茶、24小时全天候的电视节目、越来越精美的商品包装、影视歌星不断变换的形象、100版的彩色报纸……一种“现代生活观”正不断被强化:省时省力还要有感官刺激。意识到这一点,就不该觉得把创可贴和感冒药弄出新花样无聊,“拥抱流行”的有心人没准儿还能从种种蛛丝马迹中看出“现代药物”的端倪。
如果不是一上车就打瞌睡,数十万北京地铁的乘客(以日客流量计)都会注意到入秋以来的一则“六味地黄胶囊”的广告(贴在路线示意图旁边):“提炼、提炼、提炼……直至菁华诞生”下面是一枚黄金镶钻戒指,再下面是一粒药物胶囊。旁边注上了几行小字,说在同等功效的情况下,“六味地黄胶囊比六味地黄丸体积减小若干倍”云云。广告语很醒目:“这样的现代中药你能拒绝吗?”广告并未突出此“现代中药”的生产厂家,以至记者也没记住。或许厂家和广告人觉得这并不重要?
“同仁堂”的丸散膏丹
“巧了,我最近一次吃的药是‘六味地黄丸’。我都好几年没吃药了。”30岁的易秉明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数学讲师。工作轻松、家庭和睦、热爱运动……易先生说他的病历上几乎是空白。
“说起来是个小笑话。我两周前打篮球把腰给扭伤了。我没向医生‘如实汇报’,只是说腰疼。医生捏了捏,说可能是肌肉轻微拉伤,也可能是肾虚。他很周全地给我开了两种药——几贴膏药和一盒‘六味地黄丸’。”
“我还‘虚’?”易先生笑道。北京的11月,他只穿了一件条绒衬衫,领口敞开,露出里面的高领T恤。不过易先生还是按时吃了“六味地黄丸”。听说,此药有增强肌体免疫力的功效,是适合男女老少的温补药(记者通过对同仁堂制药厂两位业内人士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
“‘六味地黄’有胶囊?我不知道。我吃的是大药丸子,‘同仁堂’生产的。我一点一点地咬着吃,咬一口,喝一口水,吃一个药丸要喝两杯水。如果他让我选,我一定选择胶囊,即使它是不出名的厂家生产的。年轻人大概都像我这样吧——反正都是‘六味地黄’,不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就不在乎它是不是名牌,医生给什么吃什么——更看中方便。”
著名的“同仁堂”看到那则“现代中药”的广告,听了消费者易先生对“六味地黄丸”和“六味地黄胶囊”的态度,怎么想?
北京大栅栏的同仁堂总店仍然高悬着一幅对联,上联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其实这家百年老店的生产经营者已经明白,如果他们继续把那些“丸散膏丹”当成珍贵的手工制品,当成传统的象征,“倚老卖老”,“同仁堂”(或者说传统中药)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少——年轻人顶多会把老药店当成名胜古迹,带外国友人来“参观”、买“纪念品”。
试图把“丸散膏丹”改造成“现代药”的努力实质上70年代已经开始。80年代,同仁堂对传统中药的剂型改革“大面积开花”。
“可以说,西药有的剂型,中药大都有了。”现在在华美集团工作的高级工程师傅淑梅女士说。70年代到90年代初,傅女士曾先后以工程师、同仁堂制药厂副厂长的身份参与该药厂及国家医药机构的一系列技术改造工作。
“‘同仁堂’那些著名的蜜丸都是把(药材的)草根、树皮直接打成粉末加蜜制成药丸。工序究竟多繁杂消费者不一定感兴趣,但他们会在意价钱——‘同仁堂’的传统药物人工成本非常高。以包装为例,传统药丸用蜜蜡包装,有经验的师傅拿着模子蘸溶蜡蘸水,厚度、火候特讲究,那是高级手工工艺。患者服用时也很麻烦——沿蜡丸表面划一刀,还不能彻底切开,再用手把蜡捏碎。夏天蜡软了还捏不碎它,弄得两手黏乎乎的。我们先是改造包装,用塑料壳代替蜜蜡——带罗纹的两个半球型塑料壳可轻易地结合或分离,服用都极方便。
“就药物本身看,中药改良主要是改剂型。‘中药西做’是最初的尝试。为了缩小药物的体积,我们从数十味中药里提取有效成分,熬成膏状,再烘干造粒,制成小药粒或西式的药片。不容易、不适宜提取的材料,我们把它们粉碎后直接装进软胶囊。成功的例子是‘牛黄清热散’——它一向被视为发烧感冒的特效药,但它的细粉末吃起来糊嘴。现在,‘散’变成了‘胶囊’。传统‘藿香正气水’的有效成分通过酒精转溶才能变成液体,对酒精敏感的人不仅受不了它的气味,喝完药还满脸通红,跟喝了酒似的。现在‘藿香正气胶囊’出现了,大受欢迎。”
栓剂也是一种成功的剂型。同仁堂制药厂现已退休的老厂长王群女士特别推崇它:“打针吃药谁见效快?静脉注射见效最快,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药都能注射。排在第二的是栓剂,现在中西药都有这种剂型——其实孙思邈早已经弄出栓剂的雏形了,他把药膏弄成小块,直接塞入患者的肛门。药物很快进入直肠,被其吸收。不经过胃和肝脏,药力不会被胃液化解、中和,也不会对肝脏造成不良影响。很多疾病都可以采用这种形式的药物。但不是所有患者都接受这种形式。比如野菊花栓剂,患者想不通为什么治疗结核病的药要塞进肛门。我想这是个观念问题。”
药越“现代”越好吗?
传统药物是不是一定要改造?傅淑梅女士提出了“反现代”的观点:“药片为什么一定要五颜六色?我不大喜欢口服药看起来跟扣子似的。我尤其不赞成中药片上有颜色,让它有‘更好看’的颜色就得先在药物上裹一层滑石粉,让颜色附着在其上。我吃有糖衣的药一定先用水把糖衣泡掉——那东西即使无害至少也是没用的。现在中药片剂开始出‘裸片’了,这应该成为继90年代初‘无糖冲剂’之后新的回归自然的潮流。”
事实上。“让药物更好看些、吃起来更省事儿些”这个简单的愿望实施起来非常困难,甚至有的药物根本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改造”。难就难在配方上。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药方里可能有几十味药,药理复杂。比如“同仁堂”著名的“乌鸡白凤丸”,别想把它改成药片——配方中有七八十味药,依我们现有的技术和对该药众多成分的认知程度,几乎不可能将所有有效成分都提取出来。中药也几乎不可能做成针剂和口服液——因为这样的剂型在客观上都要求液体清澈、无沉淀,而中药要是去掉各种沉淀,药效就很难保证了,就如同“水至清则无鱼”。
在吃药这件事上,现代中国人注定要比我们的祖先和同时代的西方人都更苦恼——谁让我们同时拥有传统的“中国胃”和流行的、现代的、国际的眼光!
比“吃什么”这件事更重要的
29岁的高为民先生曾经是“胃药依赖者”。这位海南中泉旅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每次吃工作餐都比别人多一道“程序”——向服务员要一杯温开水,把一小把胃药送进嘴里。员工,尤其是客户肯定会不失时机地表示一下“同情”——高先生很不喜欢这种来自生意场上的同情。
“医生让我看‘奥美拉唑’的说明书,我很兴奋——每天早晨空腹吃一粒就行了。我开始依赖这种胃药,不知有没有心理因素,只要早晨吃了一粒,一整天都觉得特舒服。”那种药非常昂贵——每瓶14粒、180元。(让高先生心存疑惑的是:此药进口货和国产货的价格竟是一样的。它们的运输成本是不一样的,进口药还要加关税……他开始猜测:谁是假药?)
也许还是因为心理因素,半年后高先生对这种方便、高效的胃药也“吃烦了”。“医生对我说:‘胃病一半在吃药,一半在调理。你是不是工作压力大,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这样的人最易患胃病。再有,饮食作息要规律……’说完,她问我要不要再换一种胃药,我说:‘不必了。”’
高先生新近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公司,他也结束了“北京人在海南”的生活。“北京现在污染太严重了,人的脾气好像也变大了,路上常看到人们为一点小事儿吵起来——开车的和开车的、开车的和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和行人……我就想:他们离胃病不
70多岁的王群在退休后仍忙于各种社会工作,但她很少生病。“饭不能不吃,药却是能不吃就别吃。”此话从这位北京大学药学系1951年的毕业生、在中药提炼厂和药材公司泡了好多年的“老同仁堂”嘴里说出来,就带了点儿哲学的味道。 同仁堂中药药品创可贴中医六味地黄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