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骨殖袋》到《怪圈》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刘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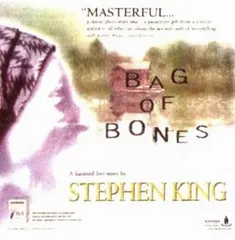
本期两刊的排名榜大体相同,新书只有3部。
《骨殖袋》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在美国以善写自然的恐怖小说而著名,其实这是读者的兴趣造成的偏见,他真正的天分在于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他迄今发表的40余部长篇堪称五彩缤纷,绝不仅是他幻想出来的那些妖魔鬼怪的故事。由于美国文学界由学者教授们划定的“纯文学”圈子过于狭窄,很多故事情节丰满、人物刻画生动的作品都被归入“通俗小说”之列,如在我国颇有市场的《战争风云》及其续篇《战争与回忆》即为一例。正因如此,当笔者和这两部小说的作者赫尔曼·沃克讨论他的作品中的司各特(苏格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以《艾凡赫》等书开创历史小说的先河)的笔法时,他简直是喜出望外。据说,去年秋天当斯蒂芬·金与他长期合作的出版商分手时(那人对他为《骨殖袋》开价1700万美元有些犹豫)感到十分沮丧,原因就是人们把他列为恐怖小说作家,而他本人却想步入严肃的“真正”小说家行列。
《骨殖袋》这一书名来自美国著名作家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等书的作者)的一句评论:即使写得最光彩夺目的小说人物也不过是一袋骨殖。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部《瑞贝卡》(中译《蝴蝶梦》)式的充满悬念的作品。
这部新作的主人公叫作麦克·努南(Mike Noonan),是在缅因州长大的四十来岁的作家。他每年都有一部畅销的惊险小说问世,主要是迎合他的贪婪的出版商、毫无创见的编辑和满脑子先锋派想法的代理人这几个纽约佬的口味。努南一向顺从他们的要求,但在他的爱妻约翰娜猝死后,却完全技穷了。每当他打开他的电脑的Word 6.0程序时,自己就会“吱嘎乱叫、抓耳挠腮”并向后倒去——完全无法创作了。
努南只好放弃他在城里的住宅,到他喜爱的度假别墅去长期休养。那所房子叫作莎拉·拉夫斯,取自世纪初一位著名美国黑人民歌手的名字。她曾一度住在附近,而且是种种作祟的神秘事件的中枢,努南在别墅里发现了不少鬼魅出没的迹象,而且在美貌的20岁少妇马蒂·德沃尔及其女儿身上又找到了爱。马蒂和她那电脑巨子的公公苦斗,而她的女儿刚好与努南夫妻为他们尚未出生的女儿(随母亲的猝死而夭折在母腹中了)所起的名字相同。对她们母女的爱使努南又回到了现实的天地,突然之间他又能写惊险小说了。
作家在此想表达的是复活的主题,鬼魂想重新作为人活在世界上,努南也想重新拥抱爱情并在长期居丧后再次提笔写作。在写法上也有些感人又含蓄的细节,绝不是一般的恐怖小说所能企及的。如努南在妻子死后发现她有一本毛姆所著的《月亮与六便士》,还在第103页处夹了一个书签,使他大受震动。而日常生活和超自然现象不可避免的关联(德沃尔老人要获得孙女的监护权的贪欲,努南在夜间听到的儿童们的怪哭,电冰箱上的信件,以及构成努南新作的那些想法),最终引向了一桩种族暴力的可怕罪行,当年莎拉目睹了这一暴行,至今仍然挥之不去。
不过,日常生活和超自然现象的结合虽然使悬念丛生,不读到最后便不明真象,但往往显得过于牵强,处处露出作者一心要追求严肃主题的痕迹。作家不甘于只有恐怖情节,竭力想写出文学品位高的小说,却顾此失彼。这或许当真是作家功力不够,或许只是追求过程中的不成熟。
另一部上榜新作是《怪圈》,其作者就是写过《马语者》的那位作家尼古拉斯·埃文思。
蒙大拿州希望镇上的形势很紧张。几只狼的骚扰,引发了牧场和政府间的矛盾,前者担心他们的牲畜受损,而后者的“恢复野生狼群”计划却造成这些食肉类动物恢复了野生的本性。
这时来了一位研究狼的女生物学家海伦·罗斯,也就自然卷入了这场冲突。这位女士29岁,因为她父亲要娶一位比她还小的继母,父女关系搞僵了,便到这里来一方面振作自己的精神,一方面从事她的科学研究。
农场上有一对姓卡尔达的父子:父亲巴克恨的是狼,喜欢的是女人;儿子卢克说话口吃,性格孤僻,和动物在一起比和人相处更为自在。这父子二人代表了人对动物的两种态度,偏偏都爱上了海伦,使女生物学家的处境益发微妙。
埃文思先生的这部新作和那部轰动一时的《马语者》一样,揭示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但是也轻松地,有时甚至戏剧化地表达了他的困惑:如果自然的生态平衡破坏了,人类会遭到惩罚,但如果让狼群肆虐,人类的生活又会不得安宁。这正是当今社会存在的“怪圈”。
当然,与《骨殖袋》相比,《怪圈》的情节要单一得多,然而却写出了更大的主题:自由、自主、自然保护和生存意识。该书的成功之处是大自然的风光描写,而那种浪漫爱情则显得难逃窠臼。
所有的希特勒都在这里
10月初,《为什么是希特勒?——至恶之谜的调查》法译本问世。年初时候,这本书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作者伦·罗森堡是书评工作者,先后在《纽约客》和《纽约时报》专栏撰文。他用了10年时间,搜罗到有关希特勒的全部资料和论著,综合成这626页的大部头。为什么这样做?罗森堡的解释是:即便有的诠释(历史的、心理的、哲学的或宗教的)不能揭示希特勒的真相,从中至少能够看出诠释者们的真相以及他们各自出于何种需要对人间至恶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诠释。
事实上,罗森堡利用的史料、采访的专家越多,读者就越会发现:希特勒实在是个谜,6年来对这个谜的种种解说实在是相互矛盾得厉害,而且越矛盾新的解说越层出不穷,以致命特勒几乎成了史学家们参不透的“神话”。正如他自己所言,罗森堡在众多解说之后再做尝试,其本意已不是提供新的解说,而是解说已有的解说。
比方说六七十年代心理分析融入历史研究,立刻就有学者论证出希特勒家庭阴暗、与母亲关系奇特、性行为变态等等,并由此去推导他纳粹心理的产生,还有学者说希特勒仇恨和虐杀犹太人是因为早年在犹太妓女身上遭遇过挫折。罗森堡在他的著作中指出类似的历史研究有着隐秘的“安慰”功能:既然希特勒的恶无法解说,干脆将他剔出“正常”人性之外。
从罗森堡对多位历史学家的访淡中可读出纳粹主义历史研究在战后的演变发展。其实欧洲战后仍是“希特勒中心”的:德国历史学家重点研究纳粹头目的罪行,结果在无形或有形之中淡化了本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对历史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则对希特勒这个人不太重视,他们把纳粹主义视为资本主义极端发展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视纳粹制度的内部运作为研究重点,尽量不去考虑希特勒个人的因素。
罗森堡也许未能穷尽各种流派的代表作品,但他的尝试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是希特勒,而不是别人,是什么情景使他在什么时候成为了希特勒,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有多少责任可以推给他承担……(刘芳) 读书文学小说作家希特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