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咖啡加点哲学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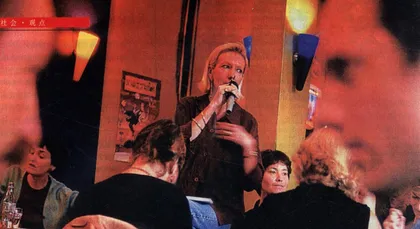
“灯塔”咖啡馆里的哲学讨论
罗素说过,哲学是科学和宗教之间的不管地带。当人们缺乏确定的答案、面对庞大的孤独感的时候,哲学给人的就是继续前进的勇气和慰藉。
哲学变得时髦又畅销
一定有很多人像巴黎的医生阿兰一样,高中毕业以后30年不曾想过“哲学”这两个字。阿兰跟大伙不一样的是4年前他因走出婚姻而走进了久违的哲学,“离婚非常折磨人,令我面对一大堆被逐出脑海几十年的问题,比如:怎样才能幸福?爱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
经朋友介绍,阿兰来到巴士底广场的“灯塔”咖啡馆寻找答案。在这里,他遇到了40多岁的哲学教授马克·索特,此人从1992年6月起每星期日11:30至13:30在“灯塔”咖啡馆与所有人公开探讨哲学问题,每次参加者均有200余人,多在35至55岁之间。
“索特总是坐在正中间那张咖啡桌边,根据提问选择讨论主题。那天真幸运,我们讨论的内容是爱自己与爱他人之间的联系,索特就我们的自由发言起承转合,讨论自始至终饶有兴味,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从咖啡馆出来后,我就去买了柏拉图关于爱的著作《宴会》。”此后,阿兰成了“灯塔”咖啡馆哲学论坛的固定成员,用他自己的话说,“哲学问答让我大脑里的钟摆重新动了起来。”
据《快报》消息,“灯塔”哲学咖啡馆的创始人马克·索特今年3月去世,不过他的信条已在城市中征服了不少人。索特生前常说:“哲学是在大街上诞生的,现在哲学应该告别大学讲堂,回到原来的位置。”当被问及“为什么在咖啡馆谈哲学”,他的回答言简意赅:“为了重新把握自己的思想。”
有思想而且想把握的肯定不止哲学教授们。继“灯塔”开哲学咖啡先河之后,巴黎现在已有20多家,外省如图卢兹、马赛、波尔多、尼斯总共也有50多家哲学咖啡馆了。如果说爱想事儿爱革命的法国人往咖啡里加点哲学并不奇怪,那美国、墨西哥、巴西、日本、德国、瑞典、甚至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上据说都有人定时定点聚在一起喝咖啡谈哲学,乍听起来,毕竟还是有点让人吃惊吧。
不仅如此,目前因特网上的哲学站点已达1500多个,大多数是些公众论坛,不过也不乏相当“精深”之所在,只钻研某位大师或某部作品。
出版界同样因哲学而热。自从1995年《苏菲的世界》走红,类似的深入浅出的哲学读本就不断冲上畅销书榜:安德烈·孔德—斯蓬维尔的《大德小论》售出22万册,吕克·费利的《人与神/生命的意义》售出了13万册,最近这两位新锐哲学家又合著了一部《现代人的智慧》,不到3个月销量已达7万册!连古老哲学也一股脑儿地热销起来,巴黎许多书店的经营者都说,这么多家庭妇女、高层白领和退休职工一起爱读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真是前所未有的美妙景象。
公众是如此地需要哲学,以至于哲学家都能与商界人士一起参与日常工作了。1989年,哲学家亚伦·艾齐戈岩开办了自己的哲学咨询事务所,将哈贝马斯的“谈话伦理学”引入公司的运作模式。越来越多的哲学教师步了他的后尘,对这种靠哲学赚钱的操作,他们一致的说法是:“不敢奢望给人们问题的答案,但是至少可以帮助管理人员和领导们学会提出好的问题。”
不是哲学回来了,是我们回去了
哲学热促动者之一的安德烈·孔德—斯蓬维尔认为,哲学现在的热不应解释为哲学回到人们中间,实际上是人们回到了哲学中间。
他说,17世纪科学迅猛发展,许多哲学的传统说法统统过时,大众仰慕的不是哲学,而是一系列技术工具;到了20世纪,人文科学的发展进一步缩小了哲学的地盘,心理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和伦理学一起把哲学挤得只能去分析语言。除了萨特、伯格森和海德格尔这些特例,在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如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列维—斯特劳斯,都出自实证或人文领域。结果大学的哲学课堂很久以来几乎只有哲学史可教。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相对于科学和人文而言的确处于退休状态。促动今日法国哲学新热的另一人——吕克·费利为此总结了另一个原因——18世纪蜂拥而出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使苏格拉底们和康德们无法继续发展,“从1789年大革命到1968年‘五月事件’,政治上的乌托邦理念一直试图大包大揽有关生存意义的一切问题,结果哲学自然淡出了公众生活领域”。
而现在,在20世纪末的时候,哲学发展的上述障碍似乎不复存在了:宗教机构衰退,意识形态瓦解、人文科学不够用、科技进步其实是双刃剑……
与此同时,人们对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孰轻孰重也有了新的判断。吕克·费利举了个例子:“战争期间,公民被要求为了公众生活而绝对牺牲个人生活。可是现在,有多少德国人和法国人时刻准备着拿起武器为这个那个捐躯?99%的人都把生存的价值定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爱情、家庭、子女和友谊等等。”
所以现代人的哲学不再是研究某个概念或者政治观念,而是“很自私”、“很实际”地弄清楚“怎样才是更好的生活”,人们回到了“善”、“幸福”和“智慧”等传统的哲学命题面前。
吕克·费利本人的思想发展走的正是一条从政治道德到个人智慧的路。1984年,这位年轻的博士出版了第一部专著《政治哲学》,当时他认为,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澄清现代民主的历史。90年代初,费利逐渐意识到这种定位的局限性:“道德是公众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它对个人生活却毫无意义。也就是说,道德在卢旺达或波斯尼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当它被实现以后,个人的存在仍然是个根本没有被解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属于智慧的范畴。”
从那以后,吕克·费利写书的对象变成了那些关注个人生活幸福与意义的民众。34岁的瓦莱里爱读他和斯蓬维尔的作品,“我对中学里的哲学课没什么好印象,那些东西理论性太强,而且对我自己的生活毫无用处。是费利和斯蓬维尔让我重新发现了哲学,他们直接探讨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比如爱情、友谊、忠诚、快乐和痛苦。这些著作虽然不一定给我什么新的知识,但是能帮助我更好地生活”。
出版社也证实,最好卖的哲学书是实用哲学。不过,许多读者对斯蓬维尔和费利这样探讨古老命题的哲学作家不满意,他们情愿去读古希腊哲学,或者来自东方的古老哲学作品,尤其是佛学。
用哲学治病?
哲学家成为畅销作家是20世纪末的新现象,斯蓬维尔一部《大德小论》卖了22万册,他哲学生涯的开端正是现代人的典型境遇:“我母亲性情异常忧郁,活得很不真实,结果当然不幸——她自杀了。我的生活因此充满焦虑,而我又不是那种轻信的人,不愿意到宗教和政治中去找现成的答案。从事哲学,让我能够拯救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罗素说过,哲学介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不管地带。当人们缺乏确定的答案、面对庞大的孤寂感的时候,哲学给人的就是继续前进的勇气和慰藉。现在,哲学已经走上畅销书榜,并且走进你的咖啡,这是否表明很多人很不确定,很有孤寂感,需要的勇气和慰藉也很不一般呢。
果真如此的话,新哲学热中的哲学就成了治病的方子了!事实上真有不少人把“哲学治疗师”当成职业在做呢。马克·索特在领导“咖啡哲学”新潮流之前就是做这个行当的,而且同样带出了一批追随者,丹尼斯·马尔克就是其中之一。他原先在巴黎第七大学当老师,1996年开了一间“生活意义工作室”,“哲学对我来说不是知识积累的途径,而是塑造自我的途径。告别教学生涯就是为了更和谐地做我自己”,马尔克说。
怎样去爱?怎样使自己幸福、自由?交250法郎,哲学治疗师就会跟“病人”对话,教他更好地把握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
只是心理问题真的能用哲学来治吗?《纽约时报》就该问题采访了全美心理学学会主席多箩蒂·坎特,她说:“我从不相信哲学能处理心理健康那样复杂微妙的事情。”另一个被访者全美实用哲学学会主席鲁·马里诺夫则说:“许许多多的个人问题,不管是心理的,还是伦理的,都不一定非得到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领域去找解决办法。”这个协会正在制定一套标准,通过考核的哲学家就能获得“哲学治疗师”的正式营业执照。纽约州政府也在考虑立法把这一行列入合法职业。已经有“病人”把哲学治疗师收费的发票拿到保险公司要求报销了。
在欧洲,对哲学的治疗能力感兴趣的人也越来越多。49岁的女记者玛丽亚娜已经是第5次到丹尼斯·马尔克的“生活意义工作室”来咨询了,她向《快报》周刊介绍了自己的动机和收获:“如果我去心理医生或精神分析学家那里,不要说别人,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是个病人;如果跟哲学家对话,那感觉就不同了:我是在完善自我,在追求生命的意义……哲学就是努力找回每个词的意思,去发现词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每个词都像活的一样,比如说‘爱’,虽然令人害怕,可我还是很想把它打开。”
在寻找智慧的新征途上,不管是简单的哲学作品爱好者、哲学咖啡馆的常客,还是哲学治疗师面前的“病人”,所有这些人的努力无非是要面对个人内心的真实世界,确立生活的意义,就像古老哲学说的那样:认识我们自己。哲学彻底实用化,对现代人而言,是幸运,还是窘迫呢? 咖啡哲学研究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