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下发响的音乐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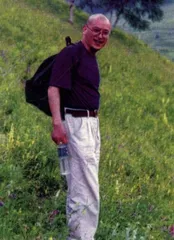
郭文景自认创作的欲望一直很强,而且一直能让人比较满意
郭文景的歌剧《夜宴》7月在伦敦首演,同台上演的还有他的《狂人日记》,被当地报纸评价为著名的Almeida歌剧院近年来最棒的演出之一。滋养生命的文化是郭文景音乐的动力来源之一,音乐在郭文景看来也绝不是简单的音响形式
▲熟悉你音乐作品的人都认为你的音乐总是带有西南地区的火辣辣的感觉,7月在伦敦首演的《夜宴》情调上能和同台演出的《狂人日记》协调吗?
郭文景:《狂人日记》由鲁迅的《狂人日记》改编,当时在编剧本的时候,我和曾力都认为一定要编一个很保守的,一点没有现代派花招的剧本。结果就顺着时间平铺直叙地讲了故事,但是其中台词全是鲁迅的原话。《夜宴》是邹敬之根据《韩熙载夜宴图》而创作的剧本,写得很优美。从外型上看,这两个作品很不同,一个是20世纪的,一个是古代南唐的故事,在深处有相同处。在我看来,这两个人都是疯子。还有,这两部歌剧都是决定了剧本后才产生音乐。《狂人日记》中的音乐风格完全是鲁迅的文风多年来潜移默化地对我的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很复杂。我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天写出了非常简单的两三个音,我发觉这几个音与我多年读鲁迅的感觉是一致的,我就从这儿开始了。但下一次就不一定是这样。艺术创作中有些难以言传的神秘的东西。虽说我是凭直觉创作,但我生长的那个环境,那个地域的文化始终是影响我创作的,像西南地区那种凄厉的山歌,高亢的船歌,沙哑的说唱,还有那些老太太讲的鬼故事。
▲虽然1985年时,刘索拉就说:要让郭文景体会生活中的困难就让他用嘴说音乐,但现在能不能讲讲《夜宴》中的音乐特色?
郭:不能。这对我最难。但有一点,写《夜宴》时,我下定决心要在这里清除一切20世纪现代音乐那种晦涩的东西。
▲为什么西南的文化你很珍视,西方现代音乐同样是文化财富你为什么要排斥?
郭:把所有人类的文化财富当作自己创作背景也是对的。谭盾就是这样的,在他的作品中他要体现这种东西文化的冲撞。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只有选择。我之所以这样选择,我想财富分为两种,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形式的,还主要是因为我对20世纪音乐的反思。从形式上看,20世纪音乐的路越走越宽,但从对社会的影响来看是越来越小。我本人很喜欢20世纪音乐,只是想寻求突破,能不能往前走下去不知道,至少横着把路拓一下子。
再仔细说,我就说不出来了。我是反对让人听纯粹音响形式的,我想让我的音乐表达、传达出更多的东西,但是我说不出来。话一出口,就假了。我特别重视作用于人的效果。比如在《夜宴》和《狂人日记》里我表达了我的做人的观点、政治观点,对我们文化的理解,但这都不是音乐的。这些东西我可以写文章表达。这都是音乐之外的。
▲音乐之外的东西有明显的文化性,音乐符号是否更具世界性?
郭:不是。一种声音就代表着一种文化符号。像古钢琴,它什么旋律都不弹,就一个和弦出来,如果你理解这声音所代表的文化,就会带出一系列文化效果。二胡“嗯”的一声,我们就有一种精神反应。以前要在世界有名的音乐厅上演自己的作品会很高兴。现在却发愁这些音乐厅对于我的作品都不合适。因为我的音乐里用了很多中国的打击乐。中国的打击乐是在露天生长的,本质上是非室内的,它是田野的、土地的,在天空下发响,而西方音乐不论多大的交响乐队,本质上是室内的。所以我的音乐在音乐厅里显得声音过于猛烈。怎么办呢?我在想,打击乐上我可能可以妥协。但嗓音不能妥协。刚才我们说到声音代表着一种文化的符号,嗓音也是。音乐学院里都教美声唱法,全世界的歌唱家都那么唱,而我在《狂人日记》和《夜宴》里根本不需要美声,要很特殊的嗓音。唱韩熙载的男低音是从英国皇家歌剧院请来的,我要男低音唱High C,我们的京剧演员都能唱,可是这位杰弗逊先生唱不了。唱得完全不是那个意思,这让我很遗憾。也许你觉得这是很形而下的小问题,其实不是,音色是代表文化的。
艺术和科学不一样。在艺术中遗留下来的习惯即使是错误的,你也无法改变。比如我上大学时的赵宋光老师,他是个伟大的老师,他把钢琴键重排。如果在科学上,他这重排是胜利的,在艺术里他胜利不了。如果全世界都用他的钢琴,全世界的钢琴大师都得重新学一遍,那些宝贵的音乐文献,李斯特、贝多芬的,都弹不了了。
▲是啊,如果不用美声,我们也不知道那还是不是歌剧。
郭:是不是歌剧都无所谓。我拿歌剧和音乐剧对比过,音乐剧里有各种嗓音,古典的、摇滚的。我想,歌剧这种铁板一块的状态也会打破的。
郭文景在Almeida歌剧院上演的两部歌剧表明了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亚洲作曲家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不仅扩大了表演的可能性,还扩大了歌剧的创作思路。《夜宴》和《狂人日记》都显示了对歌剧潜力的高度创造性理解。
要是一个西方作曲家把歌剧写成这个样子很可能会被认为犯了东方主义的滔天大罪。不过,鬼知道按照中国的眼光来看,会不会觉得郭文景难逃西方主义的罪责。
不管怎样,在西方人看来,郭文景的歌剧是精妙的,引人入胜的。现在英国的歌剧新作里能有这种效果的可不多见。
——《独立报》7.15
当代中国作曲家们开始使欧洲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谭盾是先行者,现在又来了郭文景的两部歌剧。这两个歌剧给人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它也表明郭文景在音乐戏剧方面有着创新意识的突出才能。
郭文景的音乐顺其自然地阐释了剧情,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他的音乐思路从高处扑下来并且滑翔而至,很少牵强费力,把中国的文本细腻地化为气氛。
——《卫报》7.14
多文化混合是现今的趋势,歌剧也不例外……郭文景对声音的处理遵照了中国戏剧的传统,用假声和滑音来极端地扩展了音域,还混入了口语和半说唱。
郭文景创造了他自己的风格,虽然源于中国的音乐和戏剧传统,同时又适宜西方听众。
在看惯了那么多新歌剧费力地传达信息之后,郭文景歌剧的精确讲究无疑是令人兴奋的调剂。
——《泰晤士报》7.14 郭文景狂人日记艺术音乐古典音乐歌剧夜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