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救得了大熊猫吗?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高昱)
陈大元说:“我今年已经65岁了,我非常希望退休前的这5年克隆大熊猫能够出世。”
7月19日,中国科学家宣布了对国宝大熊猫进行克隆的计划,希望以此拯救这一已不足千只的世界级珍贵濒危动物。
第二天是星期一,65岁的项目负责人、中科院动物所陈大元研究员先后接受了包括本刊在内的国内外19家新闻单位的采访。据陈研究员介绍,暑期过后,由他率领的一个科研小组将正式利用大熊猫的体细胞进行克隆试验,此项目已获得中科院第一笔10万元的启动资金。
陈大元研究员是我国受精生物学权威,同时兼任国家大熊猫繁殖技术委员会顾问。据陈大元透露,去年2月底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克隆成功“多利”羊之后,他便于3月向有关部门提出了体细胞克隆大熊猫的建议。“多利”的出世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毁誉参半。尽管英国政府以“必须正视发展克隆技术的潜在危险”为由停止了对罗斯林研究所的资助,但丝毫不能阻挡科学家们向这一神奇未知领域投入空前的热情。在国家科委召开的一系列研讨会上,学者们就曾多次提及克隆技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地挽救野生濒危动物。
据介绍,此次克隆大熊猫将采用比克隆“多利”更为高难的“异种克隆”技术,即从大熊猫身上取下一个体细胞,输入一个去核后的其它动物卵细胞中,促其分裂“借腹怀胎”,生下与原熊猫基因完全相同的幼体。“这种技术在世界上尚无成功先例”,陈大元向记者解释说,由于雌性大熊猫一年只排一次卵,每次不过一两个,而且极难获得,加之这种动物生育能力低下,“所以不能指望由大熊猫完成克隆,必须找到另一种动物提供卵子和子宫。”由于今年2月已有美国学者提出克隆大熊猫的设想,陈大元没有透露他选择了哪种动物作为代用体。据记者获悉,陈大元去年在一次可行性论证会上提到了与大熊猫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黑熊。但即便是黑熊,在进化过程中与大熊猫至少已经分开了2500万年,因此选择合适的代用动物将是比单纯的克隆技术更大的难关。
尽管如此,陈大元仍显得信心十足。他告诉记者,课题小组前期对白鼠、兔子和牛等动物进行的克隆实验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对大熊猫体细胞的培育也即将获得成功。“如果经费和材料能够保证的话”,陈大元操着浓重的江浙口音自信地说,“我不是吹牛啊,3至5年内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我今年已经65岁了,我非常希望在退休前克隆大熊猫能够出生。”
陈大元说,克隆大熊猫的计划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国内外许多公司愿意出资支持他的研究工作。8月15日,香港力康发展有限公司向陈先生无偿赠送了首批实验仪器设备。拥有世界上最大大熊猫人工繁育种群的北京动物园也已表示愿与陈大元的小组合作研究,不过他们拒绝对克隆大熊猫发表看法。
动物学家与动物保护主义者的争论
北京动物园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为陈大元先生的勇气击节叫好。对克隆大熊猫反对最为强烈的当属以北京大学大熊猫及野生动物保护中心主任、著名大熊猫专家潘文石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保护生物学家和环保主义者。记者曾想就此事专访潘教授,不巧他正带学生在广西实习。不过据其夫人向记者形容,听到要克隆大熊猫的消息,潘教授急得都“跳了起来”。
与10多年埋头实验室、致力于大熊猫人工繁殖技术研究的陈大元研究员不同,潘文石教授自1985年以来每年都要有一半时间钻在秦岭的深山密林里,跟踪考察60多只大熊猫的野外生存及繁殖习性。两位世界著名的大熊猫专家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争论可谓由来已久。
陈大元认为,熊猫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国宝,但是数量目前已降到维持物种繁衍进化的最低限,因此我们的研究,包括克隆的目的都是“为了扩大大熊猫的种群”。陈大元告诉记者,过去公认的估计是世界上还有约1000只大熊猫,而最近又有报道说只剩大约400只了,这其中还有117只养在动物园里(包括去年死于沈阳的强强、死于美国的欢欢和刚刚在太原去世的莎莎),在野外生存的大熊猫被道路、河流和居民点分割为36个“孤岛”,“长相望,难相守”。陈大元强调:“撇开物种灭绝问题而侈谈生物多样性和自然主义是毫无意义的。”
国内许多关注大熊猫的专家学者都相信,大熊猫是一个走向衰亡的物种,这是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必然,目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尽可能延续这个“国宝”。持这种观点的包括被称做“熊猫部长”的前林业部副部长董智勇和著名学者唐锡阳。首先大熊猫的活动能力很差,食物已高度特化。这种食肉类哺乳动物不知从什么时代开始只能靠吃竹为生。由于竹子并不是有营养的食物,大熊猫必然每天花14~15个小时不停地吃,一只大熊猫每天要吃掉3000余株冷箭竹,约合40公斤,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这其中只有17%能被消化。为了节省能量,大熊猫深居简出,养成了吃完就睡的懒惰习惯。更要命的是其繁殖和成活能力低下。大熊猫是季节性发情动物,雌熊猫每年只有4天发情高潮期才可能受孕。根据过去的资料,1000只大熊猫中的600只是雌性,有生育能力的只有200只。自1963年北京动物园首次人工繁殖成功以来,国内外有14处繁殖过大熊猫,共产92胎136仔,但成活半岁以上的只有56只,死亡率大大超过存活率。无论是“资本”雄厚的中国,还是科技发达的西方,都没有攻破繁殖大熊猫这一道难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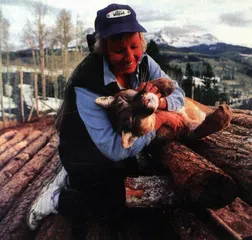
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保护自然和濒危野生动物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并不反对让大熊猫在栖息地自然繁衍,这无疑最符合自然法则,但它是濒危物种,而且在自然繁殖上是有缺陷的。”陈大元指出,更何况其前提条件已不存在,既没有足够多的种群数量,也没有足够大的不受人类干扰的野生地区。理想的解决办法是人类自行大幅度减少人口,把许多土地、森林资源让给野生动物,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即使真有这样的保护地,包括大熊猫在内的许多濒危动物都不是任其自生自灭就能保存下来的。”陈大元说,“只辟‘世外桃源’而不加帮助、‘无为而治’式的自然保护,只能算作是对困境中的动物的冷漠。”他认为,对大熊猫而言,克隆只是一种人工辅助繁殖方式,但或许真能从根本上找到一条出路,“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潘文石教授等人却对陈大元研究员的满腔热情不以为然。“他们做的是如何到月球去的计划,”潘文石说,“而我的渴望则是从北京到秦岭有一个巴士就行了。”
“大熊猫并非像他们所说的那么没有希望”,世界自然基金会负责大熊猫保护项目的吕植博士说。作为潘文石教授的得意门生,吕植与潘文石一起在秦岭工作了8年。在这里650平方公里的栖息地内,生活着250~280只大熊猫。吕植与潘文石对其中35平方公里进行深入追踪研究后发现,最近10年来大熊猫数量的增长率为4.1%,比人类的增长率还要高。吕植的另一个重大研究成果是大熊猫还远未走向高度近亲繁殖的灭绝道路。她把从各保护区和动物园收集来的大熊猫血样拿到美国做DNA测定,得出大熊猫的遗传多样性比率为46%,与人类48%o的比率相差无几。吕植经过计算后认为,在200年内,人类不加干涉,有28只大熊猫就足够繁衍物种了。
潘文石和吕植承认,动物园中的大熊猫发情和受孕率低的情况确实存在,但他们认为,这不代表大熊猫的繁殖和交配能力,而是因为缺少像野外那样的繁殖条件。早在198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美国专家乔治·夏勒博士等人就曾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亲眼目睹两只雄体争配一只雌性大熊猫,在两个多小时内交配48次的激动情景。两年后,他们又目睹了一次更为壮观的场面:5只雄体争配一只雌体,从气味吸引到吼叫呼唤,从树上咆哮到悬崖扭打,整整折腾了3天,3只胜利者先后与这只雌体交配。唐锡阳先生后来特地问夏勒博士大熊猫的交配能力究竟如何,博士答道:“它们的性欲比我强多了。”
“大熊猫完全可以依靠野生有性繁殖来维持其种群,”吕植说,“根本不需要费时费力地搞什么不能增加进化过程的克隆。”当然这需以生存环境得到保障为先决条件,尽管我国政府多次强调对国宝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并计划将保护区从13个扩大到27个,但由于无法真正“撤退人类”,20年内,大熊猫的适宜生存环境减少了一半。
“面对大熊猫的危机,我们不是自我开脱,就是想着投机取巧。”与潘文石、吕植同为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员的北京濒危动物保护中心郭耕说得更为直白,大熊猫是国宝,要挽救它,可我们不是去检讨人类无休止的扩张给大熊猫带来的灾难,却总想着是它命当该绝;不幡然省悟,下功夫创造其繁衍生息的自然庇护所,而是梦想着一劳永逸地毕其功于一役。“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态度,”郭耕认为,尚远未过关的克隆技术现在竟然成了随时可以拯救大熊猫的灵丹妙药,“还会有人再去珍惜它们,为它们保留一片净土吗?”
“陈大元先生是以科技进步为己任的生物学家,为了证明某种科学上的可能性,他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但是对大熊猫,以及东北虎、长臂猿等类似的濒危物种来说,”郭耕问道,“陈先生致力的工作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非自然的保护
据联合国环境署估计,目前地球上的物种约有3500万种之多,其中脊椎动物4.1万种,它们都是经过亿万年的自然选择留存下来的,大多数物种的历史要比人类悠久得多。人类的出现使自然选择尤其是物种灭绝的速率大大加快。目前物种丧失的速度比人类出现前的自然灭绝速度快1千至1万倍;在生物进化的大部分时间里,灭绝速度与生成速度大致相当,而现在前者要比后者快1万至100万倍。世界动物保护协会1996年的年度报告指出,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使动物栖息环境遭到破坏和正常的繁殖受阻”,已有的4600种哺乳动物中,1096种濒临灭绝。设在英国剑桥的另一家环保组织世界自然资源保护监测中心评选出了20种最濒危动物,中国的大熊猫、白鳍豚和扬子鳄赫然名列这份“黑名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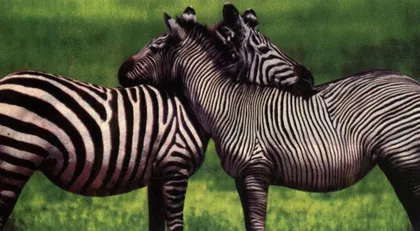
随着对野生动物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它的价值也在逐渐加深认识
类似的报告和预测还可列出长长的一大串,这一方面足以触目惊心,另一方面也说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征服自然的快意中醒来,开始反思先辈和自己对自然界、对动物生灵欠下的罪孽。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保护自然和濒危野生动物成了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人类为了现实的利益仍有条不紊地开发利用动物的栖息地,人们便把赎罪的希望寄托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上,大批野生动物被捕捉送往动物保护中心,过去仅供游人赏玩的动物园也成立了研究所。为了使濒危动物不致绝种,科学家们使用注射激素、人工授精、试管幼体等生物技术千方百计地促使它们交配、繁殖后代。
实事求是地说,圈养和人工繁殖把许多野生动物从历史舞台的尽头拉了回来,如果没有人类的帮助,现在恐怕早已见不到欧洲野牛、新疆野马、亚洲双角犀、非洲矮河马和紫羚羊了。在中国,最应对动物学家感恩戴德的莫过于扬子鳄。50年代末,这种曾盛产于长江中下游的中生代“活化石”仅存不足500条。为了拯救扬子鳄,国家在安徽宣州建立人工繁殖基地,经过15年的研究试验,这里人工繁殖的扬子鳄已达7000多条,并且有望每年以2000多条的速度增长。
人工的保护和养殖很多时候确实可以帮助困境中的动物绝处逢生,但也远非十全十美。“人们的良好愿望往往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郭耕介绍说,由于失去了原始生存环境和自然驱动,动物园和保护中心圈养的野生动物基本上都表现出性功能紊乱、繁殖弱化等症状;为了增加种群,人为操作动物近亲繁殖,甚至父与女交、母与子配的事例在动物园中也比比皆是,遗传多样性根本得不到保证。野生雌性大熊猫的发情期为每年的5月,而圈养的雌体则往往推后或提前半个月左右,排卵期很难掌握。雄性大熊猫更是由于身体臃懒、缺乏活性而几乎丧失发情功能。国内外饲养过大约120只雄兽,能交配的只有11只,现在只剩下4只雄性大熊猫具有自然交配能力了。其他濒危珍稀动物的状况也大同小异。目前全世界华南虎总数不超过50只,基本上都被人工圈养,大部分是6只老虎的后代,50%是两只老虎的后代,几乎个个都有这样那样的遗传疾病。今年北京动物园人工繁殖成功了两只雪豹,出生后才发现它们根本就没长眼睛。
尤其让环保主义者无法容忍的是,东北虎、非洲象等濒危珍稀动物被人工繁殖成功后,面临的却是更加肆无忌惮的屠杀。绝处逢生并不代表转危为安。刚刚游出苦海的扬子鳄尽管仍属世界20种最濒危的动物之列,从今年开始却已堂而皇之地成了某地政府某宾馆餐桌上一道招揽顾客的美味佳肴。据说此举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批准,因为“人工繁殖的成功已使扬子鳄免除灭种的危险”,吃扬子鳄的肉是“‘国宝’开发利用的新突破”。
不能否认,在保护野生动物乃至保护自然的情绪中,包含着人类某些赎罪的意味。但花费大笔研究经费并取得成效之后,人们当然希望得到利益上的回报。事实上,随着对野生动物研究的日益深入,在保护的同时,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价值也在逐渐加深认识,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和开发利用的规模也不断增长扩大。按照这种人性思维,保护是为了利用,可持续的利用是最好的保护,这两句话都既合情又合理。但对于与人异种的动物来讲,是生是死都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对克隆大熊猫持反对态度的人只在少数,但他们的意见在当今社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声音中确实引人深思。在商业化、实用行为方式渐渐主宰我们的时代,大熊猫被克隆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正是它新灾难的开始呢?而当克隆技术真的已成熟到可以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的时候,我们是应该把大熊猫大量繁殖,还是零星生产以保持其国宝的珍贵和标志性呢?唯一可以确知的是,它们将更直接、更完整地失去自然,被掌握了更高技术的人所控制。 成都熊猫基地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动物扬子鳄大熊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