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你老师
作者:李鸿谷(文 / 李鸿谷 事件 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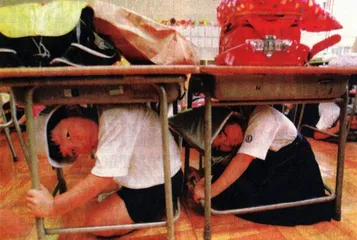
老师发威,能躲就躲
事件多耳光打在孩子脸上
今年9岁的朱海被全班同学打了耳光,是朱海的奶奶蒋太婆发现的。蒋太婆今年六十多岁,是武汉市三曙居委会的主任,这个居委会紧挨汉口的汉正街,在宝善街小学读三年级的朱海是蒋太婆的长孙。
原先也住在三曙街的大儿子一家由于搬迁,临时住在汉阳过渡,所以在三曙居委会附近小学上学的朱海,基本上由蒋太婆照料。
今年五一节前一天,蒋太婆的同事与她说闲话,问道:你家的小朱海现在好像瘦了咧!听了这话,蒋太婆留了个心跟,等到小学放学时,她有意找到朱海的同班同学问朱海现在表现,朱海的同学回答很干脆:表现不好,我们的老师还让我们一人打了他两耳光的。
被同学一人打两耳光,这让蒋太婆听来很是吃惊。等朱海放学回来了,蒋太婆假装不经意地问道:
“你上课是不是又不听讲,讲话了?”
“没有啊!没有啊!”朱海争辩说。
“你如果不讲话,老师为什么会让同学打你的耳光?”听奶奶说出这话,朱海愣了一会,放声大哭。蒋太婆当晚就赶到了学校,由于第二天放假,晚上在学校并没有找到领导和老师。
第二天就是五一节,这天上午是校长姚忠金值班。他一到学校就听门卫说昨天晚上有家长找到学校来,说孩子被打了。他问清大概,马上就把电话打到那位老师家里,在电话里姚校长刚刚问起是不是有这么回事情,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哭声。姚校长心想糟了。
打耳光事件发生在半个月之前,那天是4月14日。
这天上午,数学老师冯丹计划给朱海所在的班教新课,但课堂纪律不是太好,朱海在下面讲话,冯老师批评了他,又接着讲课。不久,朱海又讲起话来,这次不是跟同学讲,而是接老师的话。冯老师一下就火了,厉声叫道:朱海站起来!然后,冯老师又喝道:你自己打自己两耳光!朱海当然不乐意。
不乐意自己打自己的朱海被冯老师叫到了教室的第一组第一排前面。冯老师再问他打不打,朱海还是不乐意。这时冯老师就决定让全班同学一人打他两耳光。从第一组第一个同学开始,每个同学都跑到朱海面前伸手打了他两耳光。
由于事情已经过去相当时日,再回忆当时情形时,老师和学生的说法有一定的出入。
老师说当时大多同学都只是轻轻地在朱海脸上扫过两下,只有五六个同学打的重了一些,把朱海打哭了。据此,老师与学校方面认为说打了朱海八十多耳光并不准确,并没有这么多。
同学们的回忆则补充了这样的事实,在一旁观看的老师还对那些下手轻的同学说:打这么轻,重新打!你们不愿意打,我就让朱海打你们。后来,冯老师还对另外一个同学说,你下次讲话,就跟他一样的下场。一队一队的同学打完了,这堂课还没有打铃下课,这时冯老师又开始了授课。
朱海的父母与奶奶也回忆当天晚上的情况,他们确实发现朱海脸上红红的,但并没有在意,朱海的奶奶还认为这只是天热的缘故。
冯丹老师今年20岁不到,刚毕业分配到宝善街小学不久。在接受采访时,她解释说她当时只是觉着老师打学生不对,但没有想到学生打学生也不对。为什么会想到要打学生,这位年轻的女老师解释说,她很怕教不好,别人会责怪她。这件事,冯老师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说她当时就有些懵了,后来想起来也觉着后怕,所以对谁也没敢说。
蒋太婆也问自己的孙子朱海:为什么挨了打不回来告诉奶奶呢?朱海说,说这个事,太丑了。
学校知道了这件事当然很重视,学校领导三番两次地到朱海家赔不是,冯丹老师也到朱海家赔礼道歉。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尚处于良性状态,彼此还没有太介意与纠缠此事。甚至学校征询家长意见是不是想开除这个老师公职时,蒋太婆还说千万别这样,现在找 一份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后来当双方坐下来谈如何处理此事时,谈崩了。家长方面提出了3条要求。第一,冯老师在全班向朱海同学道歉;第二,冯老师不能再带这个班,因为朱海看见她就害怕;第三,学校专门找一个老师辅导朱海的学习。他们在第二条上谈崩了。
学校一位领导说,这学期也快结束了,下学期再换老师也许更合适一些。而家长则说,要马上换,因为孩子害怕这个老师。在这时,另一位学校领导脱口而出,你们的孩子怕老师,那我们的老师还怕带你这样的学生咧。这一下,彼此没法再谈下去了。
学校与家长的处理意见没有达成一致,但学校还是按步骤开始处理此事。冯丹老师受到了全区的通报批评,学校扣发了她今年一年的奖金,并决定她今年不能升级。学校也决定马上让冯丹老师在班上向朱海同学做检讨。这次检讨还安排朱海发言。为了这个发言,朱海回家要事先准备准备,他写了个发言稿,大意是:上冯老师的数学课,我讲话,冯老师让同学打我。同学打我是不对的,冯老师让同学打我也不对。我上课讲话也不对。这个发言稿让蒋太婆看见了,她一看就火了,明明说好是冯老师向朱海做检讨,为什么现在又要朱海也做检讨。
这样,家长与学校弄得更僵了。
蒋太婆向学校明确提出要求:打一耳光赔1万元钱,学校赔80万,这事才算完。家长的价码一开出,学校觉着很难办了。

学校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学生的身心健康同样重要
事实上,蒋太婆是拿这个价码与学校斗气,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再穷,也不会穷到让别人打我们孩子的耳光来赚钱吧!”她说她最生气的是学校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给孩子心灵带来的创伤,现在孩子还小,不明白事理。如果学校不把这件事带给他的阴影尽量消除。他长大了会怎样想这件事呢?他有了尊严意识后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这次被打耳光呢?蒋太婆说他们做家长的,现在想起这件事就心痛而且害怕,但是还不敢在朱海面前多说这件事,怕给他带来更多的不良的心理积累。比如现在准备给朱海转学。而朱海自己却不想转,因为在宝善街小学他有很多小朋友。而家长只能哄着他,说新学校更好,还不敢说因为这件打耳光的事情。
6月15日,这一事件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朱海转到另外一所小学读书,学校赔偿朱家1000元钱。
态度 老师是最吃亏而不讨好的职业
25岁的刘平今年考了武汉大学的插班生,但成绩离分数线差3分,能不能被录取,现在还是未知数。
刘在一年前停薪留职辞掉了他的老师工作。辞职前,他是湖南省浏阳市牛石中学的老师,教语文和政治。他还是这所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位优秀老师之一。学校计划让他带初三毕业班,这对于一个刚毕业不久的新老师而言,已算得上是殊荣了。但他还是拒绝了。
但当我们坐下来谈他真正的理由时,他说:“我用我当学生时最痛恨的办法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太没有意思。”
刘平自称他读书时是个混混是个小痞子。刘在高中时考进了他们城市的重点中学,但过不久便与班主任发生冲突。冲突的起因是刘与班上的一个同学为打开水之事打过一架,而这个同学恰好又是班主任的表弟,这下刘就有口也难辩自己的委屈了。随后,刘平就成了老师口中的“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甚至冬天也不允许他戴手套,虽然他生了冻疮。这样刘平就径直走向小混混的队伍里,经常打架斗殴,被学校处分了好多次。
上高二的第13天,他和家长被学校请去了。学校给出了两条道路。一是开除,二是转学,如果转学,学校可以取消一切处分,给个好评语。刘平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转学了。结果转的那所学校更糟,刘平“混”得更厉害了。他家人看他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动用一切力量,在他读高三那年把他转到浏阳市的一所省重点中学。在转学考试中,除了语文,刘平所有的成绩都只有20多分。校长说,我也是没法才接受你。你能不能毕业就靠自己了。
这一年刘平倒是刻苦攻读,竟也拿到了毕业证,但没有考上大学。随后他又复读了一年,终于考上长沙大学。
毕业后,他告诉家人要回他当年被劝转学的那所中学去当老师,表现给他们看一看应当怎样当老师。但家人打消了他这种可笑念头。这样他进了牛石中学。这是1995年。
当时整个教育界素质教育呼声正高,刘平到了牛石中学,正可以被容忍表现自己的能力。
刘平改革了语文作业教学,他要求他的学生每天写日记,每两周有一次口头作文课。随便找出一样道具,比如地球仪什么的,让学生一个一个上台来讲他看到什么,藉此练习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开始学生们不习惯他这一套,后来竟爱上了他这套方法。于是,学校的公开课,他总能出风头。他对学生在作文中出现的错别字,并不像一般老师在作文本上改完就完了,而是把最常见的错别字列出来一个一个的讲给同学们,比如“大吃一惊”,学生们爱写成“大吃一斤”。刘平在班上讲:你们在回家的路上看见牛屎,谁能大吃一“斤”,就上台表现给我们大家看一看。班上学生在哄堂大笑声中,明白地记住了“惊”。
在这年年末的全市统考中,刘平所教的两个班语文成绩在全校五个班中,分别只排第三与第四位。这一结果否定了他所有的努力。年终的考核评定,他仅得了个“中”,年终奖金也仅400来块。
第二年,刘平被安排带一个班的语文与两个班的政治。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在钻研历次统考试假之后,他自己出了10套语文摹拟考卷和8套政治摹拟考卷。在学期结束前一个半月就完成了新课的讲授,开始了摹拟考试。
刘认为他的考试方式既原始也有效,比如政治。根本就不跟学生们讲什么,根本就不期待他们理解什么。每次考试,凡达到80分以上的学生,就自己去订正没有答对的答案。而80分以下的学生,则告诉他们标准答案,让他们去背,背过之后再考。再次考试80分以上的也可以过关,还在80分以下的又背又考。语文也和政治一样,考过背,背过再考。刘总结规律是,一般如此3遍以上,全班的学生基本上都可以达到80分以上。
但是学生对这套方式痛恨至极,每次再背答案再考试总有学生逃跑,刘就一个一个把他们抓回来。在这套办法之下。刘平终于出了“成绩”。在这一学年的全市统考中,他所带的两个班的政治平均成绩在全校名列一、二名,在全市近200个班级里,也排到第十名和第十五名;语文的平均成绩也在学校列第一名,全市排第二十二名。随后他被评为学校的优秀老师,年终奖金也拿到了1500元。正是在取得这些成绩后,刘离开了学校。
刘平反问道:老师有什么权力?一进学校就被反复教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手打学生,但在那种紧张气氛下,谁也不能担保什么。“这不是让老师很为难吗?”他说,他们年轻老师在每次上课铃响后,拿着课本离开办公室时都相视而言:“走,我们又摧残学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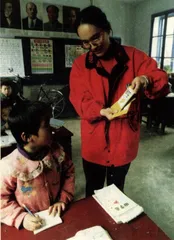
素质教育呼声正高,老师不再是仅仅传授一些书面知识
方法 老师权威的建立
李卫说他分配到学校后,受到前辈老师的第一个教育就是:如何给学生一个下马威,建立自己的威信。李分析说,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一般开始并不会从学习入手,而是先从其生活习惯着手。比如做清洁,比如队列训练等等都是校正学生习惯的内容,要训练学生对这一切形成条件反射,一提到什么事情,学生有本能的反应。
李卫1995年从湖北荆州师专毕业,他是学校的优秀学生,属于可以优分的对象,这样他被分配到了武汉的一所中学。不过,他现在还没有做班主任,所以也没有机会完全实施他所说的那些方法。
我们讨论了学生上课讲话这一现象,李卫讲述的对上课讲话学生一系列成系统的处理方式是:如果有学生上课讲话,被老师眼光扫巡后还不自觉停止,他会被请到办公室里去。这套系统自此开始启动。老师一般对到了办公室的学生并不特别理睬,这叫“冷处理”。学生呆在成人堆里,不久便会不自在,开始焦虑,渴望回到同学中去。这一切都逃不过老师的的眼神,这时老师准备处理问题了。不急不慢,老师会问学生:你觉得你今天犯了什么错误。在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如果学生表现出不认错不合作的态度,老师会使用的一招就是找来一份报纸,让这个学生从开头读到最后,“你不是喜欢讲话吗,今天让你讲个够”。不念完报纸,学生当然也不能离开老师的办公室。不过,大多进了办公室的学生会很快就范。下面一个步骤就是老师跟学生订下处罚条约。“如果下次讲话被我抓住了怎么办?”学生为了急于离开办公室,显然会胡乱想出一些自我惩罚的办法,如写检讨,如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等等。
在这一套过程中,老师总是处于主动的角色定位里,而“坦白从宽”在这种谈话里是贯穿始终的主导思路。老师的开白场永远都是:“你说你今天犯了什么错误?”
这一套过程当然显示了老师与学生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显示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最后帮助老师建立了自己的权威与威信。
观点 老师就是管学生的
刘嘉有次开车违章被警察抓住了,要扣照。刘嘉跟警察说好话,说他所在的小学与警察很近,是“亲戚”单位。警察听说他是老师,很有道理地给他来了个总结:老师是干什么的,管学生的!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就是管违章的。
刘嘉说他听来了一个真理:老师就是管学生的。
在一些小学里,刘嘉经常听到一些老老师抱怨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教了,又不听话又不敢打。说起这些老师,刘嘉总有一些不屑,教了几十年书,还不明白老师是干什么的。
刘嘉其实不是正式的老师,他至今也没有老师任职资格证,但他不时会被一些小学当做专家请去为学生们辅导数学。他自己也有长期的数学竞赛辅导班,学生多的时候达到500多人,现在也有300多人。这些学生按不同年龄被分成4个年级,每周一次或两次很正式地上课布置作业。而且他还是纳税人。这种被称为“社会办学”的竞赛辅导班,武汉市就他办得最有名气也最具规模。
刘嘉成为武汉市教育系统一个很奇特的人物。教育主管方面从来也不承认他,而家长却很欢迎他,同时一些小学也很欢迎他,他有本领让学生在各种数学竞赛里拿到名次。刘嘉自己也没有统计他所教的学生的得奖率,但在社会上传说的得奖率是很惊人的。
许多家长口耳相传找到了他。在这种民间传播中,描述刘嘉的第一句话往往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经常体罚学生的”,还有传言说没有学生没被他打过。——而这一描述,在许多家长印象里甚至比他的高得奖率更深刻。但是,仍然有一批一批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他的辅导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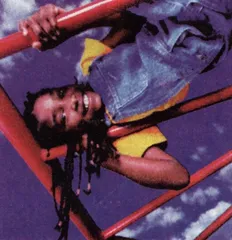
刘嘉很正大光明地实行着一套在一般学校万万不敢采用的教学方法。他每半年考试一次,按成绩排座位。成绩好的就坐在离黑板更近的前排,成绩不好的只能老老实实坐在离黑板更远的后排。当然,在他这里也分快慢班。他觉着孩子成绩跟不上的,会很明白无误地跟家长说,你把他带回去算了,免得浪费时间和钱财。当然他也有奖励的措施,比如每半年考过之后,成绩在他定的分数线上的学生,不仅可以坐好位置,还被免掉这半年的学费。
家长们回忆他的教育主导思想,很简单,他说:你们如果长大了想去踏“麻木”(三轮车),你们回家就可以睡觉。老师我当年没有12点以前睡过觉的。数学没有别的巧,就是你给我做题。
刘嘉跟我解释说,现在许多人认为小学生不需要学会竞争,而我认为恰恰相反,必须从小学会竞争才能在这个世界生存。
在他的辅导班里学习,他认为这是可以教会孩子竞争意识的好地方。他采用的方式备受家长注目,当然也是一般学校不敢想象的。在他上课时,学生凡犯有讲话、做小动作、不安心听讲等错误,他就极可能走过去,这时犯错的学生已经哆嗦着站起来,他手里的一根教鞭,对着学生要不打屁股,要不打手心。
在这种辅导班上课,差不多的学生都是由家长相陪而来的,刘嘉还特意当着孩子的家长打他的孩子,但家长似乎都无异议。刘回忆说,这些年来,打孩子也只与一个家长闹翻过,后来还和好了。
刘认为,老师的权力应当得到充分的承认。
他分析说,站在人权的角度而言,儿童与所有的人一样拥有权利,而且不能被侵犯。但如果简单地这样认定,就会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儿童的思想与行为是不完整不健全的,有些思维与行为会对个人的成长有害,这些东西当然要纠正。谁来纠正?老师这个职业应当是有权的,也是应当被认可的。
纠正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现在被广泛认可的交谈式的方式,另一种就是体罚式的。比如过去的皇帝。一个国家最大的一个人物吧,但他的老师还不是有教鞭,在他犯错时打他纠正他。
刘嘉认定,体罚的方式是在学校被最广泛采用的方式之一。比如留下来,比如罚做作业等等,这些你能说它不是体罚?这些方式无论如何批评,总比老师对学生不理不睬视若无物要好得多。而对学生不理不睬,现在正在成为一些不知该如何管教学生的老师采用的一种办法。这种被刘认为是“杀人不见血”的办法,可能会真正摧毁学生的身心。
刘称,与一般学校采用隐性的体罚方式不一样,他更喜欢直接的行动。因为一旦体罚,老师与学生的不平等就马上显示出来了,也就马上暴露了矛盾,也就使矛盾的解决成为马上的问题,并且迅速解决。而老师与学生最怕的就是彼此藏着掖着,矛盾被隐蔽着,最后演变成师生的互不信任。
刘嘉给老师的定位正如前述,很明确:老师就是管学生的。在为自己行为寻找理论基础的同时,刘嘉也注意到了教育的亚洲方式与欧美方式的不同,他归纳说这是因为文化传统不一样。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权力决定规则,规则体现秩序——老师当然也是权力环中的一环:而欧美则是法律决定权力,法律体现秩序。
常规与非常规
为着这次采访,我去找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教育学研究专家孙锦涛先生。孙先生游学甚广,在日本拿到教育学文凭后,又先后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过欧美。
但是我们的谈话长时间不合辙,后来还是孙先生发现了问题的症结。他说,你所研究的是老师的非常规行为,而我们这些教育研究者多是研究老师的常规行为。他说他很难为我提供什么帮助,他的同事也很难。“非常规行为”还没有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但是,孙说,这种研究很有意义,对他们这些专业人士更有意义。
大量的采访不能进入以个案为叙述方式的文内,但这些内容至少是可以为个案叙述提供背景的。

分数与名次成为衡量的标准,几乎也是每个学生的压力
压力
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认为他们的压力过大,一些年长的老师今昔对比,这种感觉来得尤为强烈。压力是弥漫性的,它落实在老师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每个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每学期或每学年都有不同形式的统考。考试成绩被据说很科学地分类排序,可以认定这种分类排序是为着量化地研究如何搞好教学,但其最实际的应用却在另一方面。在这种排序中,学校的位次一清二楚。在一些大型的统考时,比如初中升高中的考试,这种名次的价值就大大体现了。近年中考成绩出来后,宜昌市电视台总要接待来自家长自费的祝贺广告。重点高中入学率最高的那所学校被那些歌星深情地歌唱着。
没有学校敢不在意这一现象。如果你的升学率下降,紧接着你的生源也就成了问题。家长宁肯掏大价钱让孩子到高入学率的学校去读书,也不会到你学校里来。如此一来,学校要翻身难矣。
一位退休的老师评价说:“现在的学习更像体育竞赛,分数与名次成为衡量的标准。在这种循环里,谁也不敢掉队。”但他又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读书呢?”
学校的压力当然会往下传递。对老师们的评价又与分数与名次相勾连,你无法逃避,奖金和收入也与分数和名次挂钩。你可能一学年只拿400元的资金,也可能拿到1500元,这关乎你的班级平均分与名次。
老师的压力又会往哪里传递呢?学生,唯有学生!在这套系统里,未成年的学生成为压力终极的承受者。这公平吗?
动机
所有老师都宣称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学生好。哪有老师不希望自己学生出息的呢?这一高尚的动机,相信不会有太多人怀疑。
但是,正如前述学校与老师面对的压力,毫无疑问,与分数挂钩的评价体系和奖金分配介入,已清清楚楚表明了决定老师行为的另外更重要的因素。这一系列的评价体系的介入,并不能否定动机的高尚,但是它至少为观察教师的行为提供了另外一种方式与可能。人们有理由观察高尚动机背后所含有的另一面。当然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观察角度,但客观地说与老师谈话,不首先承认他的高尚,谈话很难进行。
我在与老师讨论动机问题时,往往不能深入。正如老师会在学生面前坚守自己的威信,老师在与非老师的交流中,坚守的是自己高尚的动机。我甚至在交谈中在再三向打断我说话的老师要求:“能不能让我把我的想法讲完呢?”老师不愿意面对你对动机背后事实的叙述。
每个老师在叙述时,都认定现在的教育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但是作为这种制度最直接的实施者,他们却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问题。
权力
在不同时代长大的两代人,老师与学生。——老师成长的时期这个国家尚处于短缺经济时代,而现在的学生们则已经在过剩经济时代享受消费所带来的快感。老师与学生都对对方有着相当多的不理解,学生的不理解倒也罢了,老师的不理解所表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权力的过度使用。
很多老师很委屈,他们说我们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权力可言,过去的老师把学生打几下不足以论,而现在你敢吗?
不过,要统计现在老师的体罚的具体数据的确是困难的。从老师的角度看来,已经是少之又少了,而从传媒报道的角度而言,现在差不多是层出不穷。可以解释的理由是,时代的变化使老师更被广泛关注了,而这种关注又是以每个个体自我权力意识的增强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权力受到广泛的质疑,随后的调整势在必然,这种调整又必须与整个的教育制度的改革相适应。
老师们也很迷茫,一位老师曾反问道:“谁能确定老师权力的底线在哪里?”

反差
有两种反差被发现是广泛存在的。
其一是老师的自我评价期许与社会真实评价现实的反差。
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夫妇都是老师,不同的是,丈夫是大学教政治的教授,而妻子是一中学的班主任。他们两人的每月总收入竟是丈夫不如妻子,而丈夫还是政府津贴的享受者。妻子在丈夫面前是得意的,她的收入高啊。但是面对像我这样的陌生采访者,她对自己的收入却更多表现的是不满,她认为她应当更高。“社会上那么多比我高得多的人。”但是社会上更有比老师收入低得多的人。我在宝善街小学采访,学校的姚校长就告诉我,他们周围很多人议论老师时就说:也不过就是一个仅仅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小学老师,凭什么拿得比我们还高,而且还这么稳定——反差因此出现。
对收入现实的评价反差又掺和了另外一层评价——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在想象中的价值与现实中的价值的反差,如此累加,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总不能合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