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方式和我们的未来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罗峪平 摄影 符建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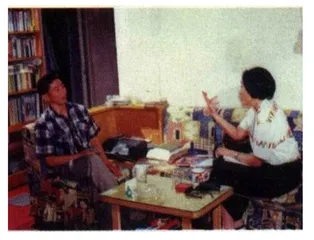
罗:你在7年前出版的《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①中,对西方经典发展方式进行的批判令人印象深刻。你认为,无论从历史和资源的角度,欠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再重复西方的发展道路。而且你认为在发达国家之间实际上一直存在一种默契,即共同维持和强化已经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格局。所以,欠发达国家要想扭转自己的不利地位,不能指望发达国家的宽宏和“真诚援助”,而应该选择一条与西方经典发展方式完全不同的道路。现在,与十年前相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占有的地位越发优越。他们不仅是大多数场合中的赢家,还充当了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我的问题是,中国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多少空间选择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式?如果不按照现有规则对世界市场开放,我们还有多少可能在全球一体的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邓:对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从资本流动占世界GNP的比例和全球贸易等孤立的指标看,现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还不如一战以前的1913年。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对全球化的认识要清醒,至少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
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应不应该选择自己的道路,这个问题的意义实际上越来越重要和明显。从现代技术的角度,也很难说发达国家提供了好的典范。他们发展方式的资源基础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说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百分之十几的人口走这条道路还走得通的话,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将达到60多亿,大家都走这条道路显然不行。现在都在讨论如何融入世界经济,其紧迫性已经被渲染得不太恰当。我提出的发展方式的问题,不关乎我们是否融入世界经济,而是我们到底要什么?中国发展是为了什么?准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为了吃穿住行达到较高的水平和更为方便,发达国家靠大批量生产,靠高效率市场体系和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达到这个目的。如果我们有办法实现上述目的,而且比它的成本更低,那你的道路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它和生活质量的关系就不大了,这时候消费的是环境,是人的精神活动的质量,是一种非有形物质。古代农业社会利用的是可再生资源,阳光、土地、水,是一种自然经济。到了工业社会,开始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煤炭、石油、铁矿等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变成商品经济。发达的商品经济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分布不匀的特点联系在一起。这些资源不像可再生资源,阳光、水、土地,分布基本均匀,它们需要搬运、交换和流通。在未来社会里,在我提到的非西方经典发展方式的新发展方式中,重新转入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基本能源和原材料可以以再生资源替代,生产过程会日益小型化,原来需要高温高压的化学反应过程,可能通过生物技术在常温常压下做到,这种未来社会中生产和生活现实胚芽,没有人去注意,但它可能是比全球化更有力量的一种东西,它能在很小的地幅内,实现自己的复合自主循环生产。科技发展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比如一种超级的太阳炉,太阳表面阳光强度比地球表面高4.6万倍,可以通过一种非光学成像技术,将地球表面的阳光强度提高到现在的8万倍,这使得人类可以不再依赖分布极不均匀的不可再生资源。那时候,流通和商业就可能失去其大部分意义。在这种以可再生资源为依托的小型智能化的制造业出现以后,在一个很小的单元里,人们就可以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要。随着这种具有更高剩余率的生产力的出现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现在人们谈论的最稀缺的一种资源,你的专栏里也提到过的,比如说以企业家为代表的管理资源不再稀缺。资本主义科层的、等级的控制体系也会渐渐失去其效能。民主不再是一种可笑的投票行为。不再是一种少数多数之间永远摆不平的虚伪说法,而是一种工作和生活中随时发生的真实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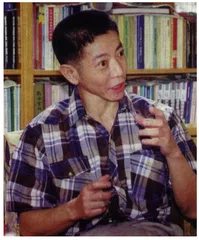
邓英淘,湖南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同期修完北大数学系四年的课程。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现为该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已出版《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走向现代化的抉择》、《邓英淘集》等二十余部著作。
罗:我想说的是,尽管你的描述让我激动和神往,让我想起古今圣贤对于理想大同社会,包括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描述。但是我仍然意识到,即使如你所说,这种基于高科技发展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剩余率很高的生产力以及循环往复的田园化生活方式会在将来出现,但他们也是在目前这种依赖耗竭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方式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不能越过目前的发展阶段,不能绕过西方经典发展方式而直接进入你所描绘的阶段。尽管我同意我们在进行发展方式选择的时候,你的思考非常有价值,但我仍然要回到原先的问题,在世界经济格局已经被别人安排成这个样子,在游戏规则已经被人家制定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不参加这个游戏?
邓:这回轮到我问你:现在有什么游戏规则制定出来让我们不能选择新型的发展方式,而一定要走西方经典方式的老路?
罗:比如说加入世贸组织的一系列规则,比如说电子技术发展造成的全球网络社会,中国可以不参加吗?还有全球金融市场开放协议、通讯市场开放协议等等,中国可能始终不加入,或者始终保持一种有限度地加入吗?
邓:尽管很多人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世贸组织的官员中却有人认为,中国并不一定需要加入世贸组织。你想过这是为什么吗?说到电子技术发展造成的全球网络社会,我恰恰认为,它给我提到的新型发展模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和更广阔的空间。要知道,信息的流动可以代替人流和物流,对于在一定地幅之内的,可以自主循环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单元来说,这是更有利的发展条件,而不是不利的条件。这种信息技术带来的无边界网络状态是一种对科层制度最有力的摧毁性力量。如果明确了非西方经典的新型发展方式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应有之义,对于中国和一切后发展国家来说,就不是开放不开放,而是如何开放,如何融入现代经济和如何使用现代科技前沿的所有成果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了。如火如荼的信息产业的革命在我看来是大批量生产方式或者说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最后一搏。西方也有人说,到下个世纪20年代,信息产业时代就过去了,将进人生物产业的时代。那时,根据西方经典发展方式制定出来的游戏规则不是能不能不遵守的问题,而是这个游戏在下个世纪将不再玩下去,何况其规则乎?
那种在较小的地幅之内,依赖较均匀分布的可再生资源的小规模的高效生产方式,在政治、经济、管理等各方面都将呈现出自主循环特征的自律发展的社会形态,确实是人类世代的理想,许多人都为它忘我地奋斗过。很多人不喜欢大批量生产的组织方式——因为它最不讲民主,但向往它高效率地创造了财富。有的人一生都在寻找和探索一种人人参与的,对等级和官僚制度保持警惕的社会形态,然而在当时找不到一种合适的载体和方法。现在,随着新世纪的来临,这种方法和载体已经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显现在我们面前了。
罗:你最近提出,中国经济想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不应去寻找什么新的增长点。你认为,通过加快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就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中国大量工业品加工能力闲置和城市数以千万计下岗、半下岗职工的问题。
邓:我是想说:现在我们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缺少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应该知道,原来起作用的那些增长点为什么现在不起作用了?我们现在彩电、冰箱等家电行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不到50%,这种状况已持续了近十年。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经济大萧条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然而说我们市场疲软,说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却是近几年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流程出现了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城市化进程滞后,第三产业发展不起来,农村居民收入不能进一步提高,没有购买力,导致本来可以高速增长的产业大面积“过剩”。所以我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投资方向要向加速城市化来进行调整,而不是向加工业、制造业继续增加投资。城乡经济流程的脱节和断裂,使得产业扩展没有空间。农民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有钱。消费人口的大多数如果不从原来的经济流程中走出来,就支撑不了工业产业的生产能力。根据我们的调查,我国现有录像机、照相机、彩电、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等十种家电产品的全国平均普及率才在20%左右,怎么就过剩饱和了呢?如果在近十年,城市人口能够与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同步增长,比如达到40%,45%,50%,还以上述家电行业为例,现有生产能力就不难达到合理的利用水平,当然也就用不着费心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了。
这里可以给出一个浅显直观的描述。1985年以前,农民平均每户10亩地,用这10亩地的剩余产出去交换“老三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每件大约需要200块钱,现在,交换“新三件(彩电、冰箱、照相机)”大约每件需要2000块钱,但1985年以来,农民户均耕地没有增加,单位产出有一定增加但可忽略不计。农民要想买得起这些耐用消费品,他们的数目要减少十分之九。这些减下来的人上哪儿?当然要进城。
罗:农民由于地不够种,或者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是在大量涌入城市。正在造成新型畸形的“城市病”。
邓:我说的进城,不是民工涌入拥挤的大城市,不是农民成为大城市的边缘人口。而是进入新建或扩建的城镇,是从农业流程中摆脱出来,是在新的城镇生活方式中产生的第三产业中成为就业人口。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我们现在的城镇人口少了将近两个亿。我们的城镇化不仅总规模不行,而且水平相当低。如果我们的投资方向能够调整到扩大城镇规模和提高城镇公用事业水平上来,光城市公用事业这一个行业,就可以多容纳1600万就业人口,整个第三产业可以多吸收5400万就业人口,进城的农民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供给满足自己的需求。总之,时代需要我们拓宽视野,从无与伦比的12亿人口的市场空间和产业纵深中寻求中国经济立于不败之地的发展之道。
①邓英淘著,中信出版社,1991年4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经济学再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