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的声音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君梅 李孟苏)

“哈雷”让李继业时刻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1903年,3个年轻人在美国中部城市的一间小作坊里,手工打制出第一辆“哈雷”,它看起来更像一件工艺品。此后,它得到改进并通过体育比赛证明自己。如果它一直沿着体育场跑下去,说不定能成为摩托车赛场上的“阿尔法罗米欧”(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生产的著名赛车)。但是,战争和生活的变革把它引到了另一条路上。
1947年7月,美国加州举行摩托车大赛。一些骑手突然冲向大街、冲向人群。这一新闻事件在被媒体竞相报道之后又被搬上银幕。在片中扮演约翰的马龙·白兰度和那辆摩托车一起成为焦点。评论家称:“约翰们难以用驾驶B-17飞机的手去超级市场打包。”他们大部分是刚从二战前线下来的退伍军人,无法适应战后“欣欣向荣的美国”,无法适应标准化的生活—从房子、汽车到发式、服装,他们从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都不愿融入这个社会。摩托车成为他们发泄的方式。或者说挑战社会的方式。在以往,在一个以貌取人的社会,劳动阶层为了掩饰自己真实的生活状况,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穿高档服装来显示“地位和富有”。但摩托车手们撕下粉饰太平的面具—刻意弄得破旧的巴顿式、麦克阿瑟式军用皮夹克和所向披靡的摩托车能显示他们生活道路的崎岖、坎坷。
马龙·白兰度和他的摩托车
记者对刘兴力的采访就从这部电影开始。“我听说过这部片子,好像叫《EASY RIDFR》”,刘说。他是中化公司的职员、“哈雷”发烧友,曾翻译过一本关于哈雷摩托车的书,所以对“哈雷”的历史如数家珍:“片中马龙·白兰度骑的摩托车实际是英国车-60至70年代,老牌工业国家英国的产品在美国人眼里还是响当当的。为什么后来人们把骑‘哈雷’的人叫easy rid-ers?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很多摩托车厂倒闭,到50年代,连老牌子‘印地安’也因经营不利倒闭了,‘哈雷’几乎成了仅存的名牌摩托车。当然,‘哈雷’是美国货,美国人对它更有感情,加上本地货的价格优势,‘哈雷’成了美国人购买摩托车的首选。事实上,很多美国人在二战前就有摩托车,那时的‘哈雷’是挺古典的—那时的生活是多么平和啊!但战后的人们,尤其是从前线回来的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变了,包括他们的摩托车。被改造过的‘哈雷’成为当时的时髦事物—摩托车把特高,骑手必须把手臂伸得老长,看上去像长臂猿,前义也特别往前探,总之摩托车的造型和骑下的姿势都十分夸张。这种车型被称为‘Chopper Style’,套用那部很有影响的电影,骑这种车的人被叫做‘easy riders’,直到现红。‘easy rid-ers’还成了一代人的代名词,现在全球发行量最大的一本摩托车杂志就叫《easyriders》,已有好几个语种的版本,中国版马上要出现了。”
不能改变生活至少还能改变自己的摩托车。摩托车手们的情感宣泄和个性的张扬并不是孤立的。“哈雷们”驶进60年代的西方,发现那个舞台挤满了革命的、反潮流的、张扬个性的人们。“早期颓废派”是一些年轻的幸运儿,他们的消费观是非主流的;“民族派”希望工业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乡村生活模式;“冲浪派”与自然紧密联系,主张刺激的享乐主义;“幻想派”产生的影响是让人头脑膨胀,并促使现代技术、新思维、新色彩出现,以此激活枯燥的生活……越南战争使这些雌不同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现代部落”最终止到一起。60年代中期,一个复杂的、反传统、信奉“爱与和平”的综合体形成—“嬉皮士”,成为当时各媒体和市场关注的焦点。很快,另一些主张个性解放的但不爱和平的“骑士”出现了。1969年夏末,一些冒失的摩托车手出现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的“滚石”乐队的音乐会上,幸好一些志愿者用免费提供啤酒的力‘式维持秩’,才避免了意外事件的发生。那些以“墨西哥人”自称的摩托车骑手是西班牙血统的美国人,他们穿磨得油光发亮的牛仔裤,长发上顶着车用头盔式的皮帽子,穿扯下袖子的粗斜纹布夹克和皮夹克。据说最理想的皮夹克是用约1英寸的小皮子一块一块拼接成的,并用链条、徽章、勋章、镀金纽扣做装饰,最引人的装饰物是十字架和纳粹的徽章—这可以解释成年轻人想“引入注意”。不过“墨西哥人”向公众发表宣言,希望人人都知道他们“站在魔鬼一边”,他们用疯狂的行为和魔鬼般的形象来证明他们到底有多坏。就在那场音乐会上,“光头派”也…现了,他们也不喜欢“爱和和平”,派是喜欢打斗,最初是在足球看台,然后是“嬉皮士打斗”、“同性恋打斗”……一路打下去,对每个“光头派”言,这些公开的暴力是自然的,显然他们不会考虑英国公众的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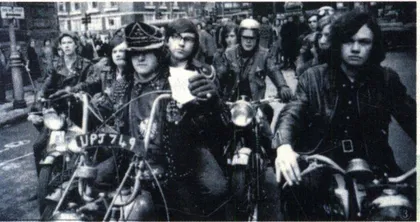
60年代的“墨西哥人”(西班牙血统的美国人)
“easy riders”这词让人联想起过往岁月里的许多人和事,所以现在的很多摩托车迷不愿意别人再这么称呼他们。他们更愿意告诉人们,他们的个性为何没有被效率、技术和信息淹没,机器和人的关系能不能很生动。
机器能教会人感受生命?
在人与人日渐疏离的今天,摩托车维系着摩托车友兄弟般的感情,李继业称他也在玩摩托车的过程中“长大”。
李继业今天真酷,身穿一身美式军装,头戴美军钢盔,身上的零碎(手表、腰带、墨镜)等无一不是“哈雷”牌。在没有“哈雷”车之前,李已经置齐了“哈雷”行头。现在他已在昆仑购物中心、蓝岛商场等开了四个销售“哈雷”服饰的专柜。生意不好。在“昆仑”,他放了辆1997年出厂的运动型“哈雷”,也是看的人多问的人少。
这丝毫不能打击李对“哈雷”的热情。他今天骑的这辆“哈雷—FXRS”是1982年出厂的,“这种型号的车外形并不漂亮,但性能好—美国警察都骑这种车”。他得意地说。
16岁时,李躲开警察,偷偷骑摩托车。到了18岁,他做的第一件“人事”就是去考摩托车本儿,花了135块5毛钱。
1990年,李知道了“哈雷”,那时全国车辆。“少年时骑摩托车除了心底对它那份说不出的真爱,就是很强的表现欲。像施瓦辛格那样骑辆‘哈雷’从台阶上冲下来。过盛的、疯狂的精力希望能通过摩托车的剽悍发挥出来。”
27岁,李有了自己的“哈雷”。“今年我30岁了。前一阵子,我老在心里想,我对摩托车了解多少?它是有生命的,它每分每秒都在颤动,时时刻刻有磅礴的生命力要迸发出来。”李竟从机器身上感悟到了“生命”。
“摩托车友时常会聚在一起,希望常听到彼此的消息。老了以后,大家或许会坐在一起谈年轻时的飞驰。”
他们中的一个骑士前几天死于一场意外。“大家都很难过。我们现在强调‘安全第一’—就是能让大家更长久地在一起。”
“麦当娜”的故事热闹和单纯
她是我们此次采访中唯一的女性,不是美国那个,是香港人,哈雷摩托车的发烧友。
“我喜欢让别人注意我”,她说。这个非常真实的“现由”先是促使她在10年前参加了香港“模仿麦当娜”比赛(她得了冠军,从此人称“麦当娜”,连她妈妈也这么叫她),后来,她又在别人的尖叫声中跨上了“哈雷”。
“因为像‘麦当娜’,香港最大的迪厅老板清我去他那里领舞。某天晚上,一位美国人对我说:‘你们应该把哈雷摩托车开到舞台上来,哈雷啊,世界上最棒的摩托车。”
“麦当娜”和同在一家迪厅做DJ的男友斯蒂文利用哈雷摩托车开了个疯狂的Fashion Show—“哈雷”呼啸着歼上舞台,钢管的蓝光、斑谰的彩漆、身穿哈雷服饰的靓女、音乐、劲舞、记者的闪光灯,每个人都在尖叫……
此后,他们用“哈雷”在迪厅举行了多次Pany。
“麦当娜”加“哈雷”,这样“酷”的组合在香港是非主流的,香港娱乐界迎合港人传统文化,喜欢捧“甜姐乖妹”。至于摩托车,香港人只骑“小绵羊”,一种小踏板摩托。所以,“麦当娜”在用“哈霄”演出之前,和男友满香港寻找“哈雷”。当时香港只有一个小老板做“哈雷”代理商,生意极其清淡。
1990年,卡拉OK在亚洲飞速流行,香港的迪厅垮了大半,“麦当娜”失业了’。为了生计,她开了间很小的店,专卖哈雷服饰、模型加头盔。这是香港第一家专卖哈雷服饰的店。
“麦当娜”继续在香港扮演传播“哈雷文化”使者的角色。很多人买不起哈雷摩托车,但表现“个性”还有别的办法,比如穿戴“哈雷”的行头—帽子、手表、挂饰。逐渐,小店有了代理哈雷摩托车销售的业务,斯蒂文学会了维修、组装大排气量的摩托车,“麦当娜”考了牌照,有了自己的哈雷摩托,她和斯蒂文一共有6辆,更多的香港青年买了“哈雷”—他们的店现在成了“哈雷”骑士的俱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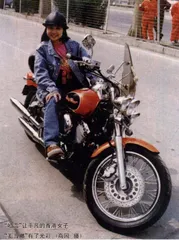
“哈雷”让平凡的香港女子“麦当娜”有了光彩(商园 摄)
组织一支女车手队—这件事让“麦当娜”再次成为焦点人物。
“一个朋友出嫁,我们去迎亲,轰动极了。好多人指着我们说,畦,女孩子骑这么大的摩托车,他们追着我们看,像看明星一样。车一停下来,就过来摸我们的车。1995看我带一队鬼佬(外围人)摩托车手.参加番禹美食节,内地警察为我们开道,很威风。当地人请我们吃龙虱,害怕,都不敢吃。”
现在的“麦当娜”在香港是明星。她怀孕时大肚子骑摩托是新闻,她频频在电视上露面,她在杂志上开专栏“猫猫走天涯”……哈雷让一个平凡的香港女子有了光彩。
追求“机器品格”还是打碎它?
90年代,摩托车迷的反叛比以往要温和,以至那些名利双收的上流社会人士和境况蒸蒸日上的新贵也开始热衷玩摩托车,以“玩野扮酷”为荣。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印尼国际银行的副行长奥基都穿着笔挺的西装上班。但在周末,他就会换上镶有铜钉的皮夹克,高级轿车也换成哈雷摩托车。在印尼,不少E层阶级的人都对哈雷摩托车着了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政府官员、高级军官都用威风凛凛的哈雷摩托车炫耀他们的成功。据说苏哈托总统在任职期间喜欢在总统府的院子里驾驶哈雷车兜风。
现在在雅加达有一个摩托车零件厂主也是个哈雷迷,他表示,骑上摩托车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利于生意上的沟通。其他的商界哈雷迷也认为,在摩托车上“办公”和在高尔夫球场上淡,生意一样有趣。虽然骑摩托与公众见而并不正规,但印尼的将军们认为“这样能更接近百姓,了解他们的想法”。
谁都知道,美国哈雷摩托车价值不菲,所以骑“哈雷”能接近百姓的想法听起来很可疑。真正的解释就像把西装换成夹克那么简单—生活需要变化,人不能在追求机器品格的过程中真的变成机器。
这让记者想起90年代初台湾的一位心理学家创作的短篇小说《情人》—金螺K刚刚过了18岁生日。18年来,这台大型情报处理机为某情报机构立下了汗马功劳,它高效、无差错、不知疲倦。操作人员为此要昼夜倒班。男操作员爱上了一同值班的姑娘。姑娘难以琢磨,自己又内向—男操作员无意识地把心里话敲到金螺K的键盘上。显示屏出现了一行字:“请定义‘爱’。”最终,金螺K在帮操作员创作了无数情歌之后明白了“爱”。但从此它频频出错,显示屏上出现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它爱上了近来与它合作的另一台机器,它已经沦落在非理性的人性的边缘,丧失了卓越的机器品格,“我不配再做机器了”,它说。
在刘驰眼里,他的哈雷摩托车也是有缺点的,因而更人性化。
“世界上不会有相同的‘哈雷’,同一型号的哈雷车出厂后,都会经过车主的改装,改装的过程是自己潜在愿望的过程。”
记者从侧面了解到刘驰是“老三届”,返城后在公安局工作了几年后,辞职开了摩托车汽车维修部。凭着维修和驾驶进口大排量摩托车的技术,他的名字在京城摩托迷中叫响了。
刘驰有一辆“哈雷”,他把它当成多年的朋友,爱“他”的优点,接纳“他”的缺点,甚至把缺点看成“可爱的个性”.,
“摩托车足拟人化的机器,哈甫一戴维森尤其是。哈雷车质量很好,材料用的全是好东西,这是大国(美国)的风范。可技术水实在不敢恭维,多少年来没有什么变化,大毛病没有,小毛病小断,骑快了震得浑身直颤.但它没钉因为选用最优质的材料受人赞赏,也没有因为技术落后遭人唾弃,它永远不变的弄双缸发动机造型,震天动地的排气 噪声是哈雷永远的专利和永恒的魅力”。
刘驰说:“不能直忍住缺陷的人不是真正爱车的人。”
1994年前后,“哈雷”的销商为了促销,发行了一张名为《Road Music》的唱片。“它的主角是‘哈雷’的声音,伴奏的是一把吉他。我那时正好被公派到美国,在驻地能找到的是一架旧唱机,虽然音质不好,但那特立独行的声音深深吸了我这个异乡客。”刘兴力陷入沉思。
追求机器品格或者打碎这种品格—这可以说是20地纪人类生活的一个主旋律。追求个性自由是生动而美丽的。
但是,“责任”呢?喜欢张扬个性的摩托车迷几科无一例外地讨厌“消音器”,据说,从技术层面看,这有助提高发动机的功率,更主要的还是个人的宣泄。大排气量和高噪声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真的事不关己(高尔人球场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在上面走来走法的“少数人”会不会为此不安)?1998年的世界环境日(6月5日)人们听日到了很多坏消息—有些是工业化、商业化利欲熏心的必然结果,有些则缘于个人的为所欲为。如果不尊重社会,社会为什么要尊重你的个性?世纪末的人如果不重新思考“责任”,可能就会“走得太远了”。 摩托车哈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