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被称为“思想事件”的话剧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4月,春暖花开,希望的季节。4月,《三姐妹·等待戈多》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这部由两位大师的两部名作重新结构而成的戏包含的是个9月的主题—等待。
喧闹的今天,无论站在何处,契诃夫对于我们都是一个遥远的名字,他的剧作《三姐妹》自1901年首演以来,已有近百年的时间流过。虽然它一直以经典之名在世界各地上演着,但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已久违了,了解它的人大多不是通过戏剧经验,而是通过剧本得到的文学知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首演于1953年,同样,了解它的多不是观众而是读者。如果在首都剧场演一出《三姐妹》或《等待戈多》,对于观众当然是一次风雅而品味高档的欣赏机会,留给导演的余地就是再次诠释一部古典精品或荒诞名作,引来的议论可能会是一与导演手法、演员技艺、演出效果相关的戏评。
但是由林兆华导演的这部《三姐妹·等待戈多》分别把两位大师的作品大卸八块,又做重新结构,此中蹊跷似乎已不完全是戏剧之事,而是戏剧之外的话题了。
在这部戏里,《三姐妹》的基本内容是完整的,但是被处理为彻底的内向。事件、人物、性格、冲突都简化为叙述,我们在戏中看到的三姐妹在舞台上几乎没有身体动作,只有一个希望—等待的符号,这种没有动静地谈论的希望充分显现的竟是无望。语言是19世纪末的语言,却没有那时的浪漫。希望的情绪被消解在静态的语调中,只剩下无行动能力的等待。舞台设计把三姐妹置于一个类似孤岛的地方,更加深了无能为力的印象,别的声音、人影都在“孤岛”之外游移,使三姐妹的无能为力又成为无法被拯救的,同时,她们的等待也成为不能被影响的。《等待戈多》的部分在戏中被拆得多一些,而且也与我们读剧本的印象很不同,这里的等待充满了动感,两个流浪汉一上来就是淌水而来,舞台上水花四溅。两个主人公完全喜剧化。虽然他们在循环往复地等待,一趟一趟地来等待戈多,观众直替他们绝望,可他们两个似乎挺高兴的,不像三姐妹那样明确地显示出生活的无法忍受,他们每天像上班一样地来等戈多,没等着也不着急,而且等着也是等着—说点什么呢?逗逗闷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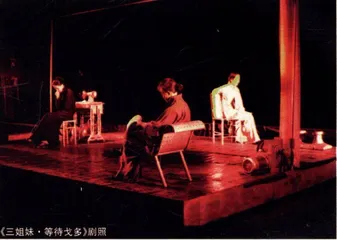
两种等待,一张一弛相互穿插,并且由今天看100年前的等待到50年前的等待,整个戏描绘出一条穿过百年历史的精神线索。这部戏里的《三姐妹》不浪漫了,《等待戈多》也不那么强调荒诞了。这种等待是谁的等待?是不是挺像当今世界的精神面貌?我们肯定不能说现在是浪漫的时代,因为人们很务实,而且现在的荒诞感也没有50年代那般的明显严重,因为人们都很忙,计划一大堆,并且目标很确切。但是等待的主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这个主题太一本正经了,而且在戏剧形态上,导演似乎有意让观众认真听大师的语言,所以该剧共演出19场,上座率不足50%,据导演林兆华讲,每场都有人中途退场。这种效果好像正对应了戏中所揭示的精神面貌。但是也正是因为它的主题与今天生活的某种联系,引起了另一部分人的热烈反应。《读书》杂志是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杂志,该剧上演后,它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讨论一部上演话剧对于《读书》大概是唯一一次,至少是第一次。《读书》主编汪晖在评价这部戏时,讲了他的复杂感受,一方面是对戏本身的改编、诠释有一些疑惑,比如,现在虽然不能再用浪漫主义诠释《三姐妹》了,但是也不见得要用《等待戈多》来诠释它,比如,《三姐妹》中生活可能将发生变化的感知是有的,但是其中的现代主义解释让人感到不满足。但是这部戏用两部不同的戏来解释今天世界的变化,试图理解我们这个既深沉又热闹的时代,使得这个戏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思想事件。
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对此戏予以充分肯定,一致的口吻是:“这是林兆华最好的戏。”评论家李陀说:“林把《三姐妹》完全抽象化、类型化,排除了其他多种可能性,只突出了等待的主题,并且是一种不动的等待,与《等待戈多》中骚动的等待形成强烈的对比。”剧中有一棵小树极为引人注意,李陀说:“小树的处理效果好—小树很矮,无聊的人想上吊往哪儿吊?这是真实的无奈。”也是这棵其矮无比的树被汪晖认为“是对贝克特荒诞感的颠覆”。这一切都直接指涉着当今世界的生活状态,而不是19世纪末的,也不是50年代的。
专事戏剧研究的沈林表示,这个戏多少有点掉书袋,因为要看懂它,观众必须有戏剧准备,必须读过两位大师的剧本。何志云也说到这一点,他的18岁儿子从小看林兆华的戏,一直喜欢看,但对此戏有点不喜欢,回家看了剧本之后,说有点意思。虽然如此,但他们一致的印象是这是一部有开创性的戏,是个有饱满精神内容的戏。
然而上座率问题还是被提出来了。评论家申慧辉认为,只要把戏放到大剧场演就得考虑观众,不一定是迎合观众,但必须认识观众,她以为林兆华的这个戏是脱离观众的。通过演员之口说出的台词缺乏表现力。所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这个戏是失败的。
或许从上座率上看,申慧辉说的是实情,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事件”,这样的上座率以及知识分子对它肯定也构成了“事件”的一部分。等待是人类精神的深刻主题。加速度发展的今天,忙碌的人们和热腾腾的未来学都暗示着今天的人们在还没过完今天的时候早就等着明天的到来。在表面上似乎很自主的生活中,我们真的有选择的能力吗?我们等待的是什么呢?贝克特不能告诉我们,林兆华用了两个戏也不能告诉我们,未来学家告诉我们的又不太让人相信。
抛开这一切,作家余华说:“很喜欢这个戏。”这又是戏中之事了。导演林兆华如是说:
—导《哈姆雷特》,我不认为是莎士比亚的,是我的。导契诃夫的戏,我也不认为是契诃夫的,是我的。
—不能排演前找专家。比如排莎士比亚的戏,我不能请莎剧专家,那样,我一个逗点都不能动了。
—(看过《三姐妹》和《等待戈多》两个本子的人,弄不清怎么把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我费了大劲交织在一起,你拆它干什么呀?
—前年我得了“缠腰龙”,但不是缠在腰上,是缠在腿上。我问医生这怎么回事,医生说:“现在发展了,哪都能乱缠。”
—戏和小品的争论是扯淡,谁爱看什么看什么。
—什么“戏剧新方向”,你排你的,我排我的。
—把荒诞的处理为不荒诞的,无奈的事情处理成不无奈的。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人们都在期待着什么,又不知道具体期待的东西,这是-无奈,荒诞,但同时又都个个欢蹦乱跳,兴高采烈的。
—我想起大导演戈达尔的一句话,他说:“我想排一部戏,一群演员在那里朗读大师的语言。” 爱情电视剧剧情电视剧林兆华三姐妹戏剧爱情电影智利电影等待戈多家庭电视剧话剧韩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