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6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舒木禄 徐斌 翃凌 布丁)
为可能的意外而忙
文 舒木禄 图 王焱
老郭是个忙人,找他的人特别多,家里的电话终日不断,搅得他无片刻安宁。这些打电话来的人多数是请他帮忙的,因为他是个能人,还不会说“不”。
终于,有一天我给老郭打电话,怎么也拨不通,没人?不可能一整天不在家。夜里拨,还是没人。后来老郭说,他把电话线拔下来了。以后,要想找他,就先Call他,然后等着他回电话。这岂不麻烦?老郭说:“没办法。”
怎么没办法?如果你忙,电话响了你别接,不就行了吗?
不行!电话声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像被抽去了,人就猜不出电话将传给你什么信息,没准是好朋友请客,没准是女性崇拜者,没准是记者来访,没准是父母大人生病了,没准是前妻来吵闹,没准仅是个来请帮忙的,总之,完全没准。一个电话声包含无数种可能,你说你接不接这电话!
这就是电话的诱惑力之所在,你猜不透它,同时它又潜在地拥有提供重大信息的能力。
现住流行BP机,流行E—mail,像老郭那样坐在电话机旁也不用它接收信息。因为BP机,E—mail比起电话有两项重要功能,一是可以“随时随地传信息”,这是摩托罗拉广告承诺的,不管你身旁是否有电话;_二是可以“不”随时随地传信息。你传你的信息,我想理就理,不想理可以不理,但又什么都不会耽误。
可是,大多数不像老郭那样不会说“不”的人还是很自在地用着电话,不忙的人能显出不那么无所事事,忙的人可以摆摆谱,在电话里拒绝人又方便又有气派。
电话一响,为什么人一定要去接?不管忙不忙,哪怕是正在极不方便的时候也有“步步高”无绳电话跟随着。这有点像人攒钱的心态。
占有钱比占有实物能给人更多的刺激或富足感,尤其是对不那么有钱的人。虽然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需要用钱换的东西,但如果攒着钱不花,一万元钱的拥有能幻化出比同等价值的实物多的多的“享受”拿着一万块钱,你可以买一个大大的舒服的沙发,或买一整套雅兰诗黛化妆品,或一套过得去的音响,也可以买身西服帅一把,要不就买一套二十四史,加金庸全集,一直想买都没钱买呢!剩下的钱买莎剧全集,外加几本大辞典。但是,这钱不能花。你只要花了就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件,就丧失了那么多种选择。
把电话声和钱放在一起也许是有点牵强,但我想,它们的相同之处就是,在人的心里可能性永远大于现实性。人喜欢迎接意外的可能,也喜欢设想可能,喜欢有选择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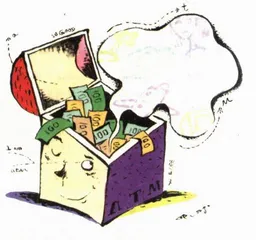
我们会不会记录自己的语言?
徐斌
一天我偶然翻了翻字典,不经意中竟然发现了好几个平素常说,也常听到,但从来不会写的字。比如我小时候把花茎、树枝上的刺叫做“gezhen”,但是从上学以来从没有人教给我它们是怎样的字。普通话里人们是把它叫作“刺”的,所以我也就管它们叫刺了。若不是这回发现,我还不会写呢。
记得我当年刚开始读英文系,抓过来啃的第一本原著是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书中黑人使用的方言土语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非常感叹英文的灵活,可以把土话拼得活灵活现,又颇为自己的汉语水平感到担忧,因为我写文章时根本就写不出日常用的一些口语词,更不用说一些方言词了。
我的读书过程有点由远及近,由古及今。说来令人害臊,我开始读《红楼梦》已经老大不小,挺晚的了。由于学英文的关系,读的时候总是带有比较的观点。撇开文学性不谈,就语言方面来讲,《红楼梦》是我的方言土语宝库。在那里边,我学到了不少口语以及方言词的写法。所以我觉得《红楼梦》是本好书。每每读到某个方言词,我总和自己的方言对照一下。方言使我觉得和书中人的关系很密切。
于是我想到我受过的教育。我认为我们的语文教育太注重普通话,太忽视口语和方言了。现今,仅仅是受过小学教育的孩子,写起作文来,就基本上杜绝了口语词汇了。我的个人经历即是如此。还是学生时,我有时候放假回到农村,跟爷爷奶奶住一段时间。我发现村里许多人说出话来是鲜活而有趣的,然而我自己既说不出来,也写不下来。但是读《红楼梦》,读字典的经验告诉我,祖先早就造好了那些字,只是我不曾学到,不会用。听着他们的言语谈吐,我感到我的言语能力被修整得太过分了。我所说的话以及写下的文字,和众多受过类似教育的人说的话及写下的文字,非常的类似。风格,对于我们这种万口同一的话语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受教育的大多数人的话语的风格差异,不过是像成衣店里的服装,仅仅是颜色号码略有不同而已。
我一直感到我不会很好地使用汉字来记录自己说的和听到的话,是一项很大的欠缺。而我们的语文教育很少涉及这一领域,是一更大的欠缺。语文教育似乎太强调标准!规范,忘记了语言是大众的创造,是约定俗成的东西。
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在读书看报的时候,实在是该问自己一句,我会用文字记录我的语言吗?
版本时尚
翃凌
一家电子行业的权威报纸上,用大标题写着:体验Windows98—Win98终于如期而来了。但放眼望去,周围还有人刚从Win95“扫盲班”毕业。而对Win98不知他们会作何感想——那感觉很像身穿过时衣服的乡下姑娘面对时髦女郎。
不觉中扯到了女人的衣服上。据说世界上变化最频繁的是女人的衣服。但现在看来,如果“微软”继续把“窗户”一扇接一扇地开下去,迟早有一天,“窗户”的变化会超过衣服的变化。届时,比尔·盖茨的众多头衔上还要加上一条—时尚大师。
无论如何,新款(不管是时装还是软件)上市了,买还是不买?、当然有人立刻就买。时装—特别是一些名牌,都有着一批自己品牌的忠实追随者。在国外,甚至有“Chaneler”、“Cuccier”等词来专指那些香奈尔迷和古奇迷。相信在不久的将来“microsofter”一词也会应运而生。面对Win98,“Microsofter”们的急切心情恐怕只有“Chaneler”们才能理解。
但也有一些女人用另一种方式来对待买衣这件事。她们或许也穿名牌,但不乏在打折时买衣的经验。买打折品是有风险的—过时落伍的风险。但只要有相当的眼光和感觉,风险也并非小能避免。毕竟,衣服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最有名、最时髦、最昂贵或最廉价都不是首要条件,最需要、最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自然,上述“买衣经”并不完全适用于软件消费。因为时装会随风水流转,而软件的版本却是日新月异步步高,最新意味着最好。但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的一个朋友得到了一台被办公室淘汰下来的苹果机,当时她只当是捡了回破烂儿。待她经人指点学会使用Machintoshi之后,发现这种几年前问世的软件有着许多独到之处—比如可以给她的儿子渎英文。在此之后,她开始到处宣传Machintoshi其实并不比Windows差。当然这只是她的个人感觉,但对于一套软件来说,使用者的主观感觉难道是不重要的吗?想来“最新=最好”的推论有时也难于成立。
写到这里,我想我应该闭嘴了—想必读此文的内行人士的嘴已经撇到了脑后。把Windows与衣服扯在一起说,正可谓是百分之百的“妇人之见”。
(本栏编辑:苗炜)
把事情干漂亮
布丁 图 王焱
几年前,曾有过一阵“第二职业”的风潮,我当时的感觉是北京街头猛然多了些小摊儿—地上.铺一块塑料布,摆上拖鞋之类的东西卖,还有修自行车的摊儿。一般都是在晚上,一个中年人拿着几件简单的工具就支起了摊子。
我的一位邻居胖哥,就支起了这样一个修车摊儿,有个晚上,我就在那摊子旁边乘凉。那个晚上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桩生意是有个中年妇人推着自行车来让胖哥上一颗螺丝钉,那颗螺丝钉的部位很特别,在后挡泥板上,要想把螺丝钉上紧,需要足够灵巧和纤细的手指,胖哥的手指很粗,弄了半天,螺丝钉总是掉下来。胖哥就问那妇人:我把螺丝钉上紧一些好吧。妇人听罢一脸困惑,那意思是说,你还没弄上去呢,谈何紧不紧,但她还是表示:好好。
胖哥听罢,就开始松自行车后轮上的所有机关,原来他是要把后轱辘全拆下,这活儿他干得熟练,还没等那妇人有机会表示异议,后车轱辘已然拆下,这一下,后挡泥板上的那颗螺丝钉就很容易安上了。
安完螺丝钉再安后轱辘,但这还不算完,胖哥如果到此罢手,难免会让人讥笑:安个螺丝钉还这么费劲。丁是他问那妇人这自行车是否还有别的毛病,妇人不识趣,只说没有了。胖哥闻听此言不再言语,抄起一块抹布将自行车后轱辘擦了个干净,然后才说:好了。
妇人问:多少钱?胖哥答:一毛钱。于是妇人交了一毛钱,推着前轱辘很脏而后轱辘发亮的自行车离去。
我在旁边目睹此事的全过程,当时的想法是:胖哥的手艺实在不怎么样,为了一毛钱还要拆车轱辘,累得满身大汗,实在太笨、太可笑。
但如今我回想起此事,却深深地为胖哥的职业道德所折服:他忙活了半个小时只收了一毛钱,而且将那颗螺丝钉上得非常之紧。不仅如此,他还将后车轱辘擦得非常之干净,这不是一毛钱收入所应付出的服务呀。
要解释清楚这件事,就要说胖哥有个概念—把事情干漂亮的概念,为了颗螺丝钉拆后轱辘,这事情干得不够漂亮,顺手把后轱辘擦得非常干净,就表明:那个后轱辘并不是白拆下来了,它至少变得比以前干净多了。至于不擦前轱辘,也有道理,因为胖哥要做的毕竟是上紧一颗螺丝钉,而不是擦车。
我当年看胖哥擦后车轱辘时才刚刚工作,工作了这些年后,我发现:把事情干漂亮这一概念在许许多多人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树立起来,正因为此,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才有日渐丑陋的感觉。有许多人,于事只求凑合,而没有完美主义者的劲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