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过剩时代的稀缺资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坤)

低通胀与廉价原料
1997年12月30日,伦敦铜,这一标志着世界铜产品总供求的敏感商品再次大跌,创纪录地达到1720美元/吨。这一天,上海期交所的铜价也达16400元的水平,无论远在秘鲁的矿主还是中国的生产企业,都会记住这个日子,因为这一价格与一年半以前一件震惊世界的事件相关。
金属中,很少有像铜那样一下子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那是1996年6月,随着伦敦商品交易所里的铜创出了近3年来的低点,一桩交易丑闻暴露出来。住友商社号称“5%先生”的金属部门主管滨中泰男因擅自交易,致使公司损失18亿美元,创下渎职记录。
6月25日铜价创下的低点是1745美元/吨,走势图上,此段下跌犹如一座瀑布。铜价自1995年8月的3000余点先是缓缓流下,进入1996年4月,便从2600点陡然跌落。来自全世界的空头们欢欣鼓舞,他们赚了大钱,而那些钞票正是住友商社的。
很难说滨中泰男缺乏判断力。自从住友认输离场后,伦敦铜又开始稳步上升,到1997年6月,铜价又回到2600美元/吨的水平。不过,如果从更长期的尺度看,滨中泰男无疑错误地估计了90年代后期的经济形势,时隔半年的12月30日,伦敦铜再度向狱中的滨中泰男证明,他的错不在于他的钱不敌空头,眼力也有差距。
滨中泰男处境不妙,全球大大小小的厂家更是前景堪忧。同样处境不妙的还有海南的胶农和泰国的种植园主。1995年橡胶价格还在每吨15000-17000元之间,1997年末商人们就看到了不足7000元/吨的胶,这几乎是整个90年代的最低价格,若再加上通胀因素,胶农们的生活恐怕要回到70年代的水平。空头们扬言,目前7400元左右的价格很可能还要狠跌一下,泰国为换汇正以600美元/吨的价格大肆抛售。泰国的庄园主更惨,加上货币贬值,他们的收入还不及原来的1/30
熟悉了90年代前期只涨不跌的死多头们也深感落伍。籼米曾连续出现过5个跌停板,咖啡的价格从百公斤1400元升到4500元又跌回到1100元。每10%的价格波动都会使交易者倾家荡产,而由牛市转入熊市的不适应已把众多大户扫地出局,商品交易所门可罗雀。
商人们寝食不安。消费者却从中得到实惠。从全球范围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同时走出通货膨胀的阴影。在美国,投资者看到了50年来最好的经济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从1979年到1995年,通货膨胀率从没有一年低于25%,现在则降到15%,而在1992年通胀率高达700%的转型国家通胀率也降到28%左右,为全球政府和经济学家期盼已久的低通胀时代就这样不经意间到来了。
人类经历的上一个低通胀时代是二战后到70年代初,在布雷顿森林协议确定的固定汇率体制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维持了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通胀率在5%左右,经济增长也在这一水平上下。这段时间被称为战后工业国的“黄金时代”。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与低通胀相伴是一种理想的增长模式。
低通胀首先得益于原材料的低价格,石油被跨国公司垄断,来自中东的廉价原油汩汩流出,滋养了西方一个时代的繁荣,而资源的所有者和劳动者却未能得到实惠。7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起的石油涨价对西方的经济理想境界给予致命一击,10年中油价及其他能源产品价格上升十余倍,威力所及,非燃料产品和一些农产品也摇身一变,引得商人以昔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交易。
20年一轮回。七八十年代的超级富翁以油田继承人为主,阿拉伯的王公们更是不可一世。现在,世人的目光已从他们堆满黄金的宫殿转向大学校园般的硅谷,那些不修边幅的电脑奇才成了财富的主宰。对于耗能机器,凭借技术创新,人们有了说“不”的权利。一台北欧产的普通冰箱,20年前耗电量是现在的五六倍,据说,不久又将下降一半。这还比不上信息业带来的效益,改用光纤传输后,信息传输量以几何级数上升,把铜矿主们搭信息快车致富的美梦挤成泡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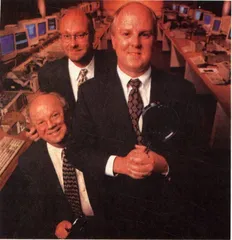
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2(X)家优秀小企业之一的Ontrack Data公司三巨头:总裁约翰·佩斯(坐)、副总裁加里·史蒂文斯(后左)、执行总裁迈克·罗杰斯都是高科技领域的顶尖人物,但在这个领域人才似乎永远短缺
最稀缺的资源
曾经,通货膨胀不像现在这样人人喊打,风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就试图通过政府干预,以政府的财政货币手段调节总需求水平,扩大就业,缓和经济波动。“菲力普斯曲线”认为经济生活存在一成不变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如是,政府则应在失业率上升时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创造就业。
政府的需求除了加税,唯有滥发钞票。无论如何,通胀都将应运而生。
人力也是种资源。在新的宏观经济指导下,发达国家开始了政策调整,失业要解决,更要解决的是如何就业。英国和美国以改革劳务市场为目标,增加人员流动,提高劳动资源对总需求变动的反应弹性。1996年,英美的失业率分别为5.4%和7.6%,通胀率则低至2.9%和2.4%明显走出“滞胀”。而劳工市场相对滞后的欧洲大陆国家的失业率则在10%以上。
低通胀时代,人们看到了另一种资源短缺。据《商业周刊》载文,信息革命的发展速度正超过其决定性的原材料—人才—的成长速度,造成软件人才的严重短缺。仅在美国,就有大约19万个高技术职位空缺,其中多数是编程人员,而美国占价值3000亿美元的全球软件产品和技术服务市场的2/3。
高技术公司正进行着一场网罗人才的竞赛。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编程人员都成为人力资源部门的目标,另方面他们又互挖墙角,将别公司的人才拢到自己旗下人力资源公司是一家类似猎头的公司走投无路之下,他们等在诸如“苹果”和“西屋”这样一些处于困境的公司门口焦急地守望,眼巴巴地等待编程人员和科学家送上门来。
人才为何如此短缺?90年代初,技术公司还没有理由为此担心,现在,人们似乎突然发现了有那么多领域需要信息化从东京到底特律,汽车制造商们正忙着将更多计算功能塞进他们的汽车和工厂中。银行、经纪行和电话公司争先恐后地抢入方兴未艾的在线服务。在世界金融中心伦敦、东京和香港,各银行正在安装大批新系统,以便适应欧洲统一货币和日本的金融解禁。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在加班加点工作,以便找出那些潜在小故障—单一项“2000”年代设置,就需要大批技术人才。
1984年,美国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为4.8万,1996年仅有2.6万。很多天资很好的年轻人认为编程工作太枯燥乏味,选择了其他职业。一台移动电话大约需要30万行程序编码,而即使顶尖的程序员有时一天也只能编出10行代码。为罗致人才,一些公司正在给中学数学教师和赋闲在家的核物理学家提供编程培训。他们还请现已退休在家、以前为主机编写程序的人重操旧业。网景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玛吉·马德说:“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像疯了似地寻找这些家伙。”
“微软”也在万维网上招聘员工,为获取人才而迅速收购新成立的公司,单1996年它就收购了大约20个公司。“微软”估计,它的服务伙伴目前缺少4.1万训练有素、能安装微软产品的专业人员。这迫使“微软”介入与教育有关的生意。根据一项名为“技能2000”的行动计划,“微软”正打人世界各地的350所学校和学院,它在这些学校制定了将培养出更多编程人员的课程表,1997年上半年,“微软”培训了3万人。
短缺已经迫使工资抬升,美国的软件人员的工资平均上涨13%,在这个卖方市场中,存在着明晰的价格体系,金字塔尖上的是眼下正火的因特网技术公司的编程员,他们拥有大量的优先选择权。稍次的是最高层的咨询人员,其年薪为8.5万到40万美元,这些人在世界各地穿梭,建网设站。在印度的班加罗尔,编程员的起薪是7000美元,人们预计,这一价格也会像70年代的石油价格一样暴升。
软件业普遍把印度看成他们的沙特阿拉伯,那里每年有5万学生从计算机专业毕业,这个数字已使印度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料储备库。随着全球技术方面的开支猛增到3万亿美元,印度的人才供应已经不够,印度软件业联合会的执行主任德旺·梅赫塔预言,不出10年,印度自己也将发生编程人员短缺。目前,印度已失去最有才华的编程人员。声誉卓著的印度理工大学计算机系的毕业生已有许多移居国外,而印度并非唯一的受害国。
高科技公司正以雷达的精密和速度搜索世界各地。中国有可能供应部分人才,但今后10年它自己的需求会更大;俄罗斯也有问题,它的技术人员很少会英语并理解商业应用软件专家担心,人才奇缺与工资上涨很可能威胁到软件业自身的发展,进而损害全球技术体系。
当阿拉伯世界的原油夜以继日流向世界各个角落时,人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当然,这种担心最终也会像“资源悲观论”样成为历史,那时人们或许已有了编程机器。 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