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修理、欲望和赵九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李孟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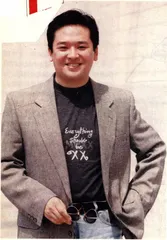
生活中的赵九泷,能和修理联系到一块吗?

正在主持节目的赵九泷(商园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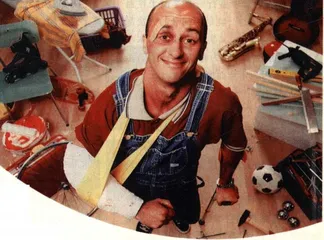
听说赵九泷这个人时,想象中我以为他是牛仔裤格衬衫身体高大强壮美国乡村好爸爸的样儿。如今,手工活儿干得漂亮,爱修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的人,怎么想怎么不像90年代的年轻男人。
和赵九泷相约的时候,他说他在北京电视台工作。可能是扛摄像机的吧,我想。电话中他要求我拟好采访要问的问题,以免准备不充分占用他太多时间。
采访赵九泷的那天,是比尔·盖茨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日子。我和一批“追星族”们被警卫拦在场外,不同的是,我在等赵九泷。盖茨走了,终于可以见到赵九泷了。我吃惊地被告知,那个头发打了摩丝、穿浅色西装上衣蓝衬衣系深蓝碎花领带、文艺腔十足地在摄像机前采访大学生的小伙子是赵九泷。他居然是电视节目主持人。
赵九泷主持的栏目是《电脑演播室》。他先后主持过五六个栏目,最火的是《厨艺大观》,看上去很福相的赵九泷向广大市民推荐美食,没有不火的道理。
坐在赵九泷杂乱而有序的工作间里,听赵九泷谈“修理”当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倒也很有趣味。
“修理”的概念不能划得太狭隘。人之所以有修理的欲望,跟人的本性有关—求知欲,征服欲。这两种欲望表现在我身上,就是我见着什么新鲜东西,总是想拆开来了解它是怎么回事,并不是仅仅把它修好。
这似乎是天生的,父母说,我小时候的玩具没有一件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没买3天就全拆了,我当时很有道理:我要看看里面是怎么动起来的。
现在我修理的兴趣仍在于此。如果有人搬来一台电视机让我修,告诉我哪儿出了毛病,我毫无兴趣—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毛病何在,甚至可以精确到是哪一只管子坏了,到商店花人民币16.5元就可以换个新的,自己装上得了。如果按照我说的做了还不行,我就愿意动手了,这说明我以前的判断错了,或者这是新机型、新问题。我最有修理冲动的是见到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微型录音机、液晶电视什么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知识积累的渴望。
如今修理离人们越来越远,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的观点:什么东西厂家都提供质保期和很好的服务,过了质保期,式样不时兴了,功能落伍了,那就不修它,扔掉,重新买新的。其实,美国现在有一种观点,“do it by myself”,提倡自己动手修理家中的坏电器坏家具,甚至自己打个橱柜什么的。当然,美国人成天花样百出,中国人完全不必理会他们。但真正喜欢修理的人不会因为修理时兴或不时兴而改变他对一件事物的好奇心。他会和大家一样不修彩电了,赶去修VCD机。一旦他知道了VCD机是怎么回事,心里会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当然,当几种VCD机的构造都了解后,他就不会再有兴趣修理VCD机了,除非这人以修理为业。
心灵手巧有很大的遗传性。我父亲年轻时就爱干手工活儿。他做的毛主席像章装上电池,里面的光芒就可以转动。他在援越战场上,仍忘不了捡来美军飞机的残骸,烧化了铸成小梳子小铲子,用钢针打上字,带回国作纪念。
从幼儿园起,我就不能忍受把手背在身后,手里需要玩点儿东西。10岁时我开始装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晾衣服的绳儿是天线,暖气管子是地线,每月2元钱的零花钱全用来买零件了。装过9寸的黑白电视机(这是当时业余爱好者的最好成绩),装过电子琴。这种过程的魅力远远大于结果。因为有一门“手艺”,我大学时生活得不错。我和另一个同学开了间下设在学生会的修理部,免费为全校师生修理电器。学生会给了我们一个套间,我们得以免受8人一间宿舍的拥挤之苦。5年大学念下来,修理的电器小到耳塞,大到冰箱、洗衣机,大概有七八万件。那时还帮广东的乡镇企业设计产品,赚设计费;向杂志投无线电修理的稿件。大学期间没向家里要一分钱,虽然我是个独生子。修理还培养了我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3岁拆一个玩具,知道先拆哪个螺丝才能卸下轮子,这不是逻辑思考能力吗?我一直不重视数学,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工具,在思考能力上,修理的功能大大超过了数学。
性格中的探索欲和征服欲,以及拆拆装装的爱好,让我心里装了匹马,总想跳出旧有的圈子去另一个天地飞驰。小时候我不知道长大后要做什么。当教师的母亲建议我念师大,理由是大家都知道的:做老师一年有两个假期,面对学生不必考虑太复杂的人际关系。1987年我在北师大无线电专业念得快毕业时,突然厌倦透了。虽然无线电技术几乎半年就要更新一遍,但原理我已经知道了,我希望能学新鲜的东西。毕业前,竟然莽撞地报考了医学院普外研究生。这真是胡闹,结果当然没考上,差6分。上学时一直给《无线电》杂志投稿,主编了解到我快毕业了,就把我要到编辑部。干了3年编辑,电台招直播主持人,朋友们怂恿我:赵九泷,你嘴皮子挺利索,主持人也挺风光的,去试试吧。就去试,考上了,后来又去了电视台。我曾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过修理摩托车的节目,现在主持《电脑演播室》,和我的专业还沾了点边儿。
修理东西只是我的一种纯粹的爱好,受发自内心的一种原始冲动的支配。当一个人自觉行动以满足他的心理需求的时候,他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但把这件事作为一项职业,就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
我对修理的执著并不体现在是否把它当作精神寄托,当作某种逃避的家园。我只是想从原理、技术上去体验我不知道的一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这种欲望驱使着我不惜代价。我用过的计算机,从286、386到奔腾II,全部是自己攒的。笔记本电脑也换了三代。
正在从事修理、使用工具的男人是性感的,这种说法有道理。这大概可以归结于原始的男女分工。男人是社会的征服者,女人是社会的维护者。男人作为社会的征服者,需要不断地探求这个社会,开发这个社会,提高社会生产力。男人的本能驱使他们去冒险,去创造奇迹。女人自然喜欢正在从事生产、劳动,并有所成就的男人。手巧一向是人类最赖以自豪、自负的东西。人类的发展得益于一双灵巧的手。用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论来说,那些有灵巧的手、有充分的智力和想象力的人得以有配偶,可以繁衍自己的子孙,种姓被保留下来。
现在许多男人已经不擅长手工了,这不能算什么悲哀。现代社会对男人的要求太多,同时又有许多诱惑在等待他。但是对孩子、学生,还是不应该放弃这种教育。我的儿子已有7个月大,他会拆笔—一枝笔最少有3个部件,多的有七八个。他有个动作很让我感动:柜门上贴了张画,他去揭下来看反面的内容。
我有一套修理电器用的设备,高档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高级万用表、频率计,等等。以前身上带把小折刀就敢给人修手表,现在没有专门的工具,谈不上修理。东西越现代化,对工具的要求越高。因为我现在把精力放在高频领域,所以钱就用在仪器设备的不断升级上。比如一台竖显读出的示波器,100兆,可以在看波形的同时在屏幕上看出电压、频率、时间差是多少,价格是普通的两三倍。花了多少钱,没算过。
我没有积蓄,不想存钱养老的事。我喜欢新东西。一种新产品刚上市时,我用高价买来,我知道它的价值,在许多人没有享受到它的时候,我享受了。这是心理的满足,钱是靠不住的。我有台机器,全中国只有180台。
我讨厌重复、平淡。最悲伤的是黄昏时看到楼群中亮着的厨房里的8瓦小灯泡。这个时候我总是逃到霓虹闪烁的地方去。
采访结束,赵九泷立刻扔下我去做自己的事,并且不客气地说:“你可耽误我不少事。”
但他又让我“呼吁”,希望大家能认真阅读各类产品的说明书。一个现代人可以不去练习装灯泡,拉电线,但应有最起码的好习惯—阅读说明书。不看说明书是盲目自信的表现。虽然现在东西做得越来越傻瓜型,但人还是应该仔细看说明书,这样才不会被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