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业:垄断打破之后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高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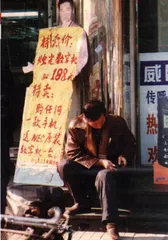
由一堆官司谈起
对于中国联合通信公司来说,今年11月可谓是其成立3年来最焦头烂额的时候,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3次坐到了被告席上。11月5日、14日、21日,3位从联通北京分公司营业厅和代理商购得联通130网“水货”手机的消费者吕英、卢涛、杨义华,分别走进北京海淀、西城和东城区法院,状告“联通”欺诈顾客,违反《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要求双倍赔偿。
面对接二连三的官司上门,联通公司显得满腹委屈。“‘联通’也是水货手机的受害者。”中国联通副总经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吕建国向记者诉苦道:“水货手机大多是进货渠道不正规的‘真品’,实际受损害的是像‘联通’这样的网络经营商。”据介绍,近年来我国移动电话以年均170%的速度猛增,年销量达600—700万部,而从海关进口数不足10万部,除去部分合资产品外,大多均为没有入网证的走私水货。因此,“联通”认为,既然进货渠道紊乱的现象“不可避免”,只要不是质量低劣的假货,不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就构不成欺诈。
然而任职北京拓世嘉华公司的卢涛在法庭上反驳道,“联通”伪造入网证号,任凭顾客反复投诉而搪塞了事,是“讳疾忌医,推卸责任”,倘若“联通”依旧“穿新鞋走老路”,其结果只能是“自毁长城”。
“老路”指的当然不是年轻的中国联通。自1994年7月成立以来,联通公司在痼疾难除、如一潭死水的电信行业屡掀波澜。对消费者来说,最明显的实惠莫过于昔日身价不菲的“大哥大”走入寻常百姓家中,10年间售价降了80%,而过去营业员冷若冰霜的脸上也渐渐堆出几丝笑意。今年夏天,“联通”在重庆、成都放装市话的计划被阻后,国内舆论曾一致声援,中国联通一时成了敢于向中国电信公开叫板、为民谋利的反垄断英雄。然而孰料想,仅3个月后,“联通”便官司缠身。
作为坐收渔利的竞争对手,中国电信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11月14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披露,一位内蒙古电话用户4年前因为查询一张41.65元的长途电话缴费单而屡遭当地电信部门的侮辱,然后是“一投诉就送你上法庭,一上法庭就判你输”,4年来始终没有得到说法,更让亿万观众气愤的是,记者前往采访,却被傲慢的邮电局工作人员带进了保卫科。
事实上,这只是反映中国电信“老大”作风的一个老式故事。几乎所有的电话用户帮领教过电信部门的类似待遇。仅北京一地,在10个月中因盗打和怀疑盗打长话而引起的话费争议就达3694起,其结果大多是用户无可奈何地忍气吞声了事。
而几乎与此同时,南京电信局却因为一次“寻呼机真情大赠机”活动,于11月11日被9家社会寻呼台联名状告“不正当竞争”,索赔2100万元。“表面上看电信寻呼此举对消费者是好事一桩,但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把我们这些竞争对手一一挤垮,恢复到寡头垄断的大一统状况。”当地一家社会寻呼台负责人说,“这种实惠十分危险。”
穿新鞋,走老路?
让人上火的不仅是电信部门,交通、水、电、气、医疗卫生……几乎所有的公共行业一直都是公众投诉的热点。“抱怨由来已久,”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余晖副研究员说,“但在行业垄断坚冰融化的今天,其内容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长期以来,这些具有公用和公益性质的公共部门一直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划拨经费,政府行政部门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垄断经营者。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拨款逐步回缩,公共部门先后被推向市场。更重要的是,其一家垄断地位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科技水平的日新月异使自然垄断的基础丧失殆尽。”余晖向记者指出,以电信业为例,光纤通讯技术的普及应用,使电讯可以绕过人为铺设的物理网(同轴电缆)迅速完成,一秒种内足以传送50套大英百科全书。“在信息稀缺时代建立起的社会结构需要再造,”余晖说,“新技术意味着垄断和限制的终结。”据他估计,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络经营商将成为中国电信业的新一轮竞争对手。
恶劣的服务态度和毫无道理的价格管制是人们过去对公共行业不正之风的普遍抱怨,尽管有关部门一再推出包括“承诺制”在内的多种纠风措施,但真正有所改观却发生在其垄断地位被打破之后。
事实上,公共部门出现的竞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自不待言,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联通北京分公司和南京电信局所惹出的麻烦只是其中的两例。
邮政特快专递业务于1984年在我国开办,这块大蛋糕由中国邮政一家独享的局面只维持6年就被打破,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敦豪速递、美国联邦快捷、澳大利亚天地、日本宅急送等“洋速递”纷纷前来抢滩,民航、铁路部门也先后建立了快件公司,目前仅在北京注册登记的速递公司就不下百家,年业务量增长70%以上,《邮政法》明令由邮电部门专营的信函寄递业务也有部分被他们揽走。一些速递公司还推出了颇为丰厚的奖励政策,或是高达30%的回扣,或是免费“新马泰7日游”。
然而在这貌似繁荣的背后,却另有一番景象。几乎所有的速递公司都称自己“有专机、专车”,但实际上除EMS外,只有联邦速递在今年获得民航总局签发的许可证,开辟了中美货运航线每周一次航班。有的一家人集资几万元买辆“面的”,竟也跑起了“速递”。更有公司连“面的”都没有,在国贸中心,一家速递公司的小老板坦率地告诉记者:“我们做的是代理,二级、三级,甚至四级代理,把快件收一下交给大公司,不买车也能日进斗金。”就是这样甚至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的皮包公司,居然也抢走了北京10%的国内速递业务。国家邮政总局提供的材料表明,1996年我国国内速递快件的丢失率比1990年增加了5倍。
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问题或许更多。随着医院补偿体制和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大批医院被迫走向市场,私人诊所纷纷出现。在给人们提供更为丰富医疗服务的同时,患者的意见却越来越大。据中国消协介绍,今年以来,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医德、医术和服务质量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倍。
最让人头痛的是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卫生部计财司张成玉向记者介绍指出,这些已无人去管的小医院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引入或干脆整个承包给私人游医,以“祖传秘方”、“神医妙药”为招牌开设所谓“性病专科”、“不孕症专科”、“骨质增长专科”等。由于普遍管理松散,这些基层医院甚至能随便开出“杜冷丁”、安眠药之类的控制药品,而30%的假药也是由他们的药房售出。
更大些的医院则另有一套诓钱的高招。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722所一位主管医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单位20多名职工到一家合同医院看内科门诊,全部先背上一种“24小时长程心电监护仪”作了一次检查,尽管谁都没有这种仪器检查的适应症,但每个人不得不交出200多元的检查费。事后得知,这一仪器是该医院内科医生们集资购买的。据国家医药管理局医疗器械司卜绮成司长介绍,这种“类股份制经济”在全国都很普遍,仪器使用率往往能达到空前的满负荷。
更为奇特的是最近武汉商业职工医院推出的“手术议价制”,患者可就手术费于有关院领导讨价还价,其他医院收费4000元的手术费,据说在这里可“砍”至3000元,一时就医者异常踊跃。
“医疗事业具有极强的信息不对称性,医患双方中,医生占据绝对的主动性。”卜绮成司长说:“是什么病,开什么药,花多少钱,患者必须听任医生处置。而一旦医院成了跳蚤市场,医生成了二道贩子,受损害的只能是病人。”
礼崩乐坏的糟糕日子
在旧有垄断被打破后的纷纷扰扰之中,昔日的“大哥大”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几十年来,他们作为政府行政部门,肩负着具有福利性质的普遍性服务和收益性服务这双重责任。前者属于纯亏损部分,后者则意味着超额垄断利润。所有的后起者都冲着暴利而来,而公共行业却还要继续承担和完善普遍性的服务,这多少让他们心有不平。
“如果向公用行业片面强调商业竞争,人们将很快产生怀疑:‘市场化给公众带来了什么?’”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经济学家伊丽莎白·皮科克去年底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指出:“政府管制的失灵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英国80年代开放供水业后,曾因自来水公司不愿更新管道而导致水源的大量流失,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地的自来水流失量约占总供水量的30%,水价不得不因此一提再提。令英国公众难以接受的是,各自来水公司每年的利润却高达20亿英镑,公司董事长的年薪和红利达到数十万至百万英镑之巨。
公共行业与老百姓的生活最为密切相关,因此在一些人眼中,也是离我们钱包最近的地方。余晖副研究员说:“在国家垄断时期,行政命令就是游戏规则,而一旦垄断打破后,行政规章失去意义,行业法律却未能建立健全起来,各集团的利益没有分摊清楚。对消费者而言,这种混乱比过去的不便更为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