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杂食动物的时代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何西风)
十多年前有人戏言:如今读诗的还没有写诗的多!那并非抱怨诗出得太滥,而是感叹诗歌读者群正有变为“濒危种群”的危险。我想,如果这个评论者到现在的报摊书市逛一道,他一定会说:如今出书的比读书的多!
的确,现在的出版物太多了,多到只能用“信息爆炸”才能描述的地步。去年我从清华大学一家电子出版物公司得知,他们将出版的电子杂志有两千多种。又据新闻出版署统计,我国现有期刊8135种,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10万种。更不用说还有几十个频道、数百个专栏的电视或电台节目,还有那正以燎原之势普及开来的互联网。即使这样,有专家仍不无遗憾地说,与那些信息大国相比,我们仍是信息不发达国家。就这样,信息爆炸的冲击波把我们推进了信息时代。
信息爆炸产生于现代“信息技术革命”:100年来的电讯革命、50年来的计算机革命乃至近年来的网络革命,突破了人们传统生活的时空界限。在现代信息世界中,纽约和北京一样远;伦敦发来的消息可以与我们身边出现的事情同时出现在媒体上。换句话说,信息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远近、快慢的分别。当世界各地的动态、人物、趣闻和说法都无分远近地同时进入我们的视、听、说世界时,我们便真的变成了“有限而无界”的动物,也就是“信息动物”。
在竞争社会中,所有“信息”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它们都是新闻。所以新闻业成为现代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信息快餐业。人们从新闻中了解这个一日三变的世界,了解相关的市场动态,根据新闻筹划自己的衣食住行,一句话,根据新闻安排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这些“信息动物”无非是“新闻动物”!
新闻快餐业在向人们提供必要信息资源的同时,也造就了公众那种旨在休闲和猎奇的阅读口味。可惜在这个世界中,富于刺激性的新闻热点并不会随着信息传媒技术的发展而增多,于是摘编、转载甚至直接挪用成为新闻界的特权。在这个背景下,一家媒体上的新闻热点立刻会幻化出无数报刊杂志的热门新闻或封面故事,繁衍出由多种语言写成的无数文字。前不久英国王妃戴安娜在车祸中丧生,随后几天,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国大众传媒都充斥着这位王妃的生平、玉照和追踪报道——她正被塑造成新一代的丽丽·玛莲或玛丽莲·梦露。此外,像波黑内战、超级世界杯球赛或某一国家中的政坛丑闻这样的新闻素材,也正如一个个“信息母体”,它们在其传播过程中繁衍出数不清的铅字、印刷纸张和热门话题。
我们由此发现了一个秘密:所谓信息传播,无非是信息在各种传媒中不断复制或繁衍自身的过程。无论其复制规模多么庞大,其固有的信息含量却不会因此而有所增加——即使一万家报纸刊载了戴妃遇难的消息,那不仍是一条新闻吗?
作品新闻化
当然,一条新闻在传播过程中的繁衍和复制本是一件未可厚非的事,因为追逐热点本来就是新闻业的生存方式,所以新闻记者和编辑在摘编和转载其他信息方面一向享有某种无形的豁免权。近期《南方周末》一篇鼓吹网络的文章以赞美的口气说:“据我所知,‘××专栏’的编辑先生之所以能用最快速度发布最新信息,所仰仗的无非是Internet上大量的信息资源。”
相比之下,图书出版业就没有这么自由。根据传统的也是法律的观点,不加声明的摘编、转载或挪用其他作品的材料或观点就是“剽窃”,它不仅可耻,而且违法。中国新闻出版署每年都会处理一些“侵犯著作权”的剽窃案,当然它处罚的只是那些过于笨拙、显而易见的抄袭作品。
不过眼下情形似乎变得复杂了。翻开时下一些图书尤其是时尚畅销书,我们常发现其中的内容似曾相识,大同小异。它们实在很像“文摘”或“文摘的文摘”。两年前适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市面上很快出现了多种二战题材的系列丛书。不过,如果撰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那位美国作者有幸活着看到某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传》、《戈培尔传》以及《阿拉曼战役》等书,他一定会指着它们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
像这样为应景而匆忙“纂”出来的书不在少数。股市刚问世,便出现许多面孔相似的“入市手册”;随着企业管理成为热门话题,书市中便连篇累牍地摆出《哈佛商学丛书》、《哈佛商学院MBA教程》或《工商管理经典译丛》,让外行人觉得“哈佛”好像是一家著名公司似的;再看看那些五花八门的电脑教材、网络读物,它们或是直接来自编译,或是通过“块移动”或“粘贴”拼凑成文,令人难分鲁鱼亥豕,好像都出自一人的手笔。这正应了一句俗语,“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总的来说,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如今的图书出版业日益具有新闻化特点。一位编辑为了完成利润定额,必定要追踪时尚或热门话题来确定出版计划。他所选定的作者自然也需具备编写抄译、调侃煽情的“捷才”。难怪如今的作家已不叫“作家”,而被称为“写手”。这正是造成当前作品新闻化的基本原因。
新闻化作品大都标题新颖醒目,导语惊世骇俗,包装透着股奶油味儿,其文字也华丽堂皇,能抓住你的眼睛,但容不得你细想。这些用于消闲解困的书或可放在床头,或可读于厕所,但却没几本是为你的书桌预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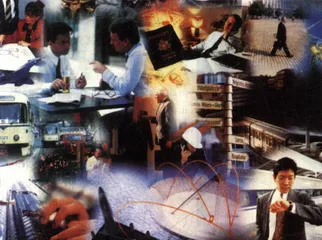
经典与摩登
数日前与朋友讨论英文“classical”和“modern”的译法。这两个词在指示时代时通常被译为“古典”和“现代”。然而它们还有另外两个对应的意思,即“经典”和“摩登”。换句话说,所谓“古典时代”其实也可以译为“经典时代”,而“现代”则可译为“摩登时代”。我由此猜想,“经典”与“古典时代”、“摩登”与“现代”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
“经典”的意思谁都明白,达芬奇的画、米开朗基罗或罗丹的雕塑、贝多芬或莫扎特的音乐,所有这些富于创造性的、不可重复的典范作品都是“经典的”。反之,“摩登”则意味着那些根据时尚批量生产或复制的作品,温莎公爵夫人的婚纱、戴安娜的孕服、张德培的球鞋乃至刘德华的洗发水,这些都是“摩登的”。
说到文字产品也一样。直到不久以前,“著书立说”还是一件惟此为大的事。中国古人一向说“文章千古事”,所以才有“锥心刺血始成书”的故事,才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自述。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那个信息相对贫乏时代形成的经典作品恰恰构成了人类取之不尽的信息资源。
反之,在信息爆炸的“摩登”时代,“文章”成为时效性很强的事情。一年前《中国人可以说“不”》这本书曾炒得沸反盈天,几个月后又听说有《中国人仍然可以说“不”》问世。我本来以为接下来还会看到《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说“不”?》这样的续篇,孰料一直没有下文。大约这个话题已经过景了吧。
当写作成为“信息制造业”后,作品的独创性标准便由时尚标准所取代,呕心沥血式的写作嬗变为以抄袭、拼凑和媚俗为特征的信息繁衍。因此,撇开由大量印刷品造成的“信息爆炸”的外观,我们时常会感到“信息贫乏”这一现实。
“信息繁衍”,套句时髦用语就是“信息克隆”。由于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视、听、说的世界中,所以大量信息克隆的新闻或新闻化作品必定会造就出一代“信息克隆人”。如今许多穿梭于报刊杂志和电子咖啡馆的人对美国大选、“保钓运动”、南沙争端、环境保护、戴妃之死和克隆技术等话题都能说出一二三来,然而不过是说说而已。信息克隆人的头脑中只有转瞬即逝的信息,而没有属于自己的问题。
不久前在《通讯产业报》上读到一篇采访文章:《在网络上探索网络文化》。其中一位被采访者说:“信息时代的来临几乎等于精神时代的来临。”这话听起来不错:“信息”让人联想到“精神”,信息无所不在,精神当然也就无所不在!
然而且慢,有时过于明显的论断反倒藏着许多误解。美国学者T·洛扎克先生在《信息崇拜》一书中写到:“信息,到处都是信息,惟独没有思考的头脑!”这话让人想起上世纪德国思想家尼采在一封信中说的话:“我的头脑,不是别人的跑马场!”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了不起的乐师名师旷,相传他能奏《清徵》、《清角》,一奏而“玄鹤云集,延颈展翼而舞”,再奏则“凤凰来翔,大合鬼神”。据说他最初学艺时总嫌进步太慢,说:“技之不专,由于多心;心之不一,由于多视。”于是用艾绒熏瞎双眼,终于练成鬼神不测的绝艺。后世因此称他为“乐圣”。
这个故事虽然夸张,而且充满“五色使人盲,五音使人聋”的道家情调,但它可以提醒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为自己的精神留下一个思想的和创造性的空间。如果没有这个空间,我们似乎就会沦为一个吃什么排泄什么的信息杂食动物。
一旦人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信息量才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