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天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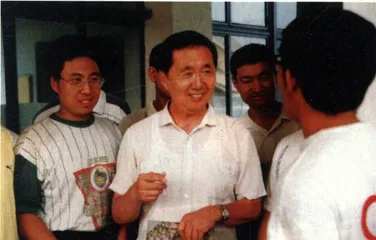
孙老师像一面墙,挡住了外面的世界
8月29日和9月5日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这两天班主任孙维刚总是先和他的学生们在北京22中校门口集合,作别校园,然后驮着脸盆挂着暖瓶,骑自行车穿城上路,直奔清华、北大。
22中是北京一所普通中学。据介绍,22中的高三(1)班也没什么“不普通的”,6年前,67%的同学成绩低于任何一所区重点分数线,34%的同学是大拨儿轰就近入学的。班主任孙维刚也不像有什么“特别”的样儿,浅灰的确良半截袖,微笑中有迟暮之态,他今年58岁。
但22中的高三(1)班总有些“不一样”,这“不一样”有分数条成绩单公众展示媒介“炫耀”的意思——今年高考平均总分558.67,比东城区一所市重点中学的平均分高43分;600分以上9人,全班40人中有22个进北大、清华;闫珺获第3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在1996—1997年全国数学联赛中,全班有5人一等级,3人二等级,6人三等级,连年校运动会总分第一,任晓军获北京市中学生体操全能第一名;……“不一样”还在于孙维刚和40个孩子所体认的做人准则和精神气质上。孙维刚老师在8月31日接受记者采访,对此有如下诠释:
记者:请您从教学方法或治班原则上,谈谈您是怎样使他们考上北大、清华的?
孙维刚:使这些天资一般的孩子变“聪明”,我的经验是:一要使知识系统化;二是提示规律启发联想;三是让孩子成为课堂的主人;四是在精不在多,不搞题海战术;五是鼓励他们写科研论文;六是让学生每天睡8个小时。
记者:您认为“读书——考试——升学”是长大成人的唯一途径吗?
孙维刚:不是唯一,但是最佳。面对今天的现实,读好书考好试多学知识是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一种方式。他们应考虑更大的命题,比如国家、人民。
记者:根据您多年做班主任的经验,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幸福快乐是什么?这一阶段富有成效的人生状态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
孙维刚:快乐幸福的标准因人群而异。对于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的理想是成为划时代的科学家,我认为,他们的幸福快乐就是刻苦学习,为将来打好基础。这一阶段的成功就在于获得一种高水平的思维能力和卓越的品格修养。这也是他们的想法。教育的目的是现在将来时。
记者:就我的采访经验,有很多孩子不但对学校、课堂没有热情,而且对传统的价值观漠视甚至反叛。我想知道您的评价。在您所带的班里,是否有这样有“个性”的孩子,您是怎样校正,使其走上您所设定的正轨的?
孙维刚:您所说是一种普遍现实,非常强大。作为个人,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是非常苍白无力的。我对此表示遗憾和同情。人们喜欢说,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做人、成长没有唯一标准。但我认为,还是有最高标准的,比如正派、诚实、庄重。美国乒乓球队70年代初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个留长头发的嬉皮士科恩问总理怎么看嬉皮文化,周恩来总理的回答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为打破现状做过各种努力,但我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所在。我希望美国青年人尽快找到正途。”我想总理的话也是对今天一些孩子的寄语。
我们班不存在这样的同学。我每一轮都从初一带班,那时候他们还像一张白纸。虽然我没有力量左右社会大气候,但是可以建构自己的小气候。我单枪匹马是无论如何敌不过流俗的洪水猛兽的,我借助集体的力量、荣誉和舆论。我们班初一时,也有考试作弊的,我个别找他们谈话,在集体中形成舆论,欺骗是遭鄙弃的。我们班同学不大和外面同学联系,我反对他们过生日搞聚会、过年给同学邮卡片。因为我们是最好的。大家都这么认为。
我们班孩子不追星,不唱流行歌曲,不喜欢刘德华,我们唱的歌是《跟着毛委员长上井冈》、《在太行山上》和《长征组歌》,我们的孩子知道什么是艺术。我们班男女生之间从不打打闹闹,他们很庄重。男生都剃很短的头发,女生不穿奇装异服。
记者:能否讲一下您的“好学生”的标准?
孙维刚:一是慎独,洁身自好;二是宽广的胸怀,能接受甚至不公正的批评;三是有责任心。
记者:您的建班方针是:诚实、正派、正直,树立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做有丰富感情的人。您认为这样单纯的价值观和生活理想所竖起的心灵屏障会在孩子未来的人生中坚持多久?
孙维刚:我不敢下定论。肯定会有否定,认为它幼稚可笑的时候。但是也不能排除否定之否定。因为毕竟,这些东西曾经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要素,成长中一个美好阶段。迷茫、忧郁谁都会有,但我相信叶落归根。一个有思维判断能力的人终会找到正途。我们班的孩子正是这样。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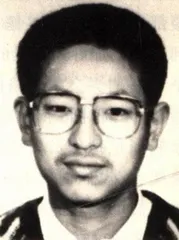
杨维华
他像一面墙,挡住了外面的世界
杨维华,孙维刚老师6年的学生,刚刚考取北京大学数学系。
随便把我们班哪个同学拎出来和外班同学放在一起,你会一眼认出哪个是高三(1)的。我们剃平头,不穿皮鞋,不唱流行歌曲。这没什么不好,形成了习惯,我们觉得这样最正派。按照孙考师的意思,我们把所有的脑细胞都留着学习。
甚至不和女生说话。我6年来就没和女生说什么话,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我们班男女生说话仅限于“某某某,孙老师找你”一类的。这也是我上大学有点儿担心的。
孙老师经常开家长会,学生家长一起开。我妈特别乐意听,6年来记了好几个笔记本。
孙老师讲课很有心计。他讲数学,讲α,β,ε,从希腊字母讲到希腊文化,再讲到欧洲,讲到二战,讲到二战他就画军事地图……看似信马由缰,可他最后总又能回到原话题。非常到位,像是精心设计的。
他对我们上大学提出了10点希望,要自省,要以班规要求自己,不要随波逐流……我都能背下来,我也要这么做,但他可能有点担心,毕竟他曾像一面墙一样挡住了外面的世界,现在我们得独自面对了…… 孙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