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论坛:白天不懂夜的黑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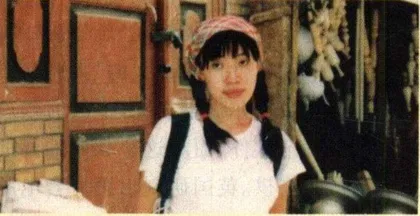
张红婴: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美编
今天晚上干什么
一个朋友去珠海呆了一阵儿,他说珠海的夜生活是分年龄段的:20岁以下的打街机和上迪厅,20岁到25岁的蒲吧(泡吧),25岁到30岁的泡茶馆和打台球,30岁以上的去卡拉OK。这是珠海,外地人居多,没有夜生活是不行的,非得出来玩。广州是非常自足的,它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一部大片在北京引得不少人去电影院,但在广州,最新的大片刚刚预告,VCD已经满大街了,谁还会去看电影。比如酒吧,在别处似乎是有文化品位的地方,在广州却不同,要么演变成大排档,要么最后成为青少年聚集的地方。
但广州毕竟是所有城市中最有夜激情的城市,不管你心情怎么样,有钱没钱,所有的商店和排档都会开到10点以后,不要说夜总会、歌厅、保龄球馆、迪厅、茶馆、啤酒岛、溜冰馆等等等等了。广州的晚上就是吃和玩,就是挥霍和赚钱,就是灯光和灯光。
对个人来说怎么样呢?看你现在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一个人就是一大帮人,一大帮人就只能吃饭、蒲吧、聊天:现在兴泡茶馆,一壶茶又一壶茶,一通宵玩牌——“拖拉机”。又有新兴的在酒吧做陶器,太矫情了。两个人就只能逛街、看电影、最多听听音乐会,最好的是上白云山兜风,上面空气非常好,一排排乌黑锃亮的摩托车,一对对男女:再有呢,就是两个人相对发傻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喜欢打台球,还有有意思的是晚上钓鱼,钓鱼然后喂猫,这就是夜生活中的两件事了。还能干什么呢?听起来多其实每个晚上都得想:今天干什么呢?泡吧没劲,大家都没得话说了。抓本书刚翻了一会儿,有人Call:我们在非洲吧,谁谁来广州了,你过来吧。觉得闷,没得玩。
父母根本没有夜生活。广州也有老年人跳舞,在广场或者公园,跳交谊舞、迪斯科,还有什么扇舞。但那是工人阶级,喜欢群体方式,知识分子走不进去,我妈说她觉得太尴尬。他们就看看电视,看看书报,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夜生活就是等孩子回来,一起吃饭。再好的就是能一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吃完饭散散步,到商店买点日用品,招手打的一起回来。
我所知道的还有一种——上夜课也算夜生活吧。我有个女友就每晚去上夜课。但这种夜课不是充电,她不是去学什么电脑,什么财会对工作会有帮助的课,而是完全的一种闲课。她去上化妆课。班上很多女孩,但没人想成化妆师,就为化着玩,给自己化,给朋友化。化妆课上完了,她去上美术课——“看你们画画我很喜欢。”然后去学电脑设计——我猜想她想找个美术圈的男朋友了。然后去上家政课,如何做个贤妻良母。其实就是另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她也许是去充血。
就这么多吧,你要觉得好玩,那是因为人和人不一样。

CaraScherer史美星: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
他们没有钱,但有夜生活
在北京有酒吧、有舞厅、Party和音乐会,夜生活非常丰富。像三里屯的酒吧,和美国一样,可以在外面喝酒,看人们走来走去,很好玩。只是很贵。在“HardRock”(酒吧),我们是免费的,所以简直成了……美国村,每个人都是认识的,你、你、你都是朋友,我们谈美国、中国、各种各样的事。
但是这不是我的全部。这是expatriots(移居外国的人)的夜生活,他们只去“Lightman”(迪厅)、“Solution”(酒吧)和三里屯;我不是expatriot,我去更多的地方,因为我喜欢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我觉得中国的跳舞很有意思,他们跳交谊舞,在学校的舞厅,在马路边,而且他们都会跳。在美国这是很高级的东西,是总统的舞会。还有,夏天的晚上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有人聚在一起,在路边Playcard,聊天,我很喜欢。(但是他们不穿衣服,肚子很大,我不喜欢;如果我加入,可能也需要大肚子。)很多人一块玩儿,有孩子、老头、老太太、年轻人,非常有意思,这说明他们有很好的社会联系。在美国朋友们也聚,但是去酒吧,去某个人的房间,不在路上,除非wandering(游荡)。我的父母每天工作,晚上很累,做饭、看电视,看到12点睡觉,他们没有夜生活。在美国如果你没有钱,就没有夜生活;但是中国不是,他们有夜生活,他们在马路边玩儿。
我在哈佛时有各种各样的夜生活,非常有意思,美国各地的夜生活不一样,也有意思,但是我都去过了,没有意思。在中国我到处去explore(探险),去别人不去的地方,非常有意思。昨天晚上我在修路的大沟里面走,这就是我的夜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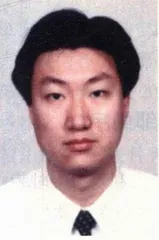
王欣:阿科化学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业务代表
夜生活就是背单词
以前有女朋友,每天下午就会通电话,今天晚上上哪儿吃饭?下了班赶过去,吃完饭逛逛商场或者看场电影,回家看书睡觉。两个人关系好既不会放纵地玩,也不会把时间抓得多紧地学,两个人的夜生活是有序的、恬淡的。
一个人恰恰相反,你发现整个晚上都是你自己的,夜生活是用刀子大块大块来切的。我和一大帮人到迪厅,热闹热闹,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朋友们各各找人走散了,自己一个人拿着杯饮料。去夜总会,发现别的生意人都是特别得其所哉,吃喝玩乐——一切就是为他们准备的。能力也强,欲望也强,相辅相成;我就不一样了,提不起兴趣来。而且小费高得实在惊人,在上海一家夜总会端盘子小姐要200块小费,我跟她开玩笑:是你给我小费呢,还是我给你小费。读美国的MBA要4万美金,我说你干一年就去美国读书吧。
夜生活和夜生活太不一样,在夜总会1000元钱就是几张纸,眨眼就没;花30块钱买本书可以看半个月。半年下来我发现最能安慰自己的是坚持了每天晚上3个小时的背单词——那是雷打不动的,所以现在的夜生活就是背单词。一个朋友说他女朋友的爸爸跟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夜生活,多少年来他每天都在反省自己:我今天都干什么了?时间是怎么过的?!他看电视时肯定要同时干着另外一件事,否则就不看电视。我们用不着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在28岁之前不应该有什么夜生活,不说它浪费时间,但是会觉着没劲的。
可能最需要夜生活的就是父母那一辈人,但偏偏是他们没有夜生活。回家一趟每顿晚饭都能吃到10点钟,就是聊啊聊——但从根本上我们又帮不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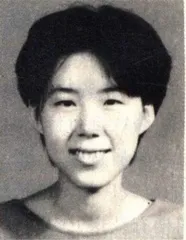
严蓓雯:上海《电影故事》记者
你觉得上海的夜生活丰富吗?
上海作为一个极其欧化的城市,它的夜生活也在追求一种被称之为“时髦、情调”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忘了就在不远的十年前,他们最幸福的晚上,是到家里附近的工厂里去打一壶现在看来根本不屑于喝的冷饮水;是街坊邻居聚在一起,到马路对面刚造起来的高房子下享受穿堂风,谈论东家长,西家短;是跟着父母去外滩看灯,因为交通管制又走很远的路坐车回家;是相约到同学的家里一起做功课,一起欣赏收集的邮票、糖纸。而现在,他们感到最丰富的晚上又是他们隐隐感到最无聊的晚上,他们感到最时髦的夜生活又是他们暗暗觉得最无趣的夜生活。首先,他们聚在包房里卡拉OK,把每一首凄美哀怨的爱情故事唱一遍,到了午夜,他们又去饭店吃夜宵,夜宵里有顶时髦的咸菜泡饭,好几块钱一碗;接着去打保龄,凌晨二三点正是保龄房里最热闹的时间,大概都是沿着这样一个顺序玩下来后到这里的。到了五六点,便去喝早茶,相约下一次的聚会时间。夜晚的消磨变成了一个固定的程式,越来越多的娱乐项目出现,而新鲜感越来越少,有所变化无非是先保龄再夜宵,或先吃饭,再OK。如果是所谓的白领女性,她们的消磨也无非是先去逛“伊势丹”、太平洋百货之类的商场,再在商场的酒吧里或顶楼的快餐厅来一杯加冰块的饮料,聊聊或有或无的感情生活,然后各自打的回家。酒吧一个个如雨后春笋出现,好像都极有风格,其实不过也只是一种时髦,木头的镜框里配发黄的照片,格子的大台布罩住一张很小的桌,更时髦的人或者只去波特曼的“HardRock”,只去钱柜订座唱歌。你觉得上海的夜生活很丰富吗?在外滩上闲来逛去的都是外地对上海的丰富充满了憧憬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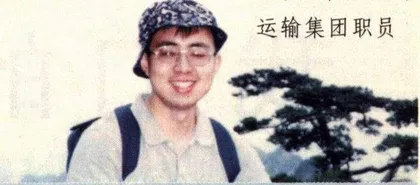
王敦: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职员
摘下白天的面具换上夜晚的面具
从前最快乐的晚上,是和父母一起到北海划船,那种氛围,那种情调,似乎永远不可能再追回了。现在,可以穿过雅致的静心斋去划船,夜色仍是从前的夜色,但没有小木船了,都是唐老鸭船和米老鼠船之类,而且最要命的是都成了脚踏船和电瓶船——难道人们真的懒得用手划船吗?“让我们荡起双桨”变成了“让我们踩起踏板”,不知道怎么说好。
现在的夜生活变成了两种人的夜生活,一种是花钱买情调,去夜总会,去酒吧,大把花钱来感受——其实情调是内在的东西,花钱是买不来的。另外一种以在立交桥底下扭秧歌为代表,这倒是不花钱,又畅快,但别人就畅快不了,我每次听着Walkman过桥就是一阵耳鸣。夹在这两种人之间似乎就无事可做,没有夜生活了。
当太阳落下去,夜色升起来,人的心灵是最敏感的时候。如果说白天是一种刻板的、秩序化的社会时间,晚上就属于极端个人化、自由化的时间,每个人都应该上心地、珍惜地去过。我看了许多海员写的世界各地见闻,夜生活都很丰富,尤其是南美国家,比如在一个大广场上有杂耍的、有卖东西的、有滚轴的、拉小提琴的、有看热闹的、有找素材的;男女老少、不同层次、不同收入的人,每个人都能尽情地欣赏和拥有美好的夜晚。
我觉得要达到那种有情调的、自由的和兼收并蓄的夜生活氛围,大家得发挥想象力,不要被束缚。夜晚来了,就该摘下白天的面具,如果不愿露出真面孔,不妨戴上另一副面具——夜晚的面具,哪怕是一副抒情的或者荒诞的面具,就像现在正在放映的电影《双面怪杰》(《Mask》)一样。 白天不懂夜的黑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