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46)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布丁 刘小东 于勒 施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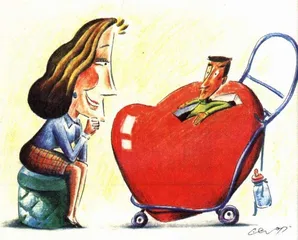
我是你大姐
文 布丁 图 王焱
我念大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女同学,擅长用扑克牌给人算命。更擅长跟人探讨人生。她的声音有股“摄魂大法”的功力,如今可能正在某个广播电台主持人生热线或情感热线之类的节目。
那时候,我是个自作多情的家伙,跟那个女同学探讨过几回人生问题,并且自以为是地认为她很喜欢我。
不过,这错觉很快就纠正过来了。原因是她愿意和所有男同学探讨人生,确切地说,是她愿意倾听所有男同学诉说心中的苦闷,并适时地予以点拨和鼓励。她做出能够了解每个人内心活动的姿态,并想以这种姿态引导着我们度过青春岁月。
我不无恶毒地将这种姿态命名为“大姐欲”。有一种女人,似乎在给别人做人生指导,在充当大姐这样的角色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需要。
我找到第一份工作时,我的领导恰巧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比我大几岁,按理说完全有资格在某些方面指导我,但因为我大学时受过那位女同学的刺激,所以对女领导敬而远之。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停止对我的骚扰。
作为一大嗜好,她总用电话指导她的朋友,告诉他们该怎样消除非份之想,怎样维护家庭和谐,怎样与领导相处与同事相处,怎样寻求人生的快乐等等等等。我跟她同处一个办公室,听她软言细语地给别人打电话当大姐,耳朵真受不了。
科学知识告诉我们,听觉对声音的反应很特别,如果是铁匠铺的噪声,因其单调,听觉系统会自觉缩小这噪声的影响力,但如果是有内容的声音,比如两人私语,听觉系统就会自觉地上捕捉并放大这声音,结果是听两人私语要比听打铁的声音更令人疲惫。
我就是这样被折磨了大半年,然后忍无可忍地换了一份工作。与女领导分别之时,我让她彻底地当了回我的大姐,絮絮叨叨,历时一钟头。听完她那一席话,我竟不无惋惜地想:如果我能把与她相处的这段时间内她所打过的大姐电话全部记录下来,兴许能出一本书。那阵儿,街上正流行一套叫忠告什么什么的书。
都是年轻人
刘小东
我们的报纸没有社交栏,我们也没有机会穿戴整齐地去出席什么晚宴,也没有沙龙,也没有高尔夫球场聚会,但我们可以吃饭和泡酒吧。
城市里有股聚会的味道,有些人热衷于参加各式聚会,有些人热衷于组织各式聚会,这里所说的聚会并非老同学或老朋友的那种叙旧,而是一帮年轻人或不那么年轻但心态还年轻的人聚在一起,他们彼此并不都相识,需要旁人引见,确切地说,这类聚会属于社会范畴。我们的城市里正充满了社交的味道。
大致的情形是这样:一帮人在某家饭馆或酒吧的桌边坐下,互相介绍寒喧,开吃或开喝,气氛快乐。就像当年费翔的一首老歌所唱:“年轻的朋友一见面,比什么都快乐。”
“都是年轻人”,这是社交活动组织者邀请参加者时要透露出的信息,这句话意味复杂,可意会不可言传。下面我要讲述一次我的经历让各位体会。
某位朋友,从事艺术工作,热衷于参加各类社交活动,天天想聚会,实在没得可聚,便在自己家里搞聚会。某晚,他打来电话说,我这儿聚了一帮朋友,你来一趟吧,我这女孩儿太多,得来几个男的。
我知道如今“女孩儿”这称谓用得太过混乱,就跟北京人逮谁管谁叫“师傅”似的,三十大几的女士也敢说自己是女孩儿。我问他是什么女孩儿。
他说,是外国女孩儿,有一韩国的,有一日本的,有一美国的,绝没有三十大几,我一听心花怒放,但还是问了句:“没有欧洲人呀?”
没有欧洲人,我也跑去了。到那儿一看,果然有一韩国人一日本人一美国人,年纪绝对都在40以上。我的朋友并没有骗我,她们是没有30多了。
朋友没骗我,而是利用了我的弱点,利用了我对社交活动某种不健康的期待,所以,我在那次聚会上反而不敢表现出任何不满的情绪,坚持用英语和“外国女孩儿”交谈,我想的是,一次聚会总有一些收获才好,我要练一练我的口语。
如今,这位朋友仍频繁组织聚会,且屡屡打出“都是年轻人”的招牌,但我已不敢去赴约了。这倒不是怕他再利用我的弱点,而是我正努力消除这弱点。
“都是年轻人”,这不是社交活动的理由,我希望有一天,我去参加某个聚会时能纠正我的态度:不是去打发一段无聊的时光,而是印证一下我体面的生活。
于勒叔叔
于勒
我的侄女今年读一年级,喜欢画画。为了表示我对她的喜欢,我给她买了一盒蜡笔,二十多支五颜六色的笔让我觉得挺像她的可爱的样子,而好看的文具也是我喜欢的。那次在西单赛特看到另外一盒蜡笔,售货员说是水溶性的,被装在一个漂亮的木匣子里面,打开看那笔漂亮得令我很嫉妒。标牌上说它的产地是瑞士,价钱是630元。我觉得我真应该给我的侄女买这一盒,但我没有那么多的钱。
前两天电视新闻里说现在中、小学生用的文具在玩具化——比他们的父母小时候用的文具花哨得太多。一个卷笔刀被做成汽车模样,价钱达到了两位数。有一位小学教师在荧屏上说玩具化的文具有两个坏处,一是孩子上课要玩文具,影响学习;二是小孩会互相攀比,养成花钱的坏习惯,对家庭经济不富裕的孩子来说则会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最后播音员说现在商场内已经找不到一块纯粹的三角板了,文具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消费者被赚了过多的钱,这种局面应该改变。
卖文具的赚了多少钱与我无关,如果真的在急用时找不到一块合用的三角板,我是要骂人的,同时我也会努力到别的商场上找找。但是玩具化的文具让孩子学习退步,甚至让他们道德变坏的逻辑我不同意。
被美丽诱惑是否有害?我认为这分对象是准。我就喜欢到高档商店看一些好东西,比如一个文具盒——上下两截插筒式而不是传统的翻盖式,没有图案的外壳散发出钢的光芒——让我欢欣鼓舞。小孩买不起100多元的文具盒,那还有很多便宜得多而且同样漂亮的卷笔刀可买。喜欢漂亮文具是我和他们同样的立场,我维护这一点。
如果我的侄女要我买那盒蜡笔,我不敢对她说“咱们还不富裕,不能买这么贵的文具。”那我就彻底失败了,因为我教会了她卑微。我们的家长是否已脆弱到不敢告诉孩子:我们是穷人。
一次一个朋友说用了几支德国产的圆珠笔后发现它们不如国产的好使,因为那种洋货总是漏油把手弄脏。我听了又欢欣鼓舞,因为好用的笔也是我要的。这证明我在对文具的人格立场上没有问题,我没有盲目崇拜。
笔有好有坏,价钱有贵有便宜,孩子和我们都很清楚。根据喜好和经济水平选择合适的文具是我们应该教会孩子的。但是有人告诉孩子说好看的玩具是有害的,那些使用昂贵的文具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我就要怀疑他教育的动机了:掩盖事实,要孩子相信那样的胡说八道?我很爱我的侄女,我想让她知道这一点:我不富裕,这我也要让她清楚。我也不想让她看见我被贫穷打倒的样子,我情愿告诉她:你的于勒叔叔正在努力挣钱呢。所以当新闻重播的时候,我把频道调开了,我怕我的侄女看见,怕她以为电视里说的那些是真的。
过度诠释
施武
“吐故纳新”,这在我小时候是一句很有气概的革命口号,它所指称的是一些社会性的、历史性的选择或举措,与生活情调无关,与生物本能无关。
在一个讲究情调的时刻,我和几个讲究情调的朋友走进一个小饭馆,这个小饭馆一切正常,只是小,人不多;菜的种类很正常,只是量大得让人觉得占了便宜。突然,桌边上的4个精致小字像儿时玩具一样不待自来地现身于我的眼前——吐故纳新。环顾四周,此饭馆里每张桌子的四边都影子一般印刻着同样的字样。看着拿起筷子准备进餐的朋友,这4个小字在一片暧昧的气味中,变形得越来越有生物性,越来越有广告的姿态,它似乎用一种很平静很客观的道理在告诉你,把旧钱都吐出来,你才能有机会进新的财。它也有另一种理解,在这另一种理解的暗示下,那几个朋友正在把菜一口一口运进嘴里的行为更为贴切的理解就是“纳新”,那么,我就疑心,我们正在坐着的椅子是不是马桶,以备“纳新”的同时“吐故”之用。
这饭我是没法好好吃了。
我努力地摆脱在这一片菜香中“吐故纳新”给我的不良暗示,我努力地向时间的反方向退,其费力程度与逆流而上等同。当我的记忆将要接近“吐故纳新”的岁月时,恍惚之中,“吐故纳新”一下跨越时空、远涉重洋走入了中世纪的欧洲——我的同伴突然都变成了中世纪的贵族,这小饭馆里正在演绎着我在历史书中读到的故事:中世纪黑暗无聊的生活中,有钱有文化有情调的贵族们也只能过最无聊的日子。那时的禁忌之多,最快乐的消遣只剩下吃。可是,一个人使足了劲吃能吃多少呢?吃饱了,不是又无聊了?要把胃里的东西消化完到能再吃的时候,这段时间如何打发?于是,他们一定是想到了“吐故纳新”,在丰盛的餐桌上预备了一根根鹅毛,旁边预备了一个个大痰盂。贵族们吃撑以后,不要脸地张开大嘴用鹅毛扫扫嗓子眼儿,然后,对着大痰盂反胃,吐空了胃,再端坐桌前,又一轮“纳新”开始。
“吐故纳新”到此时,完全没有了社会历史感,没有了革命性,连时间概念也被缩短到了连消化都来不及的程度。新与故只在吐和纳之中显示区别,而光怪多元的现世与黑暗古板的中世纪在吐和纳之中竟有了相似。
至于这顿饭我是怎么吃下去的,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这家饭馆的设计者不太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