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45)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李佺 吕浩东 赵晓阳 郭莲芝 龙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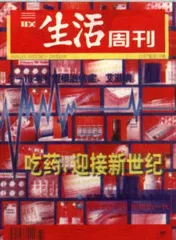
药物从某种意义上正在起到与毒品同样的作用。谢谢贵刊的提醒:一个依赖药物的社会可能和疾病肆虐的社会同样可怕。
广州李佺
污染经济
上海泛雅公司吕浩东
编辑先生:
我大学里是学经济专业的,看到贵刊今年陆续发表的几篇关于环保的文章,不禁联想到一个概念——“污染经济”。由于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故需作一个解释。
比如小时候可以游泳、垂钓的苏州河,如今却逼得路人掩鼻而过。据报道,上海市政府下决心在下世纪初将苏州河变清,也已采取了不少措施,并计划投资几百个亿。而另一方面,上海电视台最近的一篇报道表明,这条母亲河仍是某些地方和单位无法无天的“摇钱树”。苏州河支流流经的上海嘉定区某村与环卫部门签订了一份在河边建立一个大型露天垃圾场的协议,这份给苏州河带来严重污染的协议竟堂而皇之地得到了该村所在镇政府的盖章批准,批文称该村“无环保”,而该村领导的解释是“给村里一年创造两万元的经济收入”。
又听说有些企业在沿海地区不能再污染下去了,转而打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主意,大有不把内地青山绿水变成“烂酱缸”决不罢休的“气概”。如果广袤的内地真正成了“大染缸”,再像治理苏州河一般回头治理,我不敢想象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将要付出何等代价。
以上只是“污染经济”的一方面,而间接依靠污染产生的经济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茁壮成长”。记得以前我甚至敢喝生的自来水,而现在人们喝的越来越多的是所谓的纯净水、矿泉水,还有不惜千里迢迢去深山老林里搬来的“源头活水”。记得大学里教《政治经济学》的老教授给我们举例说,空气是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的东西,故不用交换,也就谈不上价格。而城市里如今一间间氧吧,我还未见过哪一间是供免费消遣的。如果马克思他老人家突然活过来,怕要大跌眼镜吧。
如果有一天,我们每喝一杯水都要付相当于一升硫酸的价钱,每吸一口空气也要付出相当于一包名烟的价钱,污染经济就太不经济了。当然,我指的是现在市场上硫酸和香烟的价钱,也许到那时每天天上都降硫酸,空气里尼古丁含量是50%以上,根据供给需求理论,供给泛滥,需求乏力,硫酸和香烟也就像此前的水和空气一样“一文不值”了。
地名命名与主权意识
中国地名研究所赵晓阳
编辑先生:
地名是历史文化的化石,不同的地名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近年来,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城市地名和建筑物名称中,以外国人名、地名、公司名命名的“英国区”、“西门子路”,在武汉港对面曾公然出现过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福尔摩沙娱乐城”(Formosa,音译为福尔摩沙,是16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对我国台湾省的称呼)。
建筑物名称,目前以“广场”、“花园”为通名命名的最多。从语言学角度上来说,“广场”、“花园”作为建筑物通名与规范的汉语表述实在格格不入。以广场为例,广场一词源于西班牙文plaza,最初指露天的、摆卖东西的市场。后来,市场搭起了顶,里面仍保留一个大的空地,国外一直沿用称为“plaza”。该词的含义有广场、市场、场所、大商场、十字路口等。如果一幢商业大楼,外文完全可用“plaza”,但汉语称作“广场”就十分不准确。名称的译写也存在问题。北京西客站名的译写专名用汉语拼音Beijing,通名用英文WestRailwayStation,违背了国家地名罗马字母拼写使用汉语拼音的规定,也违背了联合国标准地名单一罗马化的要求。联合国地名标准化“是一项旨在通过国家标准化和(或)确定不同书写系统间相互转写,使地球上的每个地名和太阳系其他星球上地名的书写形式获得最大限度的单一性”。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各国采用一种书写形式使国内地名标准化;2,采用非罗马字母语言的国家,提供一种罗马字母拼写的标准形式;3,制定一套国际公认的不同书写系统对应的转写法,以便将地名由一种语言转写成另一种语言的形式。
语言文字、名称规范固然是全民族性的社会交际工具,不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但文字、名称中所反映的仍然是主权意识。这是各个国家民族都十分重视的问题。法国政府为维护法语和法兰西文化的纯洁性,于70年代中期制定一条禁止在广告和政府文件中使用外来语的法令,法令规定:必须使用法语词语;若法语中暂无某一词,使用者必须提供法语解释。1994年2月又扩大了禁止使用外来语的范围,宣布一切经贸交际中均不可使用外来语。为了抵御英语对法语的侵袭,法国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全国规模的法语听力比赛。很多家庭已形成这样的一个传统,逢到听写这一天,就把家里人集中起来,由长辈念读,小辈默写,已形成一种保护法兰西文化纯洁性的自觉意识。
独联体国家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原来都使用俄语,所有的官员、译员都受过俄语的正式训练。但是中国学者赴两国会谈时,他们都提出在正式场合使用本国语言。因此出现了中国人讲汉语,翻译翻成俄语,对方翻译再译成立陶宛语或拉脱维亚语。但会后闲聊时,才发现他们所有的人俄语都非常流利。像立陶宛、拉脱维亚这样的小国,即使处在大国的威胁下,仍然不屈不挠地捍卫本民族语言的主权地位。日本也是非罗马字母国家,地名标志大都用汉字书写,汉字下面也有罗马字母拼写。拼写不是用英文字母拼写,而是按照日文的发音拼写。虽然日本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尚无国际标准,但仍然坚持用本国语言的发音拼写,坚持了他们自己的主权立场和民族尊严。近年来,各种名称西化成风,甚至比旧中国还厉害。在解放前,即是美国人开办的学校,也要按我国人民的习惯取名,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如今各种商品名称、商标名称、建筑物名称却直接使用外文或外文音译。
1962年11月周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地区的地名大都是用藏语命名的。例如,人们在这里把河叫‘曲’,娘江河叫‘娘江曲’;把山口叫‘拉’,色山口叫‘色拉’;把地方叫‘隅’,门地方叫‘门隅’。”这是用地名通名论证领土主权的一个典型例证。当子孙再次遇到地理主权问题时,我们留下的是殖民文化的“英国区”、“福尔摩沙路”,又有什么颜面面对子孙呢?
用墙能解决环境问题?
北京郭莲芝
编辑同志:
地处八大学院中心地带的北航北门正对着一堵墙。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建筑工地,其实不然,它是“卫生”的分界线。
20年前这里也围过墙,那时是为了把庄稼地改造成小区。现在,人们再度把墙建起来则是为了墙内的一片绿地。
昔日的庄稼地上数不清的居民楼、政府机关林立。路边上,饭馆、菜摊把本不宽的马路挤得只能通过一辆车。路边的绿地便成了这一切“便民设施”的腹地,各种不洁物在灌溉绿地的水沟里堆积起来,包装袋则挂满了树梢。前些天,听说北航饭馆里打死了人,路边的环境就更糟了。学校内的所有不易管理的设施全部外迁,学校里环境优雅了,可校外却更惨。
有人说,北航只知道收管理费,连卫生都不管。后来才知道错怪了北航,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北航、东升乡、学院路街道都有份。不知谁找来了电视台,曝了一次光,各部门来了好多人,突击来了次大清扫。接着是贾庆林市长上任,狠抓一下,面貌又有改观。现在每天有专人扫马路,清垃圾,人们心里舒坦很多。
言归正传。现在讲讲墙是怎么回事。马路有人整治了,满是花草树木的绿地管理机构却鞭长莫及。于是干脆垒起一堵墙,让谁也进不去。
进不去自然是治根治本的方式。可本来供人们休息娱乐的环境却从此失去意义了。不知何时,咱们的政府才会给大家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买佛龛和买冰棍
北京东四龙进
编辑先生:
上个礼拜天,陪一个朋友去双安商场买眼镜。我们俩舒舒服服地站在电动扶梯上上楼,看见上下扶梯中间的楼梯上黑鸦鸦坐了一大片,吓人一跳。原以为是买东西的顾客累了,商场却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座椅。然后发现不是:有两个小孩拿着扑克在敲三家儿,更多的人在闲聊或养神。他们心安理得的样子让我很吃惊,觉得商场让人挤兑得很委屈。
两天后报纸上报道:由于天气炎热,北京各大商场成了市民纳凉避暑的又一个好去处。这倒是合了商场的心愿了:他们总是唯恐自己的地方不人满为患。可是报纸接着报道:商场除了冰棍饮料销售略有上升之外,其他照旧。有商场的总经理不情不愿地说欢迎市民到商场来乘凉。
基辛格有句名言:如果政府不准备足够多的厕所,那么市民就有权随地大小便。可我觉得凉快应该是个人的问题,还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觉得目前的温度不至于产生这么严重的结果。商场有为顾客提供优越的购物环境的义务,但没义务招呼所有怕热的市民都到商场去休息,媒体不应进行误导。就像侯宝林先生说过一个相声《买佛龛》:老太太一方面觉得应该对佛更加尊敬,一方面又为那么个破玩意佛龛竟然要卖5毛钱而耿耿于怀。那个总经理就有一个两难的佛龛:他不敢冒得罪顾客的风险去得罪坐在楼梯上的市民。顾客是上帝,市民是更大的上帝。问题在于:这些上帝只吃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