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你笑,谁难受谁知道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君梅)
“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说的是台上的演员。而小剧场的实验话剧更在意观众的脸色。近日在北京人艺小剧场连演一周的《爱情蚂蚁》的主创者们在该剧的宣传品上印着“把看别人笑话的习惯留在剧场门口”,“不妨把进剧场当作看(自己的)CT报告”。
是不是这么回事?看了才知道(内容)。而很多热情极高的观众是冲着形式来的:青年导演孟京辉+青年音乐人张广天+喜剧+悲剧+言情剧+艳情剧+荒诞剧+市井滑稽剧+13首歌+音乐剧……当观众满满当当地坐进小剧场,当舞台脚灯暗了又亮时,形式和内容就难分彼此了。
这出由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推出的喜剧被标了一个“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喜剧”的标签。原作者是以色列当代剧作家兼导演汉诺勒温。业内人士称他对人生社会极为悲观,形之于舞台,便是“热热闹闹的冷嘲、认认真真的荒诞”。他的力量不是因为有开门见山、直指人心的嘻笑怒骂,而且因为对社会那种戳心窝子的批判。尽管译者黄纪苏的再创作以及探索喜剧语言的努力受到了业内业外人士的首肯,但以色列民族的“精气神儿”翻到“中国版”上会不会变得似是而非有气无力?如果有人就此质疑,恐怕不是译者的功力能圆满解答的。导演孟京辉力求在这部反映当代都市年轻人心态的戏中探索“中国式的喜剧”。他用直白的(简直可以说是直勾勾的方式表现3个年近30的男女对自身价值的“标价”、“追逐”。他们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状态,男人和女人、情人和朋友相互轻视甚至是敌视又不得不“粘”在一起。他们的无聊、痛苦“像某些候鸟因为风的缘故而生下的蛋形状不明”(台词);他们又曾快乐得“不知所措”(一位业内人士语)。他们相互拆台相互排斥又相依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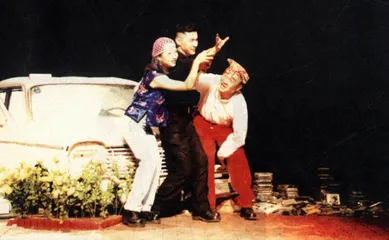
《爱情蚂蚁》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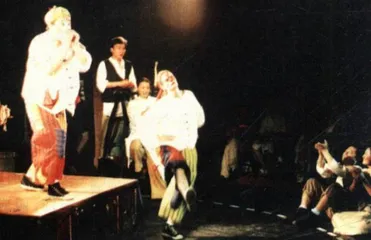
《放下你的鞭子》剧照(1994)
这部戏的音乐创作值得一提。
在这出一个小时的戏里,作曲张广天和他的助手用一把吉它、一把大提琴、一把小提琴为13首歌伴奏。音乐总在适当的时候响起——说得酣畅淋漓时自然该唱了,说得没词儿了也不得不唱。这种类似酒吧弹唱的方式轻易就煽起了观众的情绪。或许语言太像“固体”因而难于流动,而音乐则如液体般自由得多。
剧中人手拿一只黄灿灿的橙子唱:“桔子黄了,就要掉了/狐狸老了,眼光暗了/书上的自己变得越来越模糊/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衣服小了,穿不上了/开水凉了,冲不出茶了/生锈的钥匙,打不开家门/风沙吹过,看不见脚印……”
某刊物编辑,29岁的苗先生事后说:“我当时坐第一排,好多年没人这么面对面的对着我唱歌。”
当事情变得莫名其妙地令人不能忍受,当女主人公跪下抱住她丈夫的腿哀求他别离去,当男主人冷冷地说:“别这样,把我的鞋都舔湿了,软羊皮的!”当女主公大哭:“我没法重头再来了!”音乐再次响起。女人唱:“我知道这是结局/我已经永远失去。”合唱:“风一样凑近又云一样跑开/雪一样凝固又水一样流去。”这时大提琴的低沉听着像是一种隐痛。
在接近尾声时,女主人公唱:“有一天我要弹琴,为了你,我亲爱的人。”合唱:“这一天不会来临,我亲爱的人”几个反复:“我为了你我要穿上白纱裙”,“这一天不会来临,我亲爱的人”,“有一天,晚霞很温柔,我要握住你的手”,“这一天不会来临,我亲爱的人”,而此时小提琴的独奏却是深情而缠绵。
60年代生于上海的青年作曲家张广天曾为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作曲。我和他不熟但有种感觉:这个从学习京剧开始了解音乐的人总在戏里唱自己的心事。他的一位朋友说:“他的生活最近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然他不一定写出这么有感觉的歌。”
对小剧场实验剧惯用的“大写意式表现方式”,以及这出新戏里“杂烩式”的形状感,不同观众的反响差异很大。
28岁的刘莹小姐是某国驻华使馆的中国翻译。“我个人认为这出戏唱的比说的好。其中的歌每一首都可以‘单拿出来’让人品味,而台词之间要有更强的逻辑关系。直到后半部分演员陈建斌独白‘痛苦’那会儿我才开始有感觉。而前面他们试图用前卫的语言表现的城市人的空虚——为‘痛苦’作的铺垫我总觉得力度不够,没一下子戳到心窝。当然,硬让自己往戏里钻也能找到一点儿似是而非。
“形式太复杂了。你可以说是一种为了迎合没耐心的现代观众的新花样,我也可以认为这样可以在内容不够充实的时候补漏——至少你在剧场的感觉是热热闹闹、眼花缭乱的。
“我看现代戏很少。我喜欢过去的老戏——有历史在那儿垫着,有力度视野也广,浓缩出的那点儿东西当然有份量。现代人总为鸡毛蒜皮患得患失。而且老本子是几代人传下来的。现代戏的本子十有八九是在屋子里憋出来的,就算再聪明再能对现代语言驾轻就熟的人,也往往只能头几部戏先声夺人。
“另外我想引用一位外国企业家的话:一个新产品‘新’的部分应占20%左右,少了过于保守引不起人的注意,多了又不易让人产生信赖感并接受。艺术上的探索能不能也套用商业原则,我说不好。但我觉得实验剧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刘莹不是那种过于保守的人。她和现在相当一部分有“体面”工作和收入的年轻人一样,生活方式和观点都处于主流和非主流之间。因而刘小姐的话在“圈外人”(观众)中具有代表性。

《爱情蚂蚁》剧照
在我的采访中,业内人上往往对流行音乐的渗入不以为然,甚至没感觉。29岁的朱小姐作为戏剧家协会某专业刊物的编辑,更愿意谈谈青年导演孟京辉和他的实验话剧。当然先从这部《爱情蚂蚁》说起。“我看过以色列的原著,感觉这出戏试图忠实于原著。但和孟京辉以前的几出戏一样,将原著的对白作了较大改动。但他好像总能抓住‘精气神’。他的戏把生活中很表象的东西‘滤去了’,有人说看起来很‘单薄’,我更倾向于说这是‘单纯’。当然,这个戏有些例外——太闷。这和节奏有关,一个钟头太长了,不过,也许这样刚好能表达那种让人‘烦了’的状态——准都别想高兴。(笑)
“孟京辉的很多戏想表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不同,他喜欢尝试新东西,我个人认为他追求的形式感并不算突兀。这几年他把《十日谈》中皇后与马夫的私情和中国戏中尼姑与和尚的私奔揉成实验剧《思凡》;又在导演法国让·雷奈的《阳台》时,把原作者‘戏剧是仪式’的观点用自己的方式阐释:剧中人同时扮演另一个角色——妓女同时还是阔太太,将军又扮受虐狂,甚至让一个角色跑到平台上抱着吉它唱汪国真的歌。他在实验话剧院门口的空地上演《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把德国剧作家笔下那个在战争期间饱受军医、长官摧残(从精神到肉体)的下等士兵沃伊采克与我国著名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揉在一起。前年在《我爱xxx》里,他让6个演员朗诵720句‘我爱……’,爱的内容乍看风马牛不相及,细想又似乎有内在联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营造的封闭空间——大铁栅栏落下,让人紧张。小剧场戏与空间的关系很值得探讨。我觉得孟京辉对什么都有热情,对事物的态度宽容。”
孟京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态度谦虚谨慎:“这部戏的前半部分是有问题——结构和节奏,这个问题不实演是不易看出来的。以后再有机会我会作调整。能给实验剧机会这让我很知足,别的不想多说了。”
小剧场的实验剧像不像时装制作中的立体裁剪?一块布披挂在模特身上并没有“已完成”的纸样,只有无数用来临时固定的大头针,剪缝随时调整它们,为的是做出一件更妥贴也更有个性的衣服。
能不能说对于戏剧界来说,实验剧的实验刚刚开始?对于观众,这个开始也不错——至少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新鲜有趣的方式和独特角度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
而孟京辉们也用不着提醒观众:“这个戏不只是表现爱情,而是城市中芸芸众生。”事实上那些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看戏又带着不同感觉消失在夜色中的观众的生活才是更有份量的戏。
一个在京城颇有些名气的报人说他家那只总爱蹲在窗台上俯视如蚁众生的猫像个哲学家。这个比方很有趣。可真是哲学家又怎么样?那些长于语言和逻辑的天才们从古到今不是一直也没搞清我们从哪来,又要到哪儿去吗?在这个多元的、复杂的时代,没人能在一部戏里说清生活,一如一篇文章里不能涵盖所有有价值的戏。
最要紧的是谁也别蹲在自家窗台上,隔着玻璃“俯看众生”。 孟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