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声雨声说改编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自从电视剧在大众文化娱乐中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后,不少名著、经典被改编之后上了屏幕,就像电影成为人们的重要文化娱乐项目后,年年都有名著被改编为电影。但无论是电视剧《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是电影《阿Q正传》、《围城》的改编,大约都没有像最近的《雷雨》改编这样引起如此广泛的质疑。
所有的质疑大多集中在“改编”所具有的权限上。之所以电视剧《雷雨》的改编激起了大的动静,可能一个原因是读过原作或看过舞台剧并深有偏爱的人们觉得改编得有点离谱。
我也觉得离谱,问题在于离谱是否是不对的?
80年代,上海昆剧团曾演出过改编自莎士比亚剧作的昆剧《麦克白》。此剧还竟然到莎士比亚的老家英国演了一圈。昆剧《麦克白》与莎剧《麦克白》肯定是大大地不同,它的场次与原剧不同,演绎的重心也不一样,表现形式更可想而知的殊异。将一个英国人熟知的莎士比亚作很是极端的重新定位,观众自然是大感陌生。
当时一位观看了此剧的评论家看出,在莎剧中有很多人物内省过程,而很多事件性的内容放在舞台之外;而昆剧把打打杀杀、幽灵等都摆上了舞台。这位评论家看着台上那一套陌生的符号系统,甚至不知道该把它看作是悲剧、喜剧、情节剧,还是滑稽戏或马戏。但她毕竟训练有素,面对这出戏,观者最好的办法就是专注于场面的戏剧可能性,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对原剧真实意义的偏离。
看惯了话剧《麦克白》的观众面对昆剧必得将自己重新定位,因为在昆剧的语言代码中,最重要的段子是唱出来的,从而也就受制于音乐对原剧的变形,还有动作代码在昆剧中也有相应的变形,所以注重音乐和动作表现的昆剧在改编话剧时一定要把“戏”集中在能以相应形式表现的段子上。
《雷雨》从舞台搬到电视上,改编所要面对的受众是电视剧观众,对于最广泛的电视观众,文学修养的程度差异极大,因此要求电视剧随俗明了,线索清晰直接。再者,通常人们在观看电视剧时的一般期待不是想接受文学训练,也不是想受一番高深的教育。可能也正因为如此,通常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电视剧都是情节剧。
商业上的成功表明收视率高,表明它吸引了数量众多的观众。

而话剧限于舞台之上,它要求作品的结构性要强,不然无法把复杂的戏剧冲突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场地中完整呈现。
电视剧《雷雨》的改编者显然注意到了话剧与电视剧这两种不同的载体应有不同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下,《雷雨》从舞台上的结构剧变成了电视中的情节剧。
既然是让人吃完晚饭慢慢看的情节剧,它就得有情节,于是在话剧《雷雨》中,很多幕后的前因和冲突背景,甚至人物性格的发展都被拉到了幕前。
比如,在话剧中,蘩漪是一个神经质的、偏执的、阴郁的女人,在我第一次看《雷雨》时,就试图猜测过,“她怎么这样,受了多大的委曲?老周怎么欺侮她了?”这种猜测只是人之常情。同样,戏终了,心肠软的人也许很替那几个死了的人物大感惋惜,“要是他们不死多好,如果不死会怎样呢”?这种猜测和惋惜当然不是对戏剧的艺术上的要求,只是一种自然倾向。
改编者显然在这种自然倾向上发挥了一下想象力。
于是,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年轻时的蘩漪,这时她显然还没被压抑坏,漂亮、热情而矜持,挺正常一个人。在慢慢铺展开
来的情节中,她一天天变了样。这也许就是改编者所说的“详尽的补充”。同类的详尽补充也势在必然。
可能结局的改写比“详尽的补充”更让人不适。但是,让蘩漪这样一个敢恨敢爱的人也敢死,让四凤、周冲这两个非重要的人物活着,诸如此类,也可算是一种解释,一种演绎。
其实,完全可以把改编看作是一种创作,在法律上获得了改编权之后,想怎么改是一个创作的活儿,那么,活儿做成什么样该是改编者的事。所谓与原作的关系大概保持在一种建设性的相似上就可接受,改编者有必要一定“忠实”于原作吗?《三国演义》小说显然改写自史书《三国志》,它忠实了《三国志》吗?没人提出这样的质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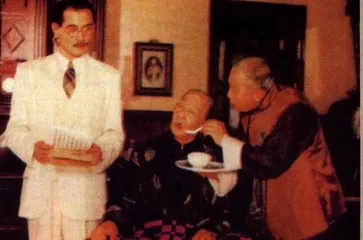
对于《雷雨》电视剧,有人以“重写经典”为题评价该剧,有人则疾呼“捍卫经典”,似乎经典是论题的中心,我倒觉得中心论题其实是大众文化的样式。之所以很多评论围着“经典”说事儿,原因也许是该剧导演李少红所说:经典进入文化市场操作,使一些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大众文化市场的形式,使文化作品的也会在形态上多样化,在不同形态上呈现的作品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同文化形态对经典的改编也会越来越多样化。电脑游戏中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正在编写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游戏软件。游戏软件中的经典名著和历史情节必定是另一种趣味,肯定与读原作或历史书不一样,它遵循的规则要易于电脑操作并有游戏之趣。如果有一天把《雷雨》编成电脑游戏软件,不知将又是怎样一番天地,不可能指望在玩这个软件时引起看话剧时的感受和经验。
几天前,我刚读到一篇杂文,说的是有关“精神贵族”与“贵族精神”的不同。这篇杂文与围绕《雷雨》的争论无关,但是“精神贵族”也许与此有点关系。精神贵族总是力图以自己的趣味规定非贵族的趣味。是不是告诉大众应该怎么读经典的教导也属精神贵族之为?精神贵族都比较严肃,体谅不了平民百姓的乐趣。
改编经典名著,无论改成什么样都不能构成对经典的损害。香港有一部改编的电影《雷雨》,其中甚至有周朴园与侍萍、与蘩漪的床上戏,而舞台上的《雷雨》依然如故。喜爱《雷雨》话剧的还能看到,至少能读到它,再不济还能在记忆中常常回味。这种“喜爱”是电视剧或电影瓦解不了的,反过来,在文化产品进入商业操作后,不同的观赏方式也是这种“喜爱”阻挡不了的。
李少红借用了一比喻,说,话剧《雷雨》是小泥壶泡茶,电视剧《雷雨》是大铜壶,谁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不能在大铜壶里找小泥壶的茶味。如果小泥壶泡的茶倒在大铜壶里,就一壶底儿,够谁喝的?
被改编的作品通常是经典名著,因为经典作品有着一般作品不可比的内在张力,这大概也就是之所以为经典的缘故。改编名著有了合理的理由之后,是否要保留原作的韵味又是另一回事儿了。
凡是名著,我们都对它有着一系列的带有普遍性的阅读,这种惯常的、经验式的阅读被一位爱尔兰批评家称为“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的”阅读。有时作者本人也会在意识形态下解说自己的作品。但是这种阅读是大可怀疑的,至少它肯定不是唯一的阅读方式。
我们阅读《雷雨》总是把它视之为反封建作品,原创思想也是如此。但是,封建被反了几十年的今天,它不好看了吗?李少红的阅读关注在人物的感情经历上。她说:“在反封建不再成为社会主题的今天,拨开阶级、社会层面,我看到这样一些活生生的男女,他们在感情生活与理性世界发生冲突时,做出了相同或不同的选择。”这也许是现在更年轻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所以李少红在阅读中寻找的线索是,为什么周萍那么爱过蘩漪,而后又残忍地抛弃了她?周朴园为什么娶了蘩漪却又保留着侍萍的家具?男人和女人在经历情感和理智的选择时有什么不同?
在阅读《雷雨》本文时,激活这一部分的潜在内容自有道理,这样的确更能贴近大多数电视剧的观众。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各自的公式,参与策划的人说过,电视剧《雷雨》也是相当公式化的。既然各有各的公式,也各有各的韵味吧。
美国的《哈姆雷特》可以一反阴郁深思而变成充满行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变成摇滚、弄枪的一代,澳大利亚的《灰姑娘》可以爱上另一个人跟王子“byebye”,那么,让周朴园去鲁妈家小坐一会儿,让四风靠在周萍怀里有什么不可?
至于有些评论说,这些细节与旧时的时代风貌不符,就更有点“精神贵族”了,且不说对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一个正在探讨的哲学大题目,电视剧观众也不该被定位于历史研究者上。
当代的观赏必定有当代的理念。在改编中加进与当代意识相合拍的细节对于文化市场的操作是精明的。
围绕电视剧《雷雨》的争论,说明大众文化市场的强大和成熟,因为大众文化也堂而皇之地跻身于文化遗产的继承者之列了。
在我整理这篇文字时,一位基本不看电视剧的朋友按捺不住好奇,问:“这电视剧好看吗”?也许这才是真正值得说的题目。但是,这个问题大概是在大众文化对文化遗产的继承权得到承认之后才可能被认真回答。 文学麦克白电视剧雷雨李少红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