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的“指纹”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天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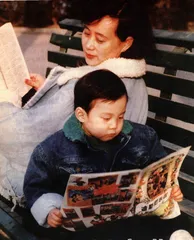
“当我把手伸向第十三个馒头的时候,我妈哭了……”我从朋友那儿听说牛育民先生这么个典故。随便聊聊吧,你母亲,你母亲和你。怎能随便?这是个沉重的话题。茶水添了又添,烟头碾了又碾。
互爱的,但又是悲剧性的
我妈现在不错,我也不错,但我们之间完蛋了。
我妈60多了,退休后不再做体力活,自己干,每年能挣20来万,身体好得再干20年没问题。我现在在《海内与海外》杂志社做广告发行,走上了“正道”,也混得过去。
但我妈和我爸一年半前分居了,她“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和我妈也闹僵了,有半年没见了。她不理我。她不接我电话我去看她,她让我把东西拎走。
我们是母子。我们曾经不是这样。
爱和耐心,即便如大理石,也会有 一天被磨成粉碎。是磨的。一点一点的苦难,一点一点的磨擦,一点一点的伤害。一件衣服,破了又缝,缝了又补,总有一天不能穿了。
在这件衣服还是崭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如何珍惜如何爱护。
我让她伤心透了。我从来就不是好孩子。
小时候,我们家住北京水碓子那一带,我是远近闻名的“傻民”,玩疯了。我们几十几百个孩子在春融秋冻之季组成“踏冰队”,沿着河走,像猫一样轻。不停地打滑不停地掉进冰窟窿,我们玩的就是这个,我们还必须不会游泳。那个季节,我的棉衣棉鞋从来都是湿的。等我妈从冰窟窿里把我拉出来等给我换了干衣服我就又去踏冰了。
我们还组织“别动队”(谁也别想惹我们的意思),去水库“漂流”,塑料桶弄个洞钻进去,拿竹竿撑着。我们点着汽油浸过的棉条在两岸飞跑,烧苇子,把河变成火龙。
我们在5层楼顶房沿儿上用报纸包了细土面码成一圈,建成烽火台。一大群挂钥匙的孩子去附近菜地偷东西,“值班战士”站在烽火台上,一有敌情跳上烽火台沿着房沿儿飞跑,让溅起来的沙土弥漫四周“掩护战友”……
那天我妈晕过去了,之后3天不能上班——她偶然提前下班看见他儿子在10几米高的楼顶狂奔。
我妈在我每件新衣服的膝盖和屁股那儿打补丁,我妈每天担心儿子能不能活着回家。
饥饿、粮票、棒子面,是使我少年时代天天不踏实的3样东西。
我15岁的时候就长到一米八七。我姐一米七三。我妈每天早晨给我俩准备的早点是一人一盆蒸米饭。我上午10点就饿得逃学了。
我爸妈都是普通人。我妈是新华书店的装卸工,我爸也是书店一般干部。我妈把能换粮票的东西都换成粮票,还得受人接济。我当时不干好事,弄了5块钱,听说我妈单位有个大爷一人挣钱养7口人,就想把这钱给他。他不要,反倒塞我一沓粮票,说给我妈的。我妈还不如他。
我妈心好,老家来人在我们家吃住长年不断。每次饭前我和我姐都把筷子数了又数,正好4双,生怕多了。因为我妈神经质,她有预感,要是多拿了双筷子她就哭——老家又要来人了。
我们家天天吃棒子面。
孩子们接受舞蹈训练,妈妈们在一旁耐心等待
除了吃饭,我妈还操心别的。1976年地震,大家都从楼里搬出来住外头,防震棚没搭好,每人早晨一身蚊子包。就我没有。我跟他们吹,我B2多,蚊子怕我。可有一天我发现我和大家一样,但是多了个妈妈。
那些天我搞个小初恋,每天回来老晚。有一天不高兴,躺下眯着眼睡不着——我妈以为我睡了,给我摇了一晚上扇子。过后几天我装睡,我妈天天如此。我在被窝里哭了。
我16岁起不大淘气了,我不能淘气了,我出了门连家都找不着。16岁到20岁那5年,我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什么都忘,整夜失眠,生活不能自理完全是个废人了。我妈每天把我当天要做的事写在小纸条上。1979年高考,我不想去了,我妈说,“民,去吧。你考1分都光荣。没关系,妈信你。”我想望子成龙这事儿是瞎说,母亲指望孩子的不是出人头地,而是平平安安在身边。
我19岁,1米87,我妈用自行车推我去三田屯考场。我不干,我妈说,“妈小时候推你上幼儿园,现在推你去高考。”我第一场考试完了,出门就朝回家的相反方向走,我妈跑来领我,大伙都看着,我妈像两军交战领俘虏一样把我从夹缝中领回来。我差5分没进录取线。
我后来也一直不是什么好人。瞎闯。我21岁当了首都机场构件厂厂长。25岁失了业,欠债27万。28岁找着工作,临时工。我妈天天为我提心吊胆。她总有一天要麻木的。
我没考上大学,就去机场当工人。一个月回趟家。那段时间我和我妈关系最好。我当厂长也让我妈骄傲了一阵子。但我却不断打破她的希望。
我今年37岁了。有了女儿。我不知道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希望。但我爱我母亲。我一直生活在她的影子里。我们很多地方酷似,我们对物质生活不够讲究,我们敬业,我们想挣脱命运。但我们永远别扭,在日常生活上。我不知道怎么回忆那些细节,太多太让人伤心了。我们都太孤独了吧。
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悲剧性的。我们的爱错开了。我但愿这是我们个人间的事。但我知道更深的原因不是,它说不清,窘困,伤害,或许还有人性本身的缺憾。我和母亲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吧。没有什么是单纯的,母爱也不是。
“作为母亲,我一直在‘得到’,而不是‘付出’”。中国科学院的施武女士对母子关系的独到见解的理由是女儿使她体验到更完整的生命,更本质的生活……
因为女儿,生活变得脚踏实地
我女儿妞妞3岁了。她每天都有新变化。对我来说,她已不是一个偶然的存在,虽然她的降生有点儿侥幸。
1993年,我结婚的第九年。读书、教课和丈夫在一起、与朋友聚会,我的生活一如既往,满满的,不觉得缺什么。也是那年春天,我怀孕了,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
年龄在不断接近生育的临界点,要不要孩子成了个问题。
去医院流产三次都没下狠心。每次挂了号,坐在台阶上,寻思寻思,回家,半个月后再来。到第三次的时候医生说“孩子长得不错”,劝我别做了,“没有孩子你不知道缺什么,有了孩子你就知道不一样了”。但最后替我下决心的还是我的感觉,对生命的感觉——5个月的小生命这拱一下那儿扑一下。我能感到她的小脑袋和小胳膊了。那种既外在于你又内在于你的生命不再是个概念了,而是冲击心智的了。
孩子快降生了,小衣服小被小床什么都没准备。与我几乎同时怀孕的一位朋友天天忙着做衣做被还要求老天爷保佑母子平安。我可不想这样,什么也别来干扰我,就我这样儿,就能把孩子顺顺利利生下来。我还生怕老天爷注意到我们呢。头一次,我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勇气保护另一个生命。
孩子降生了,拿来别人孩子的旧衣服,两个沙发方墩一拼就是小床。
护士把红乎乎的一个小血人儿在我眼前一晃,“女孩啊”。她的哭声可真粗,像个小老头儿。1小时以后,妞妞靠在怀里吸奶了,那感觉就不一样儿了。
一个迷迷糊糊的小生命,充分信任你,完全依赖你。你能感觉到乳汁在乳腺里流动,你发现自己对另一个生命负有责任,这份责任增加了你生命的份量。
是母乳还是喝牛奶?一个是对孩子有益,一个是对自己体形无益。但两种可能在我看根本没可比性。如果说巧克力和体形之间孰重孰轻还可称称比比,可孩子健康和三围之间,根本就是泰山和鸿毛的关系。
看着孩子伏在怀里,细细淡淡的睫毛,似睁似闭的小眼睛,我觉得自己无比强壮。怀疑、虚无、忧郁真成了为赋新词强说愁。
断奶和分床还算顺利。在我和女儿之间,我努力建立的是理性上的信任,而不是放任动物性的依赖。

一位自愿抚养孤儿的男性公民,在“母亲节”这一天获得中华绿荫儿童村颁发的“母亲证”(F·B·PHOTO摄影)
后来上幼儿园,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想让孩子独立去探索与同龄伙伴如何相处。妞妞没有一般孩子的幼儿园恐惧症,头一个月我每天只送1个小时,第二个月2小时……顺延下来,妞妞在幼儿园能像在家一样自如快乐了。
看着一个从你身体中分离出来的生命越来越复杂,离你越来越远了,是既伤心又欣慰的事,毕竟,她是在你的关注下长大的。
对妞妞的教育,我属于最“放任”那一类。我从没强迫过她,从没说过“一定”“不许”一类的话。我带妞妞去北大西门看麦田,一年四季都去,秋收后我把拾的麦穗碾碎了,炒熟了做成饼子给她吃,告诉妞妞面包馒头的来历。我希望女儿淡泊,清爽,本质一些。
妞妞在书店扒着我耳朵说话,还“警告”别人“不许大声讲话”,妞妞要是哭了,总要说出为什么,妞妞老因为要把最后几页小画书看完尿了裤子……
怎么谈得上“麻烦”呢?有了孩子,我的生活更真实了。喂孩子,洗尿布,买菜,洗衣,做饭……都变得那么有乐趣,家长里短成了最光明的话题。我甚至开始有了关于生命和生活的新定义,以前的疏懒和轻松算得什么?有了孩子,日常生活增加了“必须”“应该”的事情,琐碎和平常使我的感觉更接近大地。养儿育女绝不是过眼烟云,它像农民耕田种地收获一样实在。
有了妞妞,除了作息时间的调整,除了困,我学会了营养配餐,习惯了吃捣得碎熬得烂的食物末末,还“允许”别人家的小孩子在地板上撒尿了……我并没丧失什么“自我”——如果当公司经理是一种自我实现,那当一个合格的妈妈不也是对“自我”的另一诠释吗?
我一直在“获取”,而不是“给予”。我喜欢夏天,不再隔着棉被,直接接触她的皮肤,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要握着她的手,不知道是谁在安慰谁……如果要有种测量人的快感的话,我想一个母亲获得的远比孩子多。
每一细节都铭记在心,不是母亲养育了儿女,而是儿女塑造了母亲。
妞妞一直是我和丈夫共同带大的。第一年当然是最忙的。孩子尿了,我这边拆包,他那边接过尿布,甩进水盆,我给女儿擦干,他已展开新的布包……从手忙脚乱到流水作业般地熟练,这当中无需眼神的传递,无需言语的表白,完全彻底的默契……柴米油盐进入了厨房,吃喝拉撒进入了视界,夫妻也就真正进入了生活。家在共同哺育生命的艰辛中一天天清晰……
丈夫说我是个夸大其辞的母亲。也许吧。我从小就生活在母亲的饥渴之中,我对妞妞的爱可能是出于下意识的补偿心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做母亲还是做个无牵无挂的“新女性”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元的时代,是自由选择的问题。但你一旦做了,你便责任重大,只有做好的权利,没有疏忽的借口。
烦恼?啊,对,我女儿最近迷上了看天气预报查地图,可我一直没在她醒着的时间找到她要的“世界天气预报”。
“7年了,最艰难的不在生活上,而是感情上……”
作为单亲母亲,北京地铁阜城门站段艺萍女士,谈起儿子,谈起儿子刚刚过去的15岁生日……
我和儿子的感情又敏感又顽强
上上个星期六是张硕的生日。我下班回家干等不见人影。晚上10点半,张硕前脚进家门,爷爷后脚跟进来。
自从我丈夫因病去世,孩子一直住在爷爷那儿,每星期回来一次开始是因为我倒班,后来我做了站长,上班有点下班没点,爷爷那边是个大家庭。孩子大了事多了。几天前张硕没完成作业,姑姑打侄子,爷爷骂姑姑,姑姑找奶奶。乱了。而生日这天,张硕放学晚了,叔叔不让上楼,孩子蹲在楼根儿反省,爷爷急了,找到我这边来了。
孩子住在那边,由奶奶姑姑他们照顾,我打心里感激。姑姑叔叔怕硕儿学坏,严教有理。可是最好别往脸上打,伤了孩子自尊……可能还是我不好,如果硕儿天天在我身边……我从没打过他……
扶着爷爷,拽着硕儿,当晚,我们在附近的烤肉宛点两菜,生日就算过了。
打了车送走爷爷,我和硕儿边上楼边聊天。
孩子生日,高兴点吧。不谈考试、名次、分班,不谈爸爸……硕儿是个心细重感情的孩子。我俩东拉西扯,没什么正经。我问他:“你们班有抽烟的吗?”他说:“有啊。”我问:“你抽过吗?”他说:“不能说抽也不能说没抽。就那次在厕所。我们班好几个男生都在,非让我试试,我不抽不大好。”我问他:“好抽吗?”他说:“别提,头晕脑胀,我跟他们说以后别害我了。”
儿子桌上摆着同学送的生日礼物,心形像框,嵌了张小男孩小女孩亲亲密密的照片。我问他:“你们班有搞对象的吗?”他反问我:“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事,问着玩儿。”孩子说:“有。”“多吗?”“不少。”我吞吞吐吐地再问:“那你有吗?”他说:“别胡说,妈。不过……有个小女孩跟我挺好的。”“就是前两天给你打电话的?”“嗯。她转学了,我心里空荡荡的。”“那回你那个男同学走,你怎么想?”“也空荡荡的。”于是我说:“就是。所以你这不叫谈恋爱。你们约会过?”
“没。就一起买过一次笔。”
我不知道别的妈妈遇到类似的事儿怎么办。反正我想小孩子的事儿,你越把它当事儿它就越严重,这么开玩笑似地聊聊,也许更好一些。张硕是个老实孩子,有点儿柔弱,有点儿太憨了。
一年半前,张硕第一回骑自行车上马路就惹了事,挂倒了前面骑车的阿姨,61路又把人拖出五六米。我从外面回来听开电梯的说让去交通大队领孩子,汗毛都竖起来了。硕儿没事儿,但给吓坏了。在交通队人家开口就问“你爸在哪儿”,13岁的孩子哭了,受不住了。又是我们大人对不住他。
硕儿第二天发烧,我买了水果去医院看受伤的阿姨。这事儿拖了一年多,医药费我和61路共同担着,花了两万了吧。我很少和硕儿再提这事儿。孩子不容易啊。
7年来,多亏公公婆婆帮着照管,生活上还算顺利,可是在感情上,我和儿子之间,更敏感更依恋也更艰难。
硕儿怕我说老说病。我有时候开玩笑说,“等我老了进敬老院,不给你和你媳妇添麻烦”,他就急了,“哪来的媳妇啊。她要是不待你好,我也不娶她。”
前些日子我病了,他端水递药忙前忙后,也算不上什么,可我看得出他心里的焦灼和忧虑,他拉着我的手说,“妈,你快好吧。你要是……我不更惨了?”
我有时候真不知道,在我和儿子之间谁更依赖谁。硕儿一天比一天懂事,像个大人了。以前清明扫墓,总是我劝他;今年倒反过来,儿子把墓碑上的字描了又描,红着眼圈,扶着我。
我爱人去世这么多年了,亲戚朋友都劝我“再找一个”,我从没放在心上,现在居然硕儿也劝我了。而且孩子长大了,心理生理发生好多变化,做母亲的有时候很尴尬;报上又说“不健全的家庭结构”对孩子性格不好,容易孤僻,女性化,将来孩子又要夹在寡母和妻子之间……
我现在正处着一个,硕儿很支持,他们相处得不错。孩子心细,害怕我老想着他耽搁着,总跟我说,“叔叔对我挺好。管你自己吧。别老想着我。”
我和儿子谈“感情的事儿”是不是太早了?但“感情”又是我们彼此最坚信对方的。我们在对方心目中都是“第一位的”。
我开玩笑说硕儿是白眼狼,爷爷奶奶带你这么多年多不容易啊,你却老想着这边。我想在这边,硕儿多一份独立的空间,多一个平等的聊天的伙伴吧。我也想接儿子回来,多和儿子在一起可又怕伤了老人的心。
下星期吧,下星期我到爷爷奶奶那边去一趟,商量商量。我常想,像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我和儿子之间的感情又细弱又顽强,需要更精心的呵护,更多的交流和理解。
说跑题了是吗?我挺高兴挺欣慰的。对儿子的期待?最切近的?那就是他这次考试进入前8名——上次他考第十一,然后我给他买双耐克鞋,500多,我已经答应他了。 张硕母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