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眼界
作者:邢海洋(文 / 邢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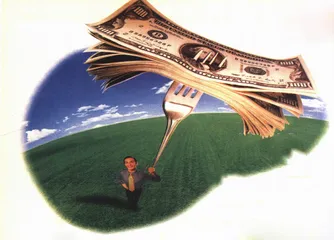
爱家基金
温州西部山区的呈岸村虽处偏僻之乡,却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基金会。每年正月,散落在上海、四川、温州、湖南等地城市中的周家子女都要回到祖居地,济济一堂,参加“周氏爱家基金会”的年会。到今年,基金会已走过5个年头。
周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山坳里,种地过活,父辈三兄弟一姐妹是靠吃番薯干、放牛羊长大的庄稼人。近四年来他们的子女走出大山,靠经商起家,在全国各地开店办厂,周家遂成一方望族。周氏子女离乡离土,第三代几乎尽在城市中就学。唯有每年春节,全家人才尽回家乡。
富裕起来的人们如何凝聚在一起?在温州,曾有许多地方大修祠堂,企望大家族财旺福旺,子孙绵绵;也有人迎佛修庙,甚或大建阴宅。而周家却选择了建立基金会。爱家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缘起于第二代事业有成的中年人对子女成长、赡养老人等问题的考虑。基金原由各家分摊,后改为由全体家庭成员自愿捐资。
基金会有章程。理事会由第二代12人中选出8名组成,理事长由理事们以无记名形式推选。每年正月的年会里既有“理事长”作总结报告,又有晚辈代表做演讲,还有成员民主提案和一系列模范(包括丈夫、妻子、家庭、孩子)的评选。“章程”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由基金会发给800元的补助,对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不能完成学业的则予以援助。
章程中全家文化素质目标制定得非常具体,第三代中要普及大学教育。时至今日,周家已出了一名研究生、一名本科生和一名中专生。研究生在西南财经大学读书,毕业于上海外经学院的大学生则接替父亲,管理起服饰公司。
异类资本家
周家以商兴家,子侄辈承继父业本不足为奇,这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家族产业世代相袭的基本模式。但来自大洋彼岸,号称世界第一大资本家巴菲特的持家风范却颇使人觉得,有钱人中开始有异类出现。
巴菲特的儿子豪伊原享有一份从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如果他把这笔钱一直留在父亲的公司里,30%的年增长率将使他温饱有余。不过,他还是希望有所作为,于是开了一家挖土公司,可惜好景不长,公司以倒闭告终,只好又回到巴菲特的公司里做职员,作为副业,还租块地种庄稼。
以巴菲特的风格,他是绝不关照子女的。当女儿需要20元在机场停车时,她必须给父亲带回发票,当他给孩子们贷款时,双方要订协议,白纸黑字,连利息都不肯优惠一点儿。这次,巴菲特发慈悲,主动提出买个农场,租给豪伊种地,当然,也没有如此便宜,农场价格封顶,这样一来,豪伊跑了上百个农场,皆因出价低备受奚落。最终,他们用30万美元买下一家农场,这也是巴菲特风格的一部分,他总是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买股票。
在豪伊种地的6年里,巴菲特只去过两次农场,他对豪伊的天地不屑一顾,见面的头一句话就是:“拿租金来,可不要少了。”在他眼中,这只是场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是商品,有一次,他讽刺道:“没人会到超市买豪伊·巴菲特牌的玉米的。”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富不过三代”,指的是家业总不免败落在纨绔子弟手里。在世界第一巨富巴菲特这儿,问题却不会这么复杂,他根本不打算把产业传给子女。他曾说过,他撒手归西之时,只会给每个子女几十万美元的遗赠,这是一个限度,因为超过之后人们就可能靠金钱的余荫过富裕的生活。现在,他的资产已经达到166亿,几十万连九牛一毛或许都算不上。巴菲特的姑姑也是他悭吝政策的“受害者”之一,姑姑买卖期权高筑债台140万美元,巴菲特只好为她安排生计,月给津贴,不过代她偿债的事却没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
在美国,曾有过一个关于家族成长的流行说法,第一代拓荒者艰苦辛勤劳作,干的是不体面的体力活,他们积聚财富,供子读书,使第二代改换门庭,兴建实业,成为社会名流,而到了第三代,衣食无忧的富家子们过腻了体面的上流生活,追逐个性,有天赋的就成了艺术家。巴菲特的身上似乎也能体现出这种传统的烙印,却又极是不同。他父亲是国会议员,严肃的自由主义战士,他却成为一个资本家,生活中处处以金钱为准则,到了儿辈,倒是出了个音乐家,可有关传统的叙述在这里却全变了味。
巴菲持仍住在50年代花31500美元买的木结构的房子里,守着一个座钟和他的金山,这使人联想到一百多年前老葛朗台的形象,形象里凝聚着原始积累中资本主义的血腥。时过境迁,巴菲特面露睿智的微笑,向崇拜他的投资者讲经布道,其乐融融,一副和谐的人间美景,不由得使人怀疑,资本主义是不是变了呢?

子承父业是家族产业世代相袭的基本模式
资本家的逻辑
20世纪初的资本家喜欢购豪宅,筑大屋,衣着亮丽。现在的资本家们却大为不同,盖茨的衬衣上经常有洞出现,曾经是美国首富的沃马特连锁店的老板因跟员工打赌,跑到华尔街上穿草裙跳夏威夷舞,这的确是先辈们不曾有过的经历,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呢?
巴菲特收购了一家叫《新闻晚报》的报纸,当然是在它处于亏损时收购的。巴菲特开始了挤垮竞争对手《信使快报》的战略,正当关键阶段,卡车司机们找上门来,要求增加人手,同时还要求不工作的时候也有薪水,否则就罢工。工会开始与董事会谈判,工人纠察队则占领了卡车,记者们停止工作并拿走纸版,一切陷于瘫痪。
据说,巴菲特当时大汗淋漓。如果报纸长期停产,竞争对手会要了他的命。要么赶紧复工,要么关门大吉,如果妥协,其他工会也会找上门来。结果,他宣布,如果报纸不能出版,他就不发工资,解雇全体员工。强硬的资本家最终迫使司机们让步了。
资本主义的逻辑从未变化。《新闻晚报》把《信使快报》熬垮了台,记者们希望从胜利中分一杯羹,有人问他:“给新闻办公室的人实行分红制怎么样?”得到冷冷的回答:“(新闻办公室)没有谁能增加利润。”巴菲特只相信冷酷而公平的资本家信条,是老板们在竞争中冒着破产的风险苦苦支撑,而雇员们却不分担损失。
这就牵扯到一个葛朗台和巴菲特共同面临的问题,那么多钱的最终去向。生前,他们用钱去生钱,可死后呢?葛朗台只给出了一个平庸的答案,遗传给女儿欧也妮,而巴菲特却想得开,他要为全世界的计划生育事业做贡献。
这也是巴菲特的逻辑,很像投资,他拒绝搞“多元化”,只愿把钱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他像马尔萨斯那样,担心人口过多会引起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住房、食品或者活动空间。他也相信人口过多会引起战争,而核战争最终将导致人类灭亡。计划生育是一笔大投资,但绝不像投资可口可乐那样立竿见影。巴菲特很想看看,社会效益是不是也像经济效益那样产生直接的影响。巴菲特已经开始了他的实践,但是,每拿走一个钱就少了个挣钱的工具,所以人们常对他的捐款报以嘲笑。
人口少了,拿红利的人相应减少,红利额自然提高,这也是自亨利·福特以来大生产的最基本信条之一。福特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达70亿美元,巴菲特身后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布什和克林顿一道竞选美国总统的亿万富翁佩罗就宣称:“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应用,……我们资助那些需要资助的人,我们资助那些能够互相帮助的人,但我们不会无原则无目的地将钱捐献出去,这不会有任何好处。比如说,绝不会把钱用于社会福利。”
佩罗在资助教育、医学研究、艺术等方面从不吝惜,因为他认为这方面的投资最终会带来收益。他捐了1000万美元在达拉斯盖一栋交响音乐厅,捐800万建市立动物园,而且还捐250万用于小孩的教育。
金钱的流向的确是个世界性话题。当中国刚刚步入殷实之家的商人们组建家庭基金的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基金已在进行各式各样的社会实验。商人们的本质却从未变过,他们只希望钱能生钱,而且希望这种状况世代延续,有的只希望子孙富庶,有的则想得更多。 巴菲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