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会升值吗?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君梅)

也许是电视剧《东边日出西边雨》勾起了现代人潜意识里的一种渴望,北京兴起了玩泥巴、拉坯、烧陶。在那部曾在北京地区创下较高收视率的电视剧里,王志文饰演的男主角一气儿把他那辆吉普车开到京郊一个“世外桃源”,置了块地,然后不食人间烟火地烧起陶来。

戏外的人们也急切地想加入这个行列。但有条件在郊外置地建窑的人毕竟是少数。商家敏感地捕捉到这样的气息。1996年春,北京青年宫首次将陶艺列入他们的经营项目。一年之后,北京又有了一家占地400平方米,专营“手工艺活动”的五色土工艺坊。他们的项目不仅有“玩泥巴”(陶艺),还包括泥塑、染织、造纸、彩绘、插花等。这家店为手工明码标价:单项价格一般是2小时40元(陶艺1小时40元)。通票60元,2小时内可以随意在各项目上露一手。陶艺和彩绘(瓷盘、瓷砖)另加烧制费。在规定时间内,一般人可扎染两块方巾、造5张彩纸。但拉陶坯如果没人手把手教,第一次十有八九“不成器”。他们还打算开设晚场,推出情侣票、月票、季票。该店还收集、展示、销售来自国内外艺术家、农民、儿童、少数民族地区的手工艺作品。
店主是一对中西合璧的中年夫妇。加拿大的周卡特先生和他的中国夫人何虹雨。他们一个是加拿大注册建筑师,一个在美国获得建筑专业的博士学位。他们90年初回国。“早有开一家手工作坊的想法,简直可以说是梦想,居然就实现了。”何女士说,“在西方,‘自己动手参与各种活动’这种概念并不新。而在中国,不失为一种比较新的娱乐方式。而且选纸、印染、制陶这些古老的技艺正随现代化逐渐减弱,把现代的一些东西,比如一些理念溶入古老的技艺,这可说是一种文化的传延。”
据说陶艺最受欢迎。扎染、造纸、彩绘是孩子们必做的。
“来这儿的客人两个年龄段的最多:5—13岁;20—30岁。我们不好意思问客人的收入,但我感觉来的年轻人至少是月薪2000元以上的。家长带孩子来的,当然未必是中高收入家庭的。另外,一些有钱有闲的商人太太、使馆武官的夫人、在京国际小学的外国孩子也是常客。”
每个人在作坊里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不同收获。21岁的小唐是学国际贸易的,现在他暂时在店里当制陶指导教师,“我也是学了制陶才迷上它的。从和泥巴开始,每一个过程都那么吸引我,制陶机底盘周而复始地转,有点像哲学。”
一位女士拿来一件丝绸衬衣——那是她送给丈夫的结婚礼物,可惜沾了污渍洗不掉。当这件衬衣最终在“五色土”被扎染出很多不经意的图案,可以想象这对夫妇的惊喜。
一个6岁的美国男孩告诉他爸爸,他造的彩纸是“Sun is going down”(日落)。
也有人对这种“花钱干活”不以为然。也许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才会回归。中国很多家庭刚刚脱贫,很多家庭还陷于繁重的家务劳动。在漫长的岁月里,手工制作一直是“劳动”的一部分,支撑生产和生活,它的文化价值被劳动的繁重艰辛淹没了。
在五色土工艺坊一进门的地方,摆了一架老旧的木制织布机。据说它曾被山东一家四代人使用过,已有100多年历史。店主“老周”强调它至今还可以织出各色古朴的长幅土棉布。所有来这里的人都围着它啧啧赞叹,但没谁非要用它织出一幅布来——都市中人希望在两三个钟头的休闲时光里“干出点儿什么”,比如扎染一块方巾、造几张纸、拉一个陶坯。而织一幅布多么辛苦。
现代人就是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生活着: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富裕便利,又频频回首来时路,为那些万劫不复的,或是渐已远去的东西黯然伤神。
这种心态其实早就被商家所察觉。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的许多城市,“手工”大量为商业所利用,其价值日显珍贵。
在一些老城区的胡同里,“手工制作旗袍、中式服装”的小店招牌多起来。一些百年老店也重整旗鼓,当年列入旧京“八大祥”的瑞蚨祥、谦祥益绸布老字号也在店中推出传统手工制作的服务。手工剪裁、滚边、盘扣的旗袍成为相当一部分都市女士的晚礼服。而内联升的千层底布鞋和绣花女鞋则成为现代人交往中“有文化品味的礼品”的象征。
不同民族的、不同类型的手工制品一起相聚在世纪末的都市。有人迷恋繁复精细的银制品,有人偏爱质朴的木珠子、陶珠子,“前卫”的、穿着有“猫须”牛仔裤的年轻人索性把皮绳、麻绳打结,系在颈上、腕间。有人甚至把啤酒、“可乐”瓶盖打个洞作项坠儿。
一条“麻绳手链”可以卖到20多元,丝绳串几个陶珠子可以卖到百元。而有些东西更是不能讨价还价。我的朋友钟芳小姐在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工作,她说:“金有价,但制成首饰,它的价值就不能用秤来称了。银本身并不贵重,银制品的价值就在于它复杂的手工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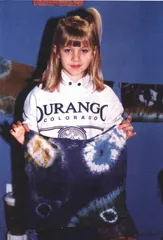
金发女孩与她的扎染作品
商家让我们明白:我们失去的只是钱,而得到的绝不是普通的商品。
从卖手工制品到卖手工制作的机会——做手工的权利真被商业垄断了吗?
我每天乘坐地铁,很多事已见怪不怪,但那天我还是很吃惊。对面那个穿“AC 米兰”足球服、戴小黄帽的胖男孩居然把书包放在一边玩起两根玻璃丝。那不是我们小的时候(70年代)或更早以前流行过的手工材料吗?那时流行用玻璃丝编各种动物造型的钥匙坠、玻璃茶杯套。这些年它几乎从我们记忆中消失了。男孩玩不出什么花样,他旁边坐的那个气质挺高雅的女士便手把手教他,直到下车……
玻璃丝让我想起小时候姐姐生病住院时,病友阿姨教她做的玻璃丝门帘还有八一电影厂一位叔叔用废电影胶片做的台灯罩。
现在我们重提手工,把它的价值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惜花钱买一个动手的机会,其实这样的机会从未远离我们。谁家没有几件手工制作的传家宝?我当然不一定非跟奶奶学绣“连理枝”,和姥姥学打“蝴蝶绊儿”,但可以跟母亲学织毛衣,像她那样善于多种编织技法的组合,像她那样谙熟不同颜色的搭配。在我眼里,她织的每一件毛衣都有很强的设计感。现在穿手织毛衣不仅不意味着穷酸、老土而且还可以说是令人羡慕的。和大机器生产的毛衣相比,它自然、它有人情味、它独一无二。我还很欣赏父亲多年前做的多宝格和音箱,尽管它们现在看上去挺土气。
现代人无疑需要轿车、金钱,但生活中这些生动的细节何尝不是一笔笔财富。城市的“金属味道”太重的时候,我们需要手工那种古朴自然、历久弥新的味道。没有哪种艺术能够不向“现代化”妥协(因而变得似是而非),只有手工仍保持它的原生态。 陶艺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