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财者的《告白》
作者:邢海洋(文 / 邢海洋)
含球在口
“这就好比现在你在超级市场里,推着小车准备购物,在拿牛奶的时候,你突然想起该买半脱脂牛奶。可是,正在拿半脱脂牛奶的一瞬间,你却发觉其价格已由每品脱30便士涨到60便士,你只好转回来买全脂牛奶。但是,你放眼望去,发现货架上所有货品的价格都已上涨很多,你进退两难了。”
这是尼克·利森在牢狱中写下的《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中的一段话,记录了他一天早晨步入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大厅时转瞬即逝的念头。这很像是一种梦境,几乎每一位在证券市场上错过机会的炒做者都有同感,但利森的问题还不只是错过了一个机会,在日经指数期货上,他拥有大量多头部位。而此时,市场却并不如他所预料,就如同逆水行舟,一旦支撑不住,身后就是暗礁和漩涡。
当日的日经指数在19250点左右,一升盘,利森就买进100份合约,但市场却出奇地平静,全球最大的投资集团摩根斯坦利和他较上了劲,都指望对方把价位推高,从中渔利。终于,利森开始了他的孤注一掷:“200份标价250,100份标价240,200份标价230,300份标价220,500份标价210,500份标价200。”新加坡金融期货交易所每天的成交在2万份左右,利森一口气就报出1800份,给人以攻其不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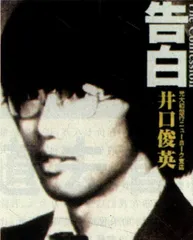
市场被激活了,散户们开始抢买,一分钟后,市价上升100点,随即停步不前。350点上则挂着大笔卖单,阻住价位上扬。人们通常把持有大量仓单称作“含球在口”,只有价位上得很高,含在利森口中的球才会顺利吐出,否则,市场的铁嘴钢牙就要合拢。这是他最怕看到的一件事,但价位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落。在350点,他曾报出100份卖单,却找不到买家;300点,他又报出500份,刚放下话筒,屏幕上就打出290的成交价位。想卖的没一份成交,可用于震摄人心的1800份合约却被汹涌的跌浪席卷一空。中午收市,日经225种股价指数期货降至19000点。指数期货的最基本作用是为买卖股票的投资者提供避风港,使他们规避由股价波动带来的风险。可作为投机者,利森的动机却是在波动中求利。最初,新加坡的金交所还是个小市场,交易者稀少,日经指数的价格常与日本大阪的交易所形成时差。巴林银行盯住这几秒钟的时差效应,由大阪操纵新加坡的买卖,微中取利。利森站在交易池边,手持电话,一边每隔两秒向大阪报一次价,一边向池内的马甲做出买卖手势。第一次,他们在新加坡以18580买进200份合约,同时在大阪以18590卖出,净挣1万6千镑。
这样的买卖没有一点儿风险,但交易必须在2.5秒内完成,不然,价格就会变化。随着新加坡市场的成熟,这种时差效应也迹近于无。利森于是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当他把全球最古老的巴林银行搞垮时,他才仅26岁,而时间也仅用了两年。
利森一如既往,只做短线交易,虽然在18000点的价位中几十点的差额根本算不上什么,但期货的保证金制度和巴林银行庞大的财富却使看似平和的买卖变成纯粹的赌博。终于,利森“含球在口”,成为市场上的困兽,要摆脱困境除了用更大量的资金改变市场的走向外别无他法,在他的欺骗下,巴林总部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汇入新加坡,含在口里的球迅速膨胀,再也吐不出。
1995年2月,利森选择了出逃,而不是在市场上认输。作为交易员,他彻底地失败了。
平淡的交易 巨额的亏空
利森蹲在新加坡的监狱里著书立说,大发横财,《我如何弄垮巴林银行》一出版即登上全球畅销书榜首,至今仍很走俏。利森借此赚的钱恐怕比他当交易员时的分红还多,此事不免令人心生艳羡。果然,时隔不久,也曾叱咤一时的日本大和银行的井口俊英也以《告白》为题,剖白心迹。此书一出,即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井口俊英写道:“起初,我觉得彻底完蛋了,当局拿走了我的房子,汽车和所有存款,我所有的,只是一些盥洗用品……呆在监狱里还是好的,在外面,我丢了工作,没有了一切……”
井口好像没有利森那样富于想象力,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利森望尘莫及。他以东方人特有的坚韧,12年如一日地赔钱,同时伪造帐目,直到赔掉11个亿,才自动罢手,这比利森的被迫出逃棋高一招。
一切都起源于1983年的一次不成功的买卖。那时井口是大和纽约分行的一名国债交易员,辛苦半年,为公司赚出5万美元,却在一天内尽数归还市场,这不能不使他焦虑。浮动利率债券本是波动非常小的品种,人们指望用它保值,身为银行交易员的井口则凭借大资金在这里赚取差价。大和是国债的经销商,井口一次买断1000万美元的债券,指望债券上市时市场上没买到的投资人会把价格抬起来。
事与愿违,价格反跌,井口只好按兵不动,这时他若卖出,则损失5万元,商人们告诉他,这是供过于求的缘故,耐心等上几天价格就会回升。可等到井口信心尽失时,价格又跌了0.2%,损失扩大到7万。
7万的损失几近天文数字,要在它上面再赚回来,至少得半年时间。井口可没时间等,他转到价格浮动更大的长期国债。当时30年期的国债每天都能动上几个点,井口便调动资金,随时准备在它上面捞回损失。经纪人告诉他,98.75的价位适合吃进,他毫不犹豫地申买了1000万美元。40分钟后,经纪人通知他全部成交,到了中午,价位跌到98,到下午,经纪人挂来电话向他致歉,因为此时的价位是97.75元。一天之内,井口再赔1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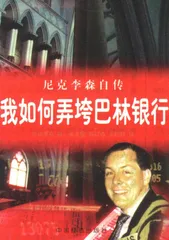
全球独家中文简体版授权 全球畅销书排行第一名
1984年春天,井口居住的新泽西州林肯公园发了一场大水,水漫上地面40厘米。早晨,孩子们下楼时,井口能听到踩水的声音。电没了,电话泡了,居民们都呆在家里,无法上班。井口牵着孩子们玩的橡皮筏,蹚水走在很少行人的大街上。他不能不去办公室,1.5亿未经批准的交易尚需了断,经纪人们如果在办公室里找不到他,3000万美元的损失将暴露。井口所能做的就是请求经纪们给他宽限时间,容他遮掩损失。此时,井口感到了他与家人的距离,他离婚了,同时,巨额亏空使他坐立不安。
井口想到自首,那是1987年末的事。但自首意味着将被开除,孩子的扶养费,前妻的生活费都会成问题,同事们也会受到牵连,这使井口一筹莫展。在公债上,他一如既往地赔钱,1988年1月已经累积2个亿,当然,这比起他1995年7月他向大和总部自首时报告的11个亿还仅是个零头。
奇妙的数字买卖
在银行里井口不仅做公债交易,还负责记录欠款单据和成交状况,如果需要,他可以把损失推迟一年再登录。1989年,大和总部派员来纽约支行查帐,纽约州银行管理机构也接到匿名举报,告之大和在国债上的巨额交易。审计师们勿勿而来,20分钟的讯问后,不了了之。1992年联邦储备银行派员检查,那家伙喝醉了,调查只持续了15分钟,甚至连银行里是不是有个交易室都没搞清楚。又有一次,监管人员对井口身兼交易与帐户管理双重工作表示质疑,因为这为内幕交易提供便利。但他们却未更进一步,指出交易与管理合一的更深层危险,而这正是井口的所作所为。有时,井口不得不把自己设想为一位福将,面对那么多常规或特殊审计,他从未出险。
来自日本总部的一个审计日程表使井口甚为惊讶,也颇宽慰。会计师们在纽约只驻足两天,在井口所在的市区营业部只呆一个早上。日程表更像度假计划,到达美国的第二周,代表团成员将举行一次美国本土经济考察,地点选在拉斯维加斯。井口不无嘲讽地想:轮盘赌没准是他们最热衷的调查项目。
利森作案时间短,没遇到那么多检查。不过,利森倒是有绝招,每次赔了钱,他都把交易记在一个户头为“88888”的帐号上,再在花旗银行虚拟一个存款帐户,仿佛赔出去的钱没进赢家的腰包,而是他们暂存在银行里的存款。
一位绰号“破坏者”的主管被派到新加坡,利森的感觉就像被绑在牙医的椅子上,就等着牙医来拔牙了。那时利森的损失已高达5000万英磅,而掩盖它的手法不过是几个假数字。如果把资产负债表简化一下,就会看到:
客户收支差1亿1千万——借方
新加坡金交所已收6000万——贷方
花旗银行存款5000万——贷方
如果“破坏者”到花旗银行去问问,或者干脆打个电话,她就会发现这笔钱子虚乌有。她是个很严肃的会计师,不苟言笑,在利森的数字迷宫中埋首3个星期,得出的审计报告上一片绿灯。报告上写道:“他同时是前台和后勤部门的经理,因此便有可能盗用集团的名义……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意清偿、记录这些交易。”这里,“破坏者”已经触摸到实质,可代之而来的却是建议总部派一名后勤经理。审计师还为利森总结出一套“低风险的,行之有效的交易模式”,为此,她还建议总部为利森补足短缺的资金。
难怪被捕后利森不断抱怨,若是在另一家银行,他就犯不了这么大的错误。
在做大笔的交易时,利森常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他把这称作买卖数字。他只要走上前,挥一挥手,就可以买进或卖出价值百万的东西,但它又不仅仅是“东西”,它不是牛奶不是面包,不是万一有一天世界末日来临时人们能用的东西。他买卖的东西叫期货和期权,大部分参与买卖的人甚至搞不清它代表着什么,但他们知道,这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一个行业只要数字随了你的愿,你就可以享用数字代表的一切。
数字不是大灾大难中人们能抓住的稻草,但在世界灭亡前,它的确意味着人们想要的东西,井口在接受《时代》采访时说:“我并不想抢劫一家银行。”但11亿美元甚至比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房子和汽车,11亿能买多少同样的房子和汽车呢?
或许只有把11亿看做11亿,把房子和汽车看做房子和汽车,才能理解井口俊英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