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秋天的鼓》到《她叫格蕾丝》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畅销书与排行榜
不出我们所料,经过圣诞假期的平淡之后,新年伊始,畅销书榜的小说类果然新书倍出。我们这期榜上所列的只是年初5周的前10名,其中竟然有10种新书。
从时间覆盖面上看,这10种新书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属于美国早期的历史,一本是《秋天的鼓》,另一本是《她叫格蕾丝》。前者讲的是美国独立前移民的辛劳和祈盼,在具体详尽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了一对夫妻的生活与爱情,评家认为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家世小说,书中的那对苏格兰夫妇极具代表性;后者则是一个历来众说纷纭的真实人物的再现。

第二类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故事;从内容上看,可归于间谍小说之列。进入90年代以来,东西方对垒的冷战局面至少表面上已经结束,原先那些以克格勃为主要对立面的间谍小说失去了现实意义,小说家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能够为众多读者接受的,自然就是二战背景了。本期排行榜上就有两部这一类的小说。第一部是丹尼尔·西尔瓦的《靠不住的间谍》。这部小说如同大家所熟悉的《针之眼》一样,也把焦点放到了生死攸关的诺曼底登陆的“D日行动”上,但主人公却是各为其主的一对男女,这样就把“忠”与“情”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可以说用惊险故事和爱情故事的双重吸引力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女主人公叫凯瑟琳·希雷克,是家住伦敦,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寡妇。她美貌热情,一方面热爱祖国,另一方面又是纳粹间谍(这一点作者如何处理,只有读了原书才能释疑)。男主人公叫阿尔弗雷德·维卡利,是个单身独居的天才,受命于丘吉尔,肩负着粉碎纳粹情报机构的重任——这又让我们联想起《针之眼》中那位历史学家。这一对男女之间的斗争与纠葛跌宕起伏,恐怕不难想象。另一部是由格里芬所著的《鲜血与光荣》,地点选在了远离欧亚主战场的阿根廷。老谋深算的希特勒集团,早就选定了拉丁美洲这块当时避开人们视线的静土作为退身之地,有组织地和被迫地向那里渗透了相当数量的纳粹分子,以图战败后蛰伏乃至东山再起。这个背景是真实的,近年来相继揭示的漏网纳粹党徒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政府对此不可能不知情,但出于一己之私,态度十分暧昧,这和战后对日本的政策同出一辙。至于书中与德国法西斯势力作斗争的3个美国人,主要出于义愤,即使背后有自己政府的支持,也是为了避免失控。
其余的6部均属当代题材。读者从榜中可以看出,《诊所》、《沉默的证人》和《大黄蜂巢》都以刑事案件为主线,《全面控制》揭露的也是商界内幕。除去《圣诞树》含有宗教博爱的温情之外,《飞机外壳》其实也是以情节取胜的。这部书去年12月22日那周初次登榜,便位居第二;一周后又跃居榜首,持续了3周,至今年2月2日才退至次席。看来这部书深受读者欢迎,一旦我们得到更多的资料,定为大家作进一步的介绍。《诊所》这部侦探小说则是乔纳森·凯勒曼先生的系列作品,主人公亚历克斯·德拉维尔也是位贯穿诸书的侦探,和上期我们所介绍的苏·格拉夫顿系列作品中的女侦探金西·米尔霍恩可以并驾齐驱,竞相辉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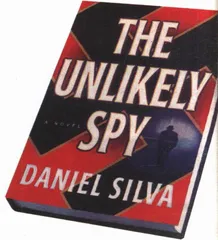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她叫格蕾丝》。格蕾丝全名叫格蕾丝·马科斯,是上个世纪从爱尔兰移民到美洲的一个端庄又不幸的姑娘。40年代时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为人充当厨房助手,干些洗菜刷碗的杂活。在她16岁那年,被指控参与了残杀她的雇主托马斯·金尼尔及其怀孕的情妇和管家南茜·蒙特高莫里的罪行。她到底有罪还是无辜?50年来,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争论的双方自然为女性生来圣洁抑或邪恶这一古老命题夹缠不清。这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也包括历史册籍,谁又能够保证其中未被篡改、处处翔实呢?)中视女性为祸水的偏见是毫无二致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士试图通过受伤害的心理这一透镜,对格蕾丝当年的罪名是否成立加以辨析。
《纽约时报》畅销小说榜前10名(1997.1.5—1997.2.2)

格蕾丝被捕入狱时,曾经承认过自己协同工作中的同伴和心目中的情人詹姆斯·麦克德莫特(这位佣仆的罪名已确定无疑)谋害了男主人和女管家。但在监狱和收容所中度过了15年之后,她推翻原供,声称不记得有此罪行。难题就此产生。
由谁来解开这一疑团呢?作者在这里安插了一位叫西蒙·乔丹的年轻医生,他来自马萨诸塞,受雇于一个专事善举的委员会,那些好心人准备请求加拿大政府赦免这不幸的女子,为她平反昭雪。格蕾丝在这桩双重谋杀案中到底是积极的参与者,还是吓昏了的目击者呢?乔丹医生被科学的好奇心所激励,又掌握着有关精神病的最新理论,便兴致勃勃地去帮助格蕾丝恢复由于震惊和损害而丧失的记忆。
有了这样一个人物,不但对拨开迷雾再恰当不过,而且为展开故事提供了手段。叙述则交替使用格蕾丝的视角和以西蒙·乔丹为焦点的第三者口吻。书中的大部分章节都采取长时间的访谈形式,由医生启发格蕾丝回忆她的生活。她那合乎常情、善于观察,又十分抒情的视点引导我们看到了她贫困的童年、艰苦的越洋航程以及在多伦多的富家中做佣工的平静的插曲,最后才来到那座乡间住宅中安居,托马斯·金尼尔和南茜·蒙特高莫里在那儿过着罪孽的日子,而格蕾丝也就在那地方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全书的情调和节奏从此急转直下。
作家为我们描绘了那座夜间令人毛骨悚然,黑暗中不断传来窃窃私语的住宅的环境——确实是产生嫉恨和罪恶的温床。
至此,作者对格蕾丝的态度已经不言自明。
评家认为,阿特伍德女士在书中成功地制造了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氛围。她为格蕾丝设计的语气和书中叙事的笔调令人信服。实际上她的写作风格一向接近上个世纪的作品,与其说描述人们相互影响的细枝末节,不如说把更多的注意力用于探讨和揭示一种观点,而小说不过是将这种观点戏剧化的手段。或许她笔下的人物还会被人遗忘,但她所选取和阐述的命题却会在人们的心目中掀起波澜。就本书而论,命题之引人瞩目自不待言,作家选取了格蕾丝这样一个有争议的真实历史人物,而且通过丰富的想象力把她写得栩栩如生,确实是畅销的原因。 文学小说格蕾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