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机器
作者:邢海洋(文 / 邢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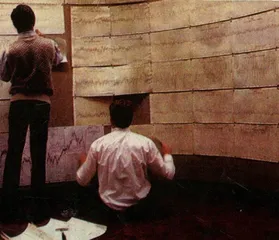
全世界的经济状况都在这里直观显视
4500亿,世界上最大的生意
在波士顿联邦大道的一座建筑物内,麦哲伦基金的48名基金管理人和81名行情分析员正在埋头苦干。麦哲伦是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诚信(Fidelity)投资公司旗下的基金,管理着近600亿美元的金融资产。但在动辄决定上亿美元资金流向的场所,你看不到任何张扬的迹象,确切地说,那里的环境有点压抑。职员们分散在3层办公室内,上下由内部楼梯连接,偶尔,分析员们离开自己的座位,踱到他人办公室门口,伸进头去,悄悄交流消息。
职员们背后,似乎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一切,这是爱德华·C·约翰逊三世。去年,道·琼斯突破6000点大关,连创新高,标准普尔不示弱,资金洪流涌入基金业。而一向雄心勃勃的Fidelity却未尽受其惠,旗下多家基金的表现还不如标准普尔,而且,这样的事还不止于1996年。执掌着4500亿美元金融资产的约翰逊当然不能坐视旁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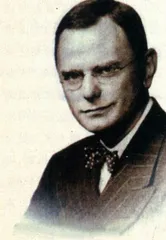
Fidelity管理的资产以10亿美元计
“你不可能永远做得最好。”爱德华是这样解释投资公司的表现的。1946年,爱德华二世创立了诚信投资公司,当时管理的资金只有1300万。50年后,Fidelity成长为4500亿美元的全美第一大基金。据《亚洲华尔街日报》统计,全美共同基金市场约3万亿美元,Fidelity占去15%。基金的高速成长来自于70年代末期,自1979年开始,它神奇地迈上扩张的历程,每年以20—30%的幅度增长。这一时期正与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阴影偶合,同时约翰逊的炒家功力也功不可没。1965年初入行时,他管理的麦哲伦创下过年回报116%的业绩,至今,还无出其右者。
当婴儿潮一代开始在投资领域寻求退休保障,为孩子的教育积累资金时,共同基金的状况就如同1848年加利福尼亚的溪流中发现金矿一样。约翰逊发明了钱生钱的机器,现在,为了保住地盘,他不得不对来自其他淘金者的挑战予以回应。1996年初,21名债券经理辞职;8月,26名经理又被调离岗位,这使得一批证券界崭露头脚的年轻人走上前台;包括人称追踪道·琼斯的猎犬的罗伯特·斯坦斯,接管了麦哲伦。Fidelity能在金融界独占鳌头,凭借的主要是约翰逊家族的稳健传统,对投资股票,他们有一套称之为底部投资的特殊方法。在很少有人注意到时,他们已经大量挖掘公司的背景资料,寻找并持有成长性股票,直到它们开花结果。
拧紧了金钱机器的螺丝后,约翰逊最想做的就是促使基金经理们坚守传统理念。如果他还是麦哲伦的经理的活,他说,他会到联邦大道的办公室里呼吁的。
“这里是钱,现在,展示你的天才吧”
桌子上、椅子上、橱柜里、地板上堆满了报表和投资报告,4台电脑屏幕几乎埋在纸堆里,这是威尔·多纳福的办公室。多纳福是证券明星,管理着Contrafund(相反基金)190亿的资产。从1990年到1995年,他的年回报是22%。而标准普尔的年增长率是14%。正对办公桌的墙上挂着丘吉尔的名言:“为赢得战争,你做了什么?”
多纳福赢得的是一场不小的胜利,在他手里,Contrafund从3个亿成长起来。如此大的资金量在市场上就像一只大笨象,行动不易。如果他要买50万股,他就不得不每天买上5万,直到建立起一个交易部位。“你开的是一辆载货卡车,而别人是跑车,你的时速是45英里,人家是70,这就是不同之处。”多纳福说,“不过跑得快容易出错,我得稳一些。”
这是一场与指数赛跑的游戏。如果你不能战胜,你的投资就毫无意义,因为闭上眼睛随便买的结果正是指数所显示的。战胜指数也绝非易事,过去5年,63%的共同基金不及标准普尔。最伟大的赛跑者应该是彼得·林奇,在他执掌麦哲伦的14年中,年回报率是29.2%,此间标准普尔平均每年涨15.8%。
再造一个彼得·林奇是Fidelity的最大目标,但这也似乎是可遇不可求。布瑞·波斯纳执掌140亿资产,1992年到1994年表现极佳,但1995年却落后标准普尔11个百分点,1996年跟市场打个平手。他自称是个学究,可交易上,还是认为灵感多来源于与炒手们的交流。对新入行的,他给出的忠告也是别过多地依赖技术。与其他经理一样,波斯纳每天清早就把交易指令传给经纪人,随后整天都很少再下单,80%的时间打电话、开会或看财务报表。报表很重要,里面能看出很多蛛丝马迹。
基金管理人共享信息,但却独自操作基金。Fidelity从不提倡其他机构里流行的委员们决策,它更倾向于给年轻人以独立,典型的Fidelity做法是,“这里是一笔钱,做个天才吧。”一般地,商学院的毕业生们要从分析员做起,同时还要管理一笔1亿左右的“小”资金。几年以后,分析员成长为经理人,手中的资金量便逐级加码,涨到几十亿。
Fidelity的成功得益于刻苦工作的企业文化。在这里,深夜两点还能接到上司的电话是常事,一位前部门经理说:“的确紧张到了极限,要么你付出120%的代价,要么他们削掉你的脑袋,脖子上就跟放了个刀片一样。”
员工们还像以前一样工作,但Fidelity 却遇上了麻烦。1993年,84%的下属基金战胜了指数;1994年变成51%,到前年就降到21%;去年,只有29%的经理做到这一点。对此,Fidelity研发部门的资源副总裁范德海登的解释是,过去,因为偏爱大比例投资,几乎所有基金在上涨中都表现出色,但下跌时却表现不佳,但从长远看,市场总是在上升的,所以Fidelity的总成绩仍将走在市场前面。
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如果Fidelity能在牛市上取利,为什么1995年它却如此之惨,1995年是本世纪最好的年景之一。去年4月份的报告显示,过去20年,以3年为单位的统计中,麦哲伦第二次败给标准普尔。报告未披露前,管理人杰弗里·凡尼克即递上辞呈。凡尼克是Fidelity的一个典型,显示出公司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它被自己令人失望的表现弄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它要面对人们的指责,太没有预见性了。自以为股票炒得过高了,凡尼克把大量资金买了公债,结果股票一个劲地涨,麦哲伦却大为落后。抛开收益率不算,人们不禁要问的是,麦哲伦是一个以投资股票为主的基金,凡尼克凭什么把公债作为投资主体。诸如此类的事情不止一件,资产基金是为分散风险建立的,却有l8%的股票陷在1993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里。
收益尚可时管理人的越轨行为被忽略,可现在它成了众矢之的。一篇名为《Fidelity透视》的文章写道:“形势大好时,谁注意到相反基金没运用相反理论,资本增值基金没在行使资本增值的方略。”
Fidelity开始加大监管力度,基金必须与其主旨吻合。那些对中小企业敏感的管理人被派去经营小股票基金,被套在墨西哥的管理者早被调离。公司的监管力度一再加大,过去它设有4个监督机构,现在4个将分成8个。
没有人认为变革意味着公司变得更保守,更专制。Fidelity执行副总裁罗杰·斯维森的解释是,这只是拧紧发条,而非重组,公司所做的是加强风险控制,促进各部分的合作,避免重复。过去,人们更崇尚在底部买入,在顶部抛出,现在的要求只是比底高一点,比顶低一些,这样虽然利润少了,但失误也同样减少。
的确,买底卖顶是所有投资者的追求,但有谁能永远测准低位和高位呢?祈求买到地板价卖到天价的人往往因自信而失去机会,接着便是一错再错满盘皆输。“人们的期望值未免太高,15%甚至10%都是不现实的,他们应该把目标订在10%以内,”范德海登道。
做老大,不容易
Fidelity的图表室里挂着约1800幅金融和经济指数的图表。每个月,它的Interner节点都要接受560万次访问。在建立庞大金融帝国的同时,约翰逊也建立了庞大的技术体系。5个通讯中心遍布美国,出市代表拥有最先进的网络终端,达拉斯的计算中心处理着包括Fidelity交易在内的各式各样的数据,其先进程度任何其他公司都无法企及。一位雇员不禁赞叹:“我觉得仿佛置身北美防卫体系之中。”
约翰逊不嗜浮华。Fidelity没有办公飞机,也没有房车,总部所在地波士顿的摩天大楼中没一幢是属于Fidelity。与公司在金融界的地位相对照的是,约翰逊的性格更像一位东方隐士,热衷佛学,他曾赞助美国的寺庙。
401(K)是投资储蓄计划的代称,约翰逊对它情有独钟,很早就作出了为之加强计算机软硬件能力的决定,现在,它已成长为Fidelity 的一大支拄,总资金额1114亿,而在1993年,它还仅有375亿。401(K)的盈利每个月自动转到本金里,它就像一个自我补充原料的机器,促进Fidelity的成长。
401(K)或能代表公司近来的经营特点,它变得越来越大的同时也就越来越难以行动,但庞大的资金量也提供着信誉,使那些渴望退休后买假日别墅的中产阶级们敢于把钱投入它的名下。没有人怀疑占有401(K)近18%市场份额和技术优势的Fidelity将在理财业继续执掌牛耳。但是,强劲的挑战、对基金管理人的限制以及它庞大的身躯都会成为负担,人们甚至敢于预言,彼得·林奇的光荣历史难再重演。
“说千道万都是白搭,”一名前雇员说道,“市场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如果Fidelity 不能再回到前10%中去,一切都将受阻,拥有基金的人们等着用Fidelity挣来的钱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买度假别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