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脑一双慧眼吧
作者:胡泳·数字化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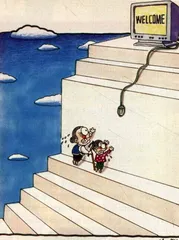
我敢打赌,没有几个人会打电话和录节目
你会用电话吗?
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天天抢着电话打的人们来说,它并不多余。据说北京现在每4个家庭中就有一户拥有电话,但我敢打赌,没有几个人会打电话。
你懂得电活号码存储、重拨功能、电话等候、电话转接、电话号码过滤吗?你听说过遇忙记存呼叫、缩位拨号、三方通话、语音信箱吗?我说你不会打电话,大概没有冤枉你,因为你多半只明白通话功能,对电话功能的开发能达到1/10就算不错了。
不瞒你说,我和你差不多,虽然我的工作离不开电话,但除了0一9十个数字键外,其他的东西我一概茫然。
我还有一块心病。录像机买了好几年了,但除了偶尔弄点录像带放放外,从来搞不清楚怎样用它录电视节目。虽说有一本厚厚的说明书,但读起来跟天书似的。从说明书目录上看,录像机功能一大堆,但遥控器上20%的按钮能干啥,我至今不甚了了。
记得《北京青年报》曾在头版发过一篇报道《身边的高科技“闲置”惊人》,其中说,科技含量越高的产品、越新的产品,功能闲置就越厉害。在发现这个事实后,记者问,这是因为科技发展太快呢?还是科学普及太慢?
文章还说,不少人都提出对于这些高科技产品的功能愿意学习,只是不知从何学起。这一点我可和他们不一样。我不但不想要所有这些花哨的功能,我甚至根本不想拨电话和录节目。《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说,产品功能的“闲置”足以令设计家们难堪。我想这些设计家的确不够聪明,为什么他们全都不明白,没有人爱拨电话,我们只想利用电话来和别人取得联系!没有人爱录节目,我们只想利用录像机方便地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
怪不得个人电脑在世界上喧嚷了17年,仍旧不如电话和录像机普遍
虽然我的见识比设计家们略高一筹,但电话、录像机对我很有用,我必须拥有它们。出于同样的考虑,我购买了一部电脑,尽管我对使用说明书的“科学笔法”深恶痛绝,而电脑的使用说明书似乎比以前我买的任何一种家用电器的说明书都更厚。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与电脑相比,操作电话和录像机简直容易极了。这家伙欺生欺得厉害,就像录像机上不停闪烁的“12:00”一样,它不停地传达一个信息:你犯了错误。可怕的事情在于,我老是不明白自己在哪里犯了错误。而我一旦犯了错误,不论是乞求还是威胁,电脑都置若罔闻。这使得我每次离开电脑时,都感觉自己智商很低。
只是到了我对电脑了解得更多以后,我才明白那是整个电脑业的错,而不是我的错。
只有电脑业,才会制造一种令人困惑和沮丧的产品,将它们卖给真心实意想要使用的顾客,并对此习以为常;只有电脑业,在大肆吹嘘自己的东西如何使用户感到亲切友好之后,再发给他们长达几百页的使用说明书;只有电脑业,把“现实世界中的解决方案”的标签,贴在一种只能在迷宫般的操作环境下运行的设备上,这一环境迷宫与我们所知的物理世界并无任何相似之处。
为什么我为使用电脑感到厌恶和恐惧?因为使用一台电脑意味着我必须掌握一种用户界面,而这种界面与我在真实生活中的体验毫无关系。以大家耳熟能详的“视窗”操作系统为例:那些未曾看见过微软公司这一王牌产品的人对它是什么东西没有任何概念。看见过“视窗”的人则会发现,电脑屏幕被切割成一块块的,一些奇怪的小图像排列在一起,内行人说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应用程序”。
问题来了。要想用电脑做事,首先得明白什么叫“应用程序”。说白了,它的意思就是指你想干什么,比如说,你想和另一台电脑交流,你就得启动一个交流程序。接下来你还得搞清楚“文档”的概念——你想和别人交流什么信息。你很快发现你的行动和目的之间出现了分裂,仿佛在一个句子中,有人非要把主语、谓语同宾语分开。我们在现实中同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不是这样的。如果真实世界照电脑的方式运行,那么,一个行人想要避开一辆迎面驶来的公共汽车的过程就会是这样的:
首先,看到车过来,决定采取某种行动,而不是像一头被灯光照晕了的鹿一样呆立不动;其次,从一系列菜单中选择一项,这些菜单项可能也包括“大哭”、“大叫”、“祈祷”以及“快跑”;再次,选择“快跑”后还要思考怎样执行这一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笨蛋,那就是挪动双脚,以便赶快跳出车道!
怪不得个人电脑在世界上喧嚷了17年,仍旧不如电话和录像机普遍。
改变界面,让老祖母也能轻松自如地玩电脑
电话的历史很长,不过录像机问世的时间与电脑差不多。同时出现的电器还有微波炉,今天,就普及率而言,录像机和微波炉远远高于电脑。
电脑业人士会认为我把电脑与录像机、微波炉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后两种东西属于家庭娱乐和实用产品,而电脑则刚刚走进消费市场。他们说,电脑在其发展进程中正在达到一个高峰,它将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随处可见。这些人对此津津乐道,认为电脑业已具备了足够的规模,如用汽车业的发展来印证,可以说到了生产福特T型车的阶段。这款车是世界上第一种大批量生产的轿车,其重要性在于,毋需配备专业机械师,普通人也能把车开好。对于这样的类比,我十分欣赏微软欧洲部总裁伯纳德·沃格尼思说的一句话。他说,只有当他的祖母也能操作电脑时,上述说法才形象而贴切。
要想让祖母也能轻松自如地玩电脑,就必须为电脑设计更加人性化的界面。界面通常被看作物理设计问题,所以设计家们才会把多得离谱的功能塞进一部电话中,让我们简直没办法使用。录像机和遥控器的使用也被看成按钮问题,结果是,大部分按钮人们连碰都不碰。
界面不仅和机器的外表或给人的感觉有关,它还关系到个性的创造、智能化的设计,以及如何使机器能够识别人类的表达方式。电话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设计出可以塞进口袋里的机械秘书,而录像机则应该成为我们的电视节目代理人。
好的电脑界面应该有更佳的表现。界面应该设计得像人一样,而不是像仪表板一样。未来学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说,电脑业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将远远不止是为人们提供更大的屏幕、更好的音质和更易使用的图形输入装置。这一挑战将是,让电脑认识你、懂得你的需求、了解你的言词、表情和肢体语言。将来的电脑将能够观察、倾听,不像一台机器,而更像一位善解人意的仆人。
我们一直执著于让机器达到“容易操作”的境界,有时候却忘记了许多人压根就不想操作机器。他们只想让机器帮他们做事。所谓的“人类工程学”或“工效学”一直致力于使笨机器更容易为聪明人所用,为什么不是反过来,让笨人也能使用聪明机器呢?敲键盘、点鼠标这些非自然生活中的动作,为什么一定非得视作计算机的常规操作?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打字决不是一种理想的界面。假如我们能和电脑说话,最不可救药的电脑盲,大约也会以更大的热情来使用电脑。说话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遥控,如果语音识别技术足够棒,电话机的操作将无需数字键盘,它将可以对口述的词语和数字作出反应。银行自动出纳机也不再需要敲人数字,只要听到命令,它就能够像变戏法一样支付钞票。
使用语言还给予我们很大的自由度来进行我们本可以同时在做的工作——不像传统的键盘完全束缚了我们的手和眼睛。今天的电脑需要人全神贯注。你通常都必须正襟危坐,同时把注意力放在互动的过程和内容上。而使用语言,则使我们能够在继续其他活动诸如沏茶、开车之类事情的同时和电脑交流。
更远一些,我们也许能用以视觉为基础的界面进行交流,届时计算机将对面部表情和手势姿态作出相应的反应。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技术挑战。尽管如此,随着科学的进步,这一点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简单地说,界面将需要不同的尺寸、形状、颜色和语调,以及其他五花八门能够感应的东西。只有这样的界面才是老祖母能够适应的。
现在是该让电脑看得见、也听得见的时候了
尼葛洛庞帝认为,个人电脑对个人存在的感觉非常迟钝,还不如装了传感器的现代盥洗室。便宜的自动对焦相机要比任何终端或计算系统都更清楚面前的景象,因而拥有比电脑更高的智能。
我们今天的着眼点完全放在如何使电脑更容易为人所用上。也许现在是问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怎样才能使电脑更容易与人相处?
现在是该让电脑看得见、也听得见的时候了。使电脑变得更像人,这种想法很容易招致批评,人们会嫌它太浪漫或太不切合实际了。但我想废除一切使用说明书,这一点有谁反对吗?想想看,多少机器徒有大量的功能说明,你却从来不愿费心劳力把它弄懂,因为那实在太难了。要学习如何使用机器,最好的老师其实就是机器本身。
前提是机器了解你,它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刚刚做了什么,甚至能猜测你将要做什么。由于大家各有不同的信息偏好、娱乐习惯和社会行为,你的界面会有别于我的界面。电脑会逐渐具有人格。
电脑常常惹我生气,但偶尔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我在撰写上一篇专栏文章时,使用新全拼想打入“全球电子村”一词,但屏幕上出现的却是“全球倒栽葱”。这使我笑了好一阵。
目前的电脑的确使全球都发生了“倒栽葱”。大的电脑公司感到,如果他们设计出的一种型号能在市场上坚持18个月,他们就算格外运气了。不走运的型号往往几个月之后就销声匿迹。大部分型号的情形介于这两者之间。而根据莫尔定律,微处理器的能力每18个月就提高一倍。软件是用来开发这种能力的东西,它将其转化为各种应用程序,正是这些应用程序使我们急着抛弃旧电脑而忙于购进拥有更快速度的新电脑。在枪口的威逼下,别指望软件开发人员会成为精雕细琢的工匠。
过去16年中技术变迁的步伐是如此之快,考虑到这个事实,电脑能像现在这样工作良好,实属奇迹。
如果你想同电脑打交道,最好相信奇迹。有关机器仆人和自动驾驶的汽车的传说一直是本世纪人们幻想中的重要部分,也许这一次终将成真——电脑智能正飞速发展。到了那一天,你可能会对着桌上一群20厘米高的全息式助理说话。
我得承认,这一景象有点怪异。但我将高兴地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因为那样,我就可以不读使用说明书。而且我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智商最高的人。 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