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户操盘警示录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方向明 皮昊 邢海洋 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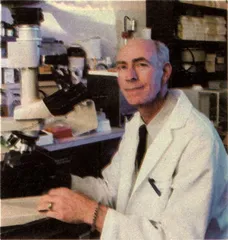
50万元以上的投资者可成为大户,券商给他们的”待遇”较好(马彦 摄)
卖空“黑箱”
商界有句黑话:“空手套白狼”。此话在股市上的行话叫“卖空”。假如你手中没有股票,你能在股市上大量抛出大发横财吗?也许你不可思议,但有人就这么做了。
24岁的廖强在股市上打了几个滚后,已成为四川乐山市小有名气的大户。1996年8月初的一天,他来到某证券公司乐山营业部,察看了一遍行情,老道的判断出有几支股票可能是先涨后跌,顿生炒作之心。可令他搓火的是,自己的账户上已没有这几支股票可卖。
坐失一轮行情,廖强实在难受。但他有自己的招数,仗着和这个营业部的人员很熟,他先后3次填写卖出委托单,连同证券帐户本、资金账户本一起交给工作人员,委托营业部卖出“川金鹿”3万股,“川长钢”4万股、“川天歌”3万股。当日上午成交,成交金额40余万。
当天下午,这几支股果然下跌,廖强为使其证券账户额平衡,委托营业部买入上述同等数量的股票,共计资金30余万。廖强空手高价卖出,又用低价买入,一天赚取差额4万余元。营业部心照不宣地收取了股票交易手续费4000多元。此笔交易在“黑箱”操作中完成。
可惜好梦不长,第二天营业部通知廖强,他有卖空行为,应当接收处罚。随后,将廖强的证券账户本,资会账户本交还给他,并将昨天的成交记录删去。此后,营业部以廖强卖空股票为由,没收其收入的4万余元,归营业部所有。事隔半月,营业部又以廖强透支为由,从其资金账户存款中扣划1.2万元作为罚款。
由于廖强与营业部发生争执,双方都托人进行私下抹合。由此,这笔“黑箱”操作的交易不胫而走,在股市上悄然传开。
比起廖强的卖空“黑箱”,一些券商手中的“箱子”可就大多了。
和廖强同籍的一位股民在账户上常看到自己不知道的成交记录。有时放在账户上的股票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卖成了钱,或者资金账上的钱被人买进了股票。这位股民想来想去,终究没闹明白自己的钱是和券商搁在一块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成交记录是券商干的,利润当然券商留下。
中国股民一件颇恼火的事,就是券商常拿他们的资金和股票去做自营。一些营业部工作人员,看到价格很高时,擅自把客户的股票卖出,等到价格降下来再卖进一些,补回空缺。股民毫不觉察,券商却赚了笔差价。股民把这种卖空行径称为“空麻袋背米”,“麻袋”里装走的全是股民的利益。
持股操市
1996年5月9日,郑州百文公司的领导人大吃一惊,该公司的股票被北京金昌投资咨询公司收购了712万多股,占到郑州百文股份总额的6.88%。
郑州百文于4月18日才上市,仅15个交易日,就被另一家公司大宗持股,创下了沪市的一项新纪录。据了解,郑州百文的总股本达10,348万股。其中国家股占15%,金昌公司执股6.88%后,已成为仅次于国家的第二大股东。
按照国家有关证券法规,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达5%时,应立即向该公司做出书而报告。但金昌公司称,他们是在5月9日上午拿到交割单后,才发现持有“郑州百文”的股份达到该公司总股本的6.88%,因此未能在执股达5%时,立即公告。
此后,金昌公司又作出进一步解释:因为误记了“郑州百文”的总股数,所以百分比算错了。
事隔一天,在“郑州百文”的股份上又爆出一个惊人新闻。一位叫袁敬民的个人投资者持有了“郑州百文”的流通股768万股,占“郑州百文”总股本的7.43%,超过金昌公司成为“郑州百文”股票的第二大执有者。按照国家有关证券法规,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家上市公司5‰以上的股票。而袁敬民所持的百文股份远远超过了这个标准。
郑州百文公司领导层顿感事态严重,立刻向中国证监会做出书面报告提出停牌申请。据悉,在郑州百文1亿多总股本中,可流通股仅占49.7%,而金昌公司和袁敬民总共就占有了14.3%,完全可以控制该股票的市场行情。据了解,金昌公司收购郑州百文6.88%的股份,按照当时市价至少需投入1个多亿的资金。而金昌公司只是一个投资咨询公司,这不得不使人怀疑这笔资金的来源。袁敬民又是一个个人投资者,他又从何处弄到这笔巨款?
事态仍在进一步发展,有关调查人员发现,袁敬民与金昌公司均为北京同一家证券营业部的客户,而袁敬民与金昌公司的总经理又同姓袁。这两个巧合使人必然产生一种设想,袁敬民与金昌公司有着某种暧昧的关系。
不料,事情更加复杂化。袁敬民的收购之举原为一个叫李石的个人投资者所为。李石称,不知道有关法律规定的个人持股比例,同时也否认同金昌公司有任何业务上的联系。但是,经调查发现,李石和金昌公司都具有相同的资金背景,资本金全由一家名为“建昊公司”来拔付。此外,建昊公司还为李石的股票交易融资提供过信用担保。事实是,金昌公司和李石的证券交易资金大部由建昊公司提供。
李石和金昌公司同时吃进一家上市公司的大批股票,而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竟丝毫没有事先警觉。这就提出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为何证券交易所没有设置预警系统?据专家介绍,设置这样一个预警系统在技术上并不是多么复杂,但就没有设置。正因如此,袁敬民和金昌公司在没有任何监控下,做出了他们想做的事情。
作为个人投资者李石执有700余万股“郑州百文”股票,由此带来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按规定,郑州百文公司应收回袁敬民的超额持有的股票。但是要收回这批股票至少需要5000多万元。如果动用该公司的流动资金,就等于占用该公司可动用资金的1/3,无疑会影响郑州百文的日常运作,而郑州百文将这笔股份收回之后,按珲说应重新通过公开竞价在股市上进行转让。但这势必造成二级市场的波动。
机构大户在国家法规的空隙下使用各种名义进行操作,这在目前的股市上已是普通现象。
事实上,股市中机构大户频频坐庄,恶炒个股,其他中小股民只有跟风的份儿,这是股市上某些个股暴涨暴跌的根结。操纵在个别庄家手中的股票,看的是庄家的“心情”,而不是市场的“行情”。
近期新股上网发行证券经营机构申购透支表

公款炒股
1996年12月13日,全国迄今为止数额最大的挪用公款炒股案被揭露。
李伟民原在工商银行嘉兴市分行工作,工商行投资组建嘉兴市信托投资公司后,他被调任证券营业部经理。走马上任不久,李伟民感到在营业部只做“过路财神”不过瘾,不如下股市捞一把。他找到过去的同事,此时还留在工商行的沈加曾,两人商量由李伟民将信托投资公司自营股票的资金打到沈加曾的股票账户上,先用这笔公款为自己炒股,待盈利后再把钱悄悄还上。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就能做成一笔“无本生意”。
在最初的几次冒险中,李、沈二人的“战斗友谊”不断加深。不久,李伟民就把沈加曾作为业务“尖子”调到自己身边做副手。
由于证券从业人员不得炒股,沈加曾进入证券营业部后,他原来的账户就不能再用了。李、沈二人又找到这时还没进证券部的寿学军,3人商定盈利后以5:3:2的比例分成,李伟民就把寿学军的股票账户拿来,分3次透支挪进公款33万元。
为了炒作方便,李伟民动用手中的权力,把和自己拴在在一根线上的寿学军也拉进营业部,安插到大户室做报价员。因为继续使用寿学军的账户风险太大,他们就借来沈加曾姐夫的账户继续透支,挪用公款502万元。
李加曾深谙股市法规,用沈加曾姐夫的账号来炒股,他心里总感到有点悬。毕竟,沈加曾和其姐夫这种紧密的亲戚关系终会给人察觉。他们3人决定去物色一个和自己非亲非故的人来做“出头鸟”。
嘉兴市总工会干部王建荣一直使用以妻子的名义开立的股票账户炒股。他和李建民3人属天那种在柜台上熟识的“股友”。几番讨价还价,王建荣经不住李建民以盈利后分成10%相诱,拱手将自己的账户让出。李建民拿来后,在上面透支挪用了公款50多次,累计1946万元。
这时的李伟民等人已经完全利令智昏了,每天买卖股票数万股,挪用公款几十万。为了隐蔽,李建民把这个营业部,上到经理、副经理,下到报价员、电脑管理员全串通成一团,外人根本无法发现。
挪用公款炒股在股市上并不鲜见,为此走进牢房,走进刑场的人每年部有。但为何仍有人“前仆后继”呢?一言蔽之,钱不是自己的,利是自己的。
对国家而言,挪用公款炒股导致国有财产巨额流失,而对股市而言,这笔不义之财也并不受欢迎。社科院一经济学者指出,存一个存在许多“玩公家钱”、“赔了”也总可以找到钱来“堵窟窿”的投机者的市场上,风险自然比都用自己钱、赔了要近期新股上网发行证券经营机构申购透支表倒闭的情况下更大些。
第一,公家资金往往巨大,对股市波动影响也大,第二,投机性更强,更容易缺乏理智地对待市场波动。他们利用公款炒股就不准备做长线投资,只希望赚取利润就撤走,一遇股价上升就追涨,一遇下跌就抛盘。所以,他们的短期炒作更给中小股民带来极大损害。这种资金的流入对股市发展绝无好处,只会使潜伏风险的股市更易动荡。
消息惑众
1996年七八月份,股市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口,因前几个月的炒作,股价暴涨使人感到风险临头,股民急欲在上市公司的中期报告中,对其业绩进行考察以调整投资方向。正因如此,一些上市公司开始在自己的业绩上“做秀”。
山东渤海集团用严重不实的中期报告来欺骗股民。集团误导投资方向,做得明目张胆。而另有些上市公司常会用居心叵测的公告来愚弄股民,让人有苦难说。张骏是南方的一名普通股民。1996年7月,他看到一家集团董事会发布的1995年度分红公告,觉得其中个人股10送3的配送红股方案很诱人,而且公告还确定股权登记日在7月26日,3天后是除权日,到了7月29日配送的红股就能上市交易了。
张骏当时心想,自己只要赶在股权登记日之前买进这只股票,就能到手不少红股,过几天把它们一古脑卖出去,自己又能小赚一笔。于是,7月24日,这天他以11.83元的成交价买进了一批股票。
7月25日,这家集团董事会又发布一条公告。张骏看见原定7月26日的股权登记日没变,只是除权日待8月份临时股东大会决定。他便在3天后将手中的这只股票以10.75元卖出去,虽然眼下赔了些钱,但好在可以到手一批配送的红股,等红股到账抛出去仍可赚一笔。
谁知左等右等,直到9月13日这家集团又发了一个分红公告,将股权登记日改为9月18日,红股上市交易日为9月19日。
张骏顿时傻了眼。自己当初就冲着北亚7月26日股权登记日后能送红股,才敢在24日买进28日抛出。现在登记时间一改,倒落得高价进低价出,想分红股还没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股市里风险浮沉,公司业绩对股民来说不亚于指明方向的罗盘。连企业利润都可以做手脚,股民的投资行为又哪有理性判断依据?
银行透支
1996年11月21日,星期四。深圳某证券公司上海营业部的大厅里,人声鼎沸,秩序大乱,营业部勿忙间只好请来了警察。面对此情此景,证券公司经理有苦难言。
今天新股要上市,一些股民准备申购,可前几天,该证券公司刚向交易所透支了一笔钱,若今天再透支去申购新股很可能被曝光。公司只好向股民表示暂时不要申购新股,等当天二级市场资金退出来后再申购。公司的做法让股民十分愤慨,纷纷要求提款,到别处申购新股。
1996年的股市违规案中,金融机构向证券经营单位违规透支占了相当大比重,新股申购发行阶段发生的违规透支事件尤其集中。
新股发行价与上市价间差价少则一倍,多则数倍。因此对券商们来说,在申购新股阶段就拔得头筹,其获利之丰,风险之小,自然与日后市场上的搏杀不可同日而语。按现行的发行方式,申购新股每个股票账户不能超过一千股。此时,券商得要做出两手准备,一方面尽可能多的搜罗身份证,动则上万、几十万个身份证申购新股;另一面又得纠集足够的资金,填进众多账户里。对于一个大券商来说,申购新股将是一次庞大的资金行动,于是券商往往会向存放资金的银行打招呼,当申购资金不够时,把已打入股票帐户的钱提出来又使一遍,这叫“二次申购”;实际上就是向银行透支去买新股。
证券经营机构透支申购新股,表面上看只是券商明火执仗地抢夺中小散户买新股的机会,而实际上它是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的一个主要渠道。
对一家证券经营机构来说,它在市场交易中应该只使用自己资金。可一旦它向金融机构进行透支,透支部分的信贷资金就会很快流入到股市,破坏股市的资金结构。
试想,要想操纵一只股票非大笔资金不可,而某些银行若成为机构大户的资金库将多么可怕。如果多家机构大户同时拿银行资金炒作,那么恶果只有一个:大市暴涨与暴跌。

李伟民等5名被告人出庭受审。左起:李伟民、沈加曾、寿学军、王建荣、叶利根(岳耀勇 摄) 新股申购股票证券操盘股民散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