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后,人也死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怀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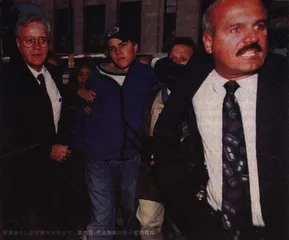
彼得森自认在犯罪时未有任何心理痛苦,但在被捕时终于感到害怕
从另一桩命案说起
这一桩也发生在最近,大概该属情杀案,想必读者们都已从报刊上了解到了。情杀的事中外古今一直都有,在文学中也是个很重要的主题,但是这一宗平淡得有点不一般,离奇得又有些怪诞。一对青梅竹马的年轻恋人,发誓海枯石烂,但男的不期走轨,又与一萍水相逢的少女有了一夜之欢。事后男的追悔莫及,女的更是痛心疾首如见玉碎。最后这对恋人认定只有一条补救办法,就是杀了那其实并不知情因而实属无辜的“第三者”,这样就可以且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两人继续过他们的好日子。他们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一切顺顺当当,居然没有经历什么良心拷问或内心冲突,以致日后女的一不留神,说话的时候把这事向别人透露了,这桩命案才算大白。
笔者关心的是人命这么一件本该“关天”的事,如何开始变得无关痛痒起来,以致会让人想到拿它来“补救”别的事。从这个思路上想就觉得陌生,拿它和一两个了解文学的人对证,也都说“缺少原型”,因而不可思议。其中一个被问到的时候不客气地说:“这事儿在小说里会显得太假,放在电视剧里还可以”,大概以为笔者在生编滥造。当笔者告知确有其事的时候,他问了一个很“到位”的问题:“上下文(context)是什么?”
上下文
不知讲出这个案子的“上下文”,是否事情就变得好理解些:此事最近就发生在美国,当事的这对恋人均是十八九岁健康活泼的大学生,生活一路平平坦坦,和周围的人没什么两样,大致就是这些。
无独有偶,美国最近又出了个案子,案情不同,但出在一个相似的“上下文”里,愈发觉得其间别有意味,故不妨先在这里仔细把它交代清楚。
1996年11月12日深夜,美国德拉维尔大学的一年级学生艾米·葛洛斯堡开始感到剧烈的阵痛。子夜0:45,她的羊水破了,于是打电话给在另一所大学念书的同龄男友布瑞安·彼得森。2个多小时后,彼得森驾驶着他的黑色丰田牌小轿车赶到了葛洛斯堡的宿舍。他和她随即驱车直奔一家旅馆。凌晨3:10,他们在旅馆包下了房间,葛洛斯堡顺利分娩一健康男婴,体重2.75公斤,身长51厘米。5:00左右,他们付账离去。新生的婴儿并没有随行,他被用一只灰色塑料袋包着,丢在了旅馆的垃圾箱里。
他们驱车回到葛洛斯堡的学校宿舍时,天还没有大亮,两人相拥补了一个短觉,然后彼得森赶回自己学校上课,新的一天开始了,他们重又回到了过去那个安宁、舒适、无忧无虑的生活中。
当日下午,葛洛斯堡因产后体虚昏倒,在被送到医院后遂向医生讲述了原委。
后据警方公布的尸体解剖结果,婴儿系脑部受多处重创导致头盖骨破裂而死,也就是说,葛洛斯堡和彼得森不仅是弃婴,而且是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目前二人已被起诉。
其实弃婴或溺婴也和情杀这类事一样,中外古今时有发生,虽然难以接受,但一般总是可以理解,因为事情背后总该有些或悲或惨的理由。但这个案子有些不同,放在它自己的“上下文”里,不光莎士比亚处理不了,恐怕专事哗众取宠的畅销书作家也会嫌这事太离谱。
这两个18岁的年轻人均出生于新泽西州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上大学时都是开着属于自己的小汽车进的校门(葛洛斯堡的车是一辆白色切诺基)。和他们的生活水准一样,他俩的学业成绩也相当令人羡慕。她是个天赋甚高的准艺术家,他则是校高尔夫球队的队长、足球队的副队长。在同学和邻人中,两人的口碑极佳,被称为“天生一对”。葛洛斯堡虽是身怀六甲进的校门,可在那么一个开明宽松、尊重他人隐私的社会中,谁会在意这些呢?这个“上下文”简单一句话就是:“他们是有着多种生活选择的两个富裕的好孩子”——一个熟悉葛洛斯堡的人这样对《新闻周刊》的记者说。
这就难免了解他们的人一致表示:“谁也不知该作何感想”(No one knowswhat to think)。
什么都有了,独独没有了人
葛洛斯堡和彼得森这件命案的取证工作已基本就绪,一个案子早晚又要了结。但看似滑稽的是,我们对事情原委了解得越详细,悬而不决的问题就越多:他们何必如此呢?
我们不是单为弃婴溺婴这种事本身而愤世嫉俗——历史上甚至有“易子而食”的事,但好歹还可以拿饥荒来说事儿;弃婴溺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绝迹(美国1994一年中共有207起),但我们总相信那和社会开化的程度、社会的福利水平、生活选择维度的多少是呈反比的。这也正是这个案子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生了孩子他们仍可以选择结婚或未婚;他们可以选择养孩子、也可以选择放弃扶养义务,放弃的话还可以选择婴儿收养机构或医院(这些机构均给当事人保密);实在懒得选择的话他们还可以就这么一走了之,何必非动手杀了自己的亲骨肉不可呢?是什么使这两个有钱、有名誉、无论怎样选择都注定会有稳定生活前景的恋人认定,打碎自己的新生儿的头颅是最佳选择呢?
《时代》周刊载文分析说:“看来让孩子们拥有了一切、一切都可以随心所欲的阴暗面就是,他们无法容忍自己生活中出现一丁点儿不顺心的事。”
这个案子几乎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心理分析的余地。据彼得森的律师说,他对他所做的事未表示任何心理痛苦,只是被收审时才感到“害怕”。缺乏对人命关天的事情的本能的心理反应(且不谈道德自律的问题)大概是这两个案子的当事者的共同之处,而案中当事人的生活经历都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当代大众生活,普通到几乎可以随便是什么人的样子,这让人不由担心它们是否正在为人类未来的生活设置一种“原型”,担心以后会有些事果真似曾相识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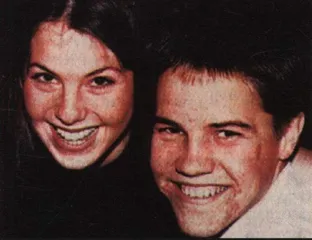
他们太习惯了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警察在这只垃圾箱里找到了弃婴的尸体
太多的担心可能于事无补,但许多事已让我们开始看到,埃利希·弗洛姆关于工业化过程中人性发展状况的分析正在得到验证。他曾经怀疑“人类将走向何方”,因为他预见,“在我们的体系中成功地解决了某些经济问题的那些要素,在解决关于人的问题时是日趋失败的”。弗洛姆的担忧是基于他对社会的期望,即让一个人是什么而不单是人拥有什么或利用什么的社会。
19世纪末,尼采在工业化社会的前夜看到了上帝的死亡.他为此欢欣鼓舞,因为他相信人类正在从神的控制中挣脱,而成为超人。掌握了技术的人类也果然相信了自我意志的无往而不胜。但弗洛姆却担心最终的结果是否是人在死去。在他看来,人类在工业体系中“正面临着失去他活生生的人的本性的危险,”因为庞大的工业体系正在把人培养成“组织化的人”,如同庞大的电子计算机把生活程序编排就序,个体从而成了无甚特征的其中一员,一种物,越来越成为“某某”而不是“我”。
弗洛姆传递的信息绝不似酒神般激越感奋,但对威胁到人类存在前景的任何一种可能性的分析都无疑是值得我们小心审视的,至少这是想到对策的前提。在这里,在讲完了两个案子之后,引用弗洛姆的这样一段话,大概不致显得太思辨、太突兀、太难以接受:“……(工业)社会创造了一定条件,它导致了人的攻击性的增长。我这里主要是指情感和理智的逐步分离。在我看来,我们正缓慢地、逐步地发展一种温和却又是执拗的精神分裂症,这种结果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性,而且也带来了人们对生命的冷漠。而且,这种冷漠很可能是人们准备消灭别人和自身的更危险的原因所在”(《人的呼唤》)。 弗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