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访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张钰 王宁 陈迈平)
英格玛·格伦德(诺贝尔化学奖评委会主席)
特邀 [瑞典]张钰
诺贝尔化学奖评委英格玛·格伦德(Ingmar Grenthe):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皇家理工学院副院长。15年前,笔者申请到皇家理工学院的化工工艺教研室进修,接到的却是无机化学教研室主任格伦德教授的邀请信,于是也就“将错就错”地由工科转理科,成为格伦德教授的学生。
笔者:嘿,英格玛,你们这次选了“碳六十”小组。在《新科学家》的这张表上,他们才排名第四,你们该不是故作惊人吧?
IG:当然不是!何况我还是强烈的反对。
笔者:那么,谁是你最支持的人选呢?
IG:很抱歉!我不能告诉你。
笔者:这还需要保密吗?既然得奖人名单都已经公布了,那么公开你支持的落选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IG:当然有关系!我甚至都不能告诉我妻子,否则就违反规定了。
笔者:不过,我想我可以猜出来,一定是这个表上排名第一的泽瓦依尔教授,你曾经对他有很高评价。
IG:不要试图来套我,无论你猜谁,我都不置可否。
笔者:此外,我的很多同胞都想知道,中国人是否有希望获得化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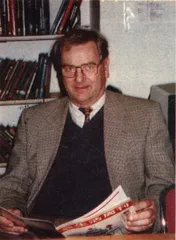
IG:我想这里有个误会。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国籍不应该成为一个条件,因此我们从不在意候选人的国籍,只比较他们的成绩。
笔者:我知道是这样。这个问题可以换个角度,是否有中国化学家的成绩已经达到或接近竞争诺贝尔奖的水平呢?
IG: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应该可以通过别的渠道得出自己的结论。
笔者:如果根据那张排名表,中国人显然毫无希望,不过,你是否注意到有哪位中国人在化学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重大的成果呢?
IG:没有,我的意思是,我个人一般不大留意这类论文作者的国籍,除非从姓名上可以看出是瑞典人。
笔者:恐怕你也记得,曾经有个中国人李远哲在1986年分享了化学奖,只不过他当时是美国籍,是在美国取得那项获奖成果的。
IG:我的个人看法是,在目前这个阶段,那些规模较大、基础较雄厚、装备较先进的研究机构,相对较容易产生较多较高水平的成果。你知道,现在的科学研究主要得靠多学科合作,那种只靠单枪匹马就可以获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了。
笔者:中国的科研,尤其是国家重视的尖端项目,一向是集中大量高水平的人力和设备集体协作攻关的。据说,中国在60年代的一项人工合成蛋白的成果,几乎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但由于中国方面不能或不愿提供有关谁是最有贡献的个人的资料,因此失去了机会。
IG:对,如果不能从中鉴别出至多3名起关键作用的人,无论是多么重大的发现或发明,都与诺贝尔奖无缘。
笔者:化学奖也有这类先例吗?你可以具体说明吗?
IG:很抱歉,我不能说。
笔者:你的意思是,你不否认有过这样的先例,但不能具体说明,对吗?
IG:对!正是这样,我不能具体说明。笔者:那么50年以前呢?
IG: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这种合作,所以不会出现这种难题。
笔者:那么你们根据什么来鉴别关键人物呢?
IG:我们当然有一些自己的标准,但不对外说明。
笔者:比如,有关某个重大发现的关键论文有5名作者,每个人可能被都认为是关键人物,你们怎么鉴别呢?是否可以肯定,论文署名的第一作者至少是关键人物之一呢?
IG:不能这么肯定,排名次序并不那么重要,第一作者也可能被排除在关键人物之外。
笔者:有些工作是多年以前完成的,除了论文或许就没有其他记录或证据了,那又该怎么办呢?
IG:如果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帮助鉴别,这篇论文也只好不予考虑了。
笔者:你们的评选最后得通过表决,是吗?
IG:是这样,不过整个评选过程分为3个级别,负责化学奖的诺贝尔委员会由7个评委组成,负责筛选候选人,研究、鉴别和比较他们的资料,最后写出推荐报告;报告先交皇家科学院化学组的院士会议审查和表决,然后再提交科学院的院士大会审查和表决,通过后即对外公布。
笔者:诺贝尔委员会在推荐报告中一般提出几组候选人供挑选呢?
IG:不,推荐报告在比较几组候选人的基础上只推荐一组。
笔者:如果推荐被否决了,就驳回重新推荐吗?
IG:不是这么简单,化学组的表决可能出现3种结果,比如报告推荐的是甲,那么就会有化学组改为推荐乙,一是化学组支持推荐甲,二是化学组改为推荐乙,三是化学组既不支持推荐甲也不支持推荐其他候选人。在后两种情况下,化学组都得将它与诺贝尔委员会的分歧提交科学院院士大会裁决,大会的决定为最后决定。
笔者:如果大会否决了所有推荐,那才需要诺贝尔委员会重新推荐,是吗?
IG:不,没有时间了。因为当天必须公布结果,所以当年的化学奖只好空缺。你看这张名单,1916年和1917年的化学奖都“保留”了,也就是空缺了,那还可以假定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1926年的保留,肯定就另有原因了。更有意思的是,1927年不但选出了当年的得奖人,而且也补选了1926年的得奖人。你看,这样的例子后来还有几次。
笔者:这就是说,一定有这样的例子,诺贝尔委员会当年的推荐人被大会否决了,于是只好改推别的人,在第二年才被补选通过。在短短一年之内,多数人对同一项成果的评价恐怕很难会发生什么变化。英格玛,是这样吗?
IG:这样推理没错,不过这只是你自己的推测。很遗憾,我还是不能证实。

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瑞典诗人、比较文学学者)
特邀 王宁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因为诺贝尔当年遗嘱中的原则比较宽泛,评委们曾有过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开头的一二十年内,在评选过程中往往谨慎有余,大胆不足,致使一些该得奖的优秀作家受到忽略,比如托尔斯泰、易卜生、卡夫卡、乔伊斯等。为此委员会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压力。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弥补时已为时过晚,因为奖金不授给故去的作家。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委员会评奖的原则和标准也相应作了调整。埃斯普马克认为,有的作家之所以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写出了不朽的佳作,而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各种活动,奖金不能授给他们。与其相反的是,有的作家并没什么名气,但写出的作品有凝重的历史感和思想深度。诺贝尔奖应该帮助这样的作家成名。这样的作家比如福克纳和艾略特,福克纳获奖在当时几乎鲜为人知,现在已被公认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当问及当今中国作家中谁最有希望获奖时,埃斯普马克笑而不答。他认为近几年来中国文学创作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人获奖,可以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于某些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埃斯普马克表示理解,但随之问道,“难道我们的作家就是为了某种文学奖而写作的吗?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为什么非要瞄准某个奖项去写作呢?再说,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衡量一个作家优劣的唯一标准。”
贝瑞·布隆贝克教授(前诺贝尔医学奖评委)
特邀 [瑞典]陈迈平
“如果不是因为制度的问题,中国至少已经拿到一个诺贝尔医学奖了。”
说这番话的贝瑞·布隆贝克(Birger Blomb■ck),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Karolinska)医学院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授。贝瑞的医学院是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医学奖评选单位,评选委员会只有5个常任委员,另外每年聘请10名教授参加评选工作。他本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数次出任过评选委员。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61年,”贝瑞说,“因为那时我还在澳大利亚工作。有一天一个同事突然跑来说:他们搞出来了!他们搞出来了!他看上去一副沮丧的样子。一开始我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是中国人搞出了人工合成蛋白,而我这个同事自己也搞了好多年,还没有成功。中国人先搞出来,他当然很不高兴。现在来看这个成就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是个重大突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以后中国人还搞出了人工胰岛素。听说就是同一些人,是上海医学院的。
“早在70年代,就有人提名他们得诺贝尔医学奖。这当然是够资格的,我们很多评委也愿意把奖给他们。但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得奖名单是一个小组,有14个人,这是不符合我们诺贝尔医学奖的评选规定的。和平奖可以给一个组织,但其他奖不行,应该给作出主要贡献的一二个人。而据我们的调查,真正主持研究的是一个牛教授,他的排名反而在后面。我们当时和中国方面交涉,但他们说中国讲集体主义,不能突出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个人就没有奖。提名有过好几次,到80年代初我们评委还讨论过,都因为这个问题而卡住了。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位牛教授是不是还活着。我想他可能已经去世了。”
贝瑞显出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这也可能是一个文化的误会。也许,按今天一些反西方霸权的人看来,应该更改的是诺贝尔奖的评选制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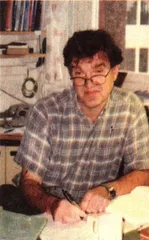
斯坦·格利尔纳(Sten Grillner)(诺贝尔医学奖评委会主席、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神经医学系主任)
特邀 [瑞典]陈迈平
格利尔纳表示:评委会对中国医学目前尚缺乏全面了解,令人高兴的是,这种欠缺近年已随中国的开放正逐步改善。就目前来看,收到的来自中国的提名还不令人满意。格利尔纳介绍,有中国人来信提出,应该给中国的针灸术发奖,格利尔纳说,针灸术现在已被世界广泛接受,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这毫无疑问,但诺贝尔奖表彰的是个人近年来在医学方面的新的重大发现,不是给什么传统医学的。
格利尔纳说,医学奖的错误和疏漏比较少。对于1993年周芷女士没有获奖一事,格利尔纳不予置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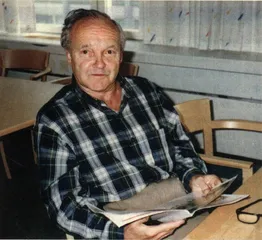
本特·纳格勒(Bengt Nagel)(诺贝尔物理奖评委会年底即将接任主席的皇家工学院理论物理系主任)
特邀 [瑞典]陈迈平
纳格勒认为,中国的物理学研究水平并不低,在有些领域如超导材料方面还有世界先进水平。从历史看,中国人没有得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评委会没有接到提名,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科学界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开放以后已经有了改变,近几年已有中国人被提名,评委会每年也要请中国一些有资格的人为中国物理学家提名。过去中国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大都没有用英文发表,而评委会没有人懂中文,这也造成一种客观困难。
至于每年的颁奖公正不公正,纳格勒说,这要看奖本身发得对不对,而不是看哪个国家多得,哪个国家少得。因为诺贝尔奖发给个人,不论国籍,本来不是给国家和民族的荣誉。就物理奖而言,错误的决定目前还没有发现,疏漏也不多。现在有一些学术论文是很多人署名的,有时有五六个人甚至更多,而诺贝尔物理奖规定不得超过3人,那就不得不排除那些比较次要的人,这是有点无情,但也没有办法。评委会只能尽量考虑作出主要贡献的人。有的人虽然只是研究生也被评上了。比如1993年得奖的卢索尔和今年得奖的利希曼,他们发表得奖论文时都还是研究生。这说明年轻人也是很有希望的。
纳格勒说,经常出现的令人遗憾的情况是晚发,比如爱因斯坦的得奖论文1905年前就发表了,但发奖是到1921年,而那时还是因为他的光电效应理论,而不是后来公认的相对论。有很多科学家的成果等了十几年才被承认。
谈及诺贝尔奖的意义,纳格勒笑着说,诺贝尔奖作为一种荣誉,对个人大概很重要,比如他听说美国加州大学校园内停车位非常难找,但得了诺贝尔奖的教授就有专用车位,所以得奖就特别有意义。得奖有象征性,会使得奖者的理论因此引起世界的注意,得到传播和推广,这是一种好的影响。不过,要说推动物理学的发展,恐怕言过其实。因为,物理学家并不是因为有了奖才出研究成果,没有这个奖,研究还是要作,物理学也是照样要发展的。倒是因为有了研究成果,发奖才有了意义。纳格勒认为,诺贝尔奖的意义和作用现在显然是被夸大了。

贝提尔·奈斯伦(Bertil N■slund)(诺贝尔经济奖评委会主席、斯德哥尔摩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特邀 [瑞典]陈迈平
奈斯伦刚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讲学回来,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印象深刻。奈斯伦表示,他对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并不熟悉,无法评价。奈斯伦说,经济奖历史较短,到目前为止,不但没有中国人获奖,甚至没有得到提名。当问及经济奖评选的标准,会不会因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背景而被排除时,奈斯伦说,从原则上说,他们不会受意识形态的干扰,所以前苏联的经济学家也得过奖。关键是要有杰出而且有实践意义的经济理论,能对今天的世界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最好是用英文发表,不然评委们不懂。
注: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主席、奥斯陆大学“技术和人类价值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塞耶斯泰德(Frances Sejersted)远在挪威,只能通过电话采访,但他总是不在办公室,因编辑部特定发稿日期不能再拖,采访也只好作罢。让我好奇的是,不知他是怎样把和平奖和技术联系起来的。 作家诺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