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时代:儿童何处栖身?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刘怀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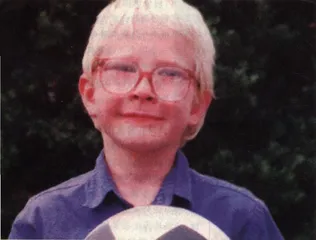
儿童怎么玩起成人的游戏来了?
儿童也骚扰?
站在新闻摄像机前的小乔纳森戴着副遮了半张脸的近视眼镜,怀里还抱了个大皮球,挺神气地挤出“今天我上镜”般的笑来,一副人见人爱的娃娃相。今年9月,小乔纳森吻了同班的一个女孩,大概人家不愿意,就告诉了老师,结果小乔纳森被校方暂时开除学籍,而且(也是对小乔纳森打击最大的)禁止他参加一个他渴望已久的冰淇淋联欢会。在给小乔纳森家长的通知中,校方明确了小乔纳森问题的性质:性骚扰。
“性骚扰”一词用在一个乳臭未干的顽童身上可能是过于小题大作了,但校方也绝非是要哗众取宠,他们坚持说他们是在照章办事——教导学生不去作非他人情愿的身体触碰,否则——按时下已达成的最时髦也是最广泛的共识来说——就构成了骚扰行为。
细究起来,“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一词是从1991年开始时髦起来的。那一年,被提名为美国联邦大法官的托马斯被他昔日的同僚、现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妮塔·希尔指控为性骚扰,此事虽未影响托马斯的仕途,但现代社会中的性骚扰现象愈渐得到关注,并最终使人们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如果一个有权力的人对其下属表达与性有关的意向,且这种意向令对方反感和感到打扰,那么这就构成了性骚扰。性骚扰的特征是行为的持续性(纠缠)和不受欢迎性,其具体形式既可能是举止(如用性感的方式触碰某人),也可能是言谈(如用语言向另一个人表达性意向)。近几年来,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现象被曝光的不少,从这点上说,传媒着实卖了不小的力气,比如至今仍让克林顿总统头痛的那些花边消息,又比如喧闹一时的歌王麦克·杰克逊的儿童性骚扰案。但曝光的结果却往往仅止于大众传媒口淫式的自我抚慰和大众“搔痒性”的一时之快,现实生活则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如果不是更糟了的话)。被杰克逊骚扰了的那名小男孩,因为家长同意接受杰克逊一笔巨款而“私了”了,让人难免觉得这孩子被成人社会和大众传媒白白地耍弄了一番,在整个事件中根本没有他的位置。
小乔纳森的情形又怎样呢?儿童也开始在性骚扰行为中唱主角了吗?恐怕事情还没这么简单(复杂?),把一个6岁小孩想象成性骚扰者无论如何会让我们忍俊不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问小乔纳森:“你知道什么是性骚扰吗?”小乔纳森懵懵懂懂地答道:“不知道”。
以他6岁的心智去理解那么复杂(而且是愈渐复杂)的成人社会的规则,不仅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残酷的,儿童本来就该有儿童社会的一套游戏和相应的规则,根本就是另一码事。但问题就来了:儿童怎么玩起成人的游戏来了?
用小乔纳森的例子来讨论这个问题或许不够典型(他吻了小伙伴的道理尚且可以是“我喜欢她”,是一种亲近的方式,不一定非要被理解为摹仿成人的性游戏),但“性骚扰儿童”的确是史无前例地在社会上出现着,已不仅是我们“拿它太当回事儿了”。举《纽约时报》今年10月3日披露的另一个性骚扰儿童事件:7岁的迪林因吻了邻座的女同学,并扯掉了她裙子上的扣子,而被学校给予停学5天的处理。
目前人们争议最大的是对所谓“性骚扰儿童”的处理方式,即大人对此的反应是否过激了,对孩子施行成人式处罚是否是在扼杀童真(这好像不该成为问题)。《新闻周刊》(1996.10.21)则在“观点”(Opinion)栏目中更进一步,将小乔纳森放到今天美国生活的大框架里,感叹“我们已步入了反直觉的(counterintuitive)、无血性的——更不必说是不着边际的——规则制定(rulemaking)的文化中”。这不能摸那不能碰的,以致人们完全不是根据个人的辨别和判断,而是机械地根据方便的人为规则行事,生活情趣丧失殆尽不说,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是断然不能“跟着感觉走”了。
关于“规则制定”的话题的确发人深思(比如美国最近一本为现代女性提供生活规则的书《规则》The Rules正红得不得了,并应景般地出了不少热衷于做“规则女子”[Rules Girls]的人们,跟她们交往你得懂她们的规则,否则就玩不转),但我们能不能先把大人的事放一放,想一想孩子们的位置:他们何以会卷到这些规则里来了?可不可以给他们一方净土,让他们玩他们的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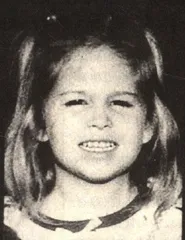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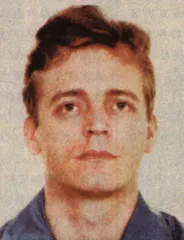
14年前虐待儿童夺走人命的凶手(右)14年后暴死狱中,杀手便是大众传媒
传媒是不是杀手?
有一点似乎是没有争议的,现在的孩子步入成年社会的年龄正在逐渐减低。如果这是指智力开发或素质的养成方面倒也罢了,但往往是令人担忧的另一些方面,比如性的早熟,比如对成人式暴力的热衷(与性骚扰儿童相比,暴力儿童更是出现频仍,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关于暴力儿童问题,美国一位著名人士曾给出过“培养暴力儿童的可靠公式”,即成人现身说法的暴力举动+影视宣传对暴力不断的演示(“……如果以上全不能达到目的,你就把他按在电视机旁,让他看各种有关暴力的电视节目”)。以此类推,关于性骚扰儿童的养成,只须将以上公式中的暴力改换成性的内容就一目了然了。这个公式可以帮助理解本文提出的性骚扰儿童“史无前例”说:这个“史”是以音像为主的大众传媒的出现为标志的。这绝不是说过去历史上就不可能出现过性骚扰儿童,但如此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社会现象,却是在大众文化通过传媒手段的科技化而成为地道的视觉文化之后。
大众传媒时代的来临当然不至于便是洪水猛兽,视觉文化的兴起自然在打破高雅文化的单一性方面功不可没,但视觉文化取代文字的过程很难被理解成人类认知能力的飞跃,尽管在它出现伊始我们曾为之欢呼雀跃过。1954年12月24日的维也纳《新闻》曾经把大众传媒时代描述为家庭和私人生活的复兴的机会:“法国的家庭发现,电视是一项特殊的工具,它使年轻人放弃费用昂贵的消遣,使孩子们束缚在家里……为家庭的集合提供了新的吸引力。”但话说得早了些,紧接着人们就看到,这种新兴的群众性文化消费手段实际上所包含的机会正在完全地瓦解家庭,虽然采取的正是家庭团聚的外貌。因为在家里由电视所统治的,是传送来的外部世界,它使共同生活的现实成为无效的幻象。西方社会学家贡特尔·安德尔斯在他的《人的老朽性》中曾指出:“如果远的事物靠近了,那么近的事物就离去或者消失了。如果幻象成为现实的,那么现实的东西就能为幻象似的。此时,真实的家降格成了容器,它的职能在包含外部世界的图像屏幕中耗尽了。”关于大众传媒时代的这幅图景,西人齐格里德·克鲁塞在一首名为《和谐》的诗里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他们四个人坐在/电视机前/每天平均四五个小时/他们不注视自己/但是他们的手不断地/触碰/在一只盛有坚果的盘里。
大众传媒借助影视音像等科技手段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种“透明的生活”(丹尼尔·贝尔语),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社会壁垒随之被打破,电视机前人人平等,儿童通过直观的传媒手段闯入成人的生活,闯入他们的卧室。
据调查,在美国家庭里,父母与子女每周真正用来交谈的时间只剩下39分钟,而子女看电视的时间则高达1680分钟。且不必说从传播学上讲,长期接受电视文化,其平俗和被动接受性及画面的直观演示会导致受众审美水平的下降,无助于发挥想象力和深层思考,单是想一想孩子们究竟能从电视屏幕上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就足以让人忧心忡忡了。美国畅销杂志《四海》1994的新年特稿为“关掉电视”,文中提到:
“假如你的孩子自小就是个电视迷,那么当他长到15岁时,总共会从电视屏幕上看到5万起凶杀案,3万起抢劫案,1万起强奸案,还有无穷无尽的床上镜头。而这些是他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体验不到的。可以说,电视节目是他获取犯罪信息的唯一来源。
“假如你的孩子是个电视迷,那么他很少有机会成为一名科学家、艺术家或网球明星,因为所有那类高度发展智能、体能和想象力的技能,都需要自小投注极大的注意力,但他付不起,因为他早已把所有的时间预约给电视机了。”
为此,美国教师联盟、未来图书馆学会及“无电视的美国”等团体在1995年初发出号召,要求人们在4月24日至31日这个星期里关掉电视,用省下的时间从事其他有益的活动。
中国的电视病状况尚缺乏比较精确的量化调查,但我们显而易见正在向西方看齐。据零点调查公司今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和日本分别以32.3%和22.6%的高分被北京家长认定为儿童娱乐消费最理想的国家。
如果理论仍嫌晦涩的话,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刚刚发生的案例,来说明媒体可以扮演的杀手角色。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一家广播电台在9月底的一次“午夜谈天”节目里,主持人声泪俱下、绘声绘色地讲述了14年前的一宗儿童性骚扰案:一个名叫娥素拉的5岁小女孩如何被她单身母亲的男友麦克窦格虐待、在饿了一周之后被毒打致死的事。在小娥素拉14周年忌日的当晚播出这个节目,当然有呼唤人们对儿童性虐待的警醒意识的一层考虑,但按理说更近前的案子有的是,主持人选择小娥素拉案实是有感而发的:像麦克窦格这样一个禽兽不如的家伙,居然还在某某监狱里活得好好的,并且由于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对一些法律条文的修改,麦氏极有可能要被减刑释放,连警方也奈何不得。
在这个“午夜谈天”节目结束时,主持人提议收音机前的听众们一起为小娥素拉静默一会儿,“这种广播节目往往有强大的震撼力”,主持人事后回忆说。
这种震撼力开始转化成了行动。很快,麦克窦格所在监狱的不少犯人得到外界口信,有人悬赏1000美元要麦克窦格的命。狱方对此有所警觉,并对麦克窦格作了5天的特别看管,但在解除特别看管的当夜,他被另一名囚犯用铁棍暴打致死。其时距他被减刑出狱只差数天。
这个故事中所包含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善恶因素可能会让我们浮想联翩,但它传达的一个最清晰的信息是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参与和操纵的程度:它可以充分调动起受众的直观感觉,让他们对它的导向作快餐式的、不假思索的接受。
儿童的失乐园?
在这样的一种时代氛围里,儿童除了一生下来就赶快长大以外似乎别无出路。只可惜,无论传媒怎么鼓噪,哪怕电视上的营养液和八宝粥直催得孩子们长胡子来月经,孩子仍然是孩子。何况,成年人是毫无权利去剥夺后人的生命中极其宝贵的伊甸园时代的。
两年前,笔者在美国洛杉矶时,曾在当地的一台脱口秀节目里,看到几个黄口啵儿由大人陪着,奶声奶气地为他们交异性朋友(指带有明确性取向)的行为辩护,要和大人讲人权,讲平等,讲……那场面真让人揪心,真想问一声:能不能让孩子们谈点别的?罗素曾经分析过,人类的行为中,作为本能的现象只有婴儿吮吸乳头这一个动作,其他都是在后来的日常生活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包括性行为。生活在上个世纪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在回忆他的孩提时代时曾讲到,在他十二三岁时,有个年龄稍长的男孩向他解释了性别之间的事,那种“如同讲述物质性生命的任何其他事实”的客观口吻令少年叶芝“难受了好几天”,因为这些事不是他那个年龄的心智所能适应的。
这让人难免要感慨于时代的变迁。在洛杉矶的一条街上,在和两个十二三岁模样的女孩擦肩而过时,笔者听到两人之间的这么一句问话:“So,did you sleep with him(那么,你和他睡觉了吗)?”语气的那种不经意几乎难以让人对她们的话题感到突兀,但那稚气未泯的童音的确在提醒着她们年龄的尴尬。
今年初,笔者曾因出差与同事一起落脚在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家中。这家中有个和小乔纳森差不多大小的男孩,也是一副乖巧灵气的模样(把这两个地域远隔万里之遥的小孩放在一起,大概不致牵扯到那么多文化的不可比性争议里去,因为他们饮食结构、穿戴样式、玩的内容越来越趋同。虽然他们在学校受的教育还不尽相似,但这部分在下面的讨论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总之,这也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家伙,但我的那位同事却不大喜欢他,因为这个小家伙对远房叔叔爱搭不理,却总围着我这不沾亲也不带故的阿姨团团转。这小家伙刻意地做了许多幼稚的举动来引起我的注意,以致我成了唯一能把他从游戏机前带走的人。最后发展到他执意要跟我到洗手间里去,包括我洗澡的时候。在遭到婉拒之后,他反过来向我发出盛情邀请:“我洗澡的时候你可以进来”。这个时候,我们还仍然可以按前述《新闻周刊》评论中的思路来欣赏这小家伙的直觉、血性和非规则制定式的行为方式,相信这里边有人性和童真中浑然率性的一面。但接下来的事就不好解释了:在我们告别启程时,这小家伙对我表达了一种成人式的眷恋不舍。在痛哭流涕了一番之后,他终于相信是“别人”非要把我们“拆开”:“我该怎么办啊!”他拉着我的衣角:“有名片吗,你记着我,我以后会去看你。”虽然说着一口大人话,但他的情绪显然还很矫情,以致我和他的家长都一时尴尬起来。“怎么和昨晚那电视剧结尾一模一样”,我的同伴鄙夷地嘟囔道。但是,这是孩子的不是吗?他们玩什么?谁跟他们玩?
西方的一位社会学家尼尔·波斯特曼在谈到“童心的泯灭”时回忆了他13岁时的经历:“那时亨利·米勒写了一本书,名叫《北回归线》。有人向我保证,这是一本每个想了解性行为知识的人的必读书。但是为了读到这本书,我要克服的困难是很多的。第一很难找到,第二要花钱,而且还必须读它。即使读了,其中许多内容我仍然不能理解,甚至以前的一位读者划了线要引起我注意的章节也要求我的想象,而我以自己的经验是难以经常办到的。”在谈到电视这一不受实际经验的、经济或感知想象诸种限制的“自由入门的工业技术”时,波斯特曼说:
“我们的孩子比过去任何时代的孩子都消息灵通。这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孩子变成了大人,或者至少近似大人。这意味着,由于人们使孩子们得到成人知识的果实,而把他们逐出了儿童的乐园。”
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
以影视音像等视觉手段为特征的大众传播方式的出现,的确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影响。从影响儿童成长的方面来说,我认为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这种形式,起了相当消极的作用。西方已经有不少教育学家在这个领域作过广泛的调查实证。比如有这么一个实验:在教室里装上电视监视器,电视里面播放教室现场的实况场景,然后让人冲进教室作模拟性暴力冲袭。结果表明,学生们的注意力全都在电视图像上,而对现场发生的情形视而不见。这个例子不仅说明电视图像对人的视觉影响的巨大,还说明电视幻像的模拟现实往往给人极强的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以致真实的一切在它面前反倒恍若幻像了。不必说,成人对电视的接受程度还可以有理性的选择,可儿童在电视视觉冲击这方面的承受力是有限的,更是无法作出成熟的判断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电视节目专门为孩子安排的极少,而孩子对电视的接受机会往往要多于成人。可以说,电视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弊大于利,因为孩子极少有机会通过电视这种娱乐手段学习到对他们的成长发育切实有益的知识,甚至反过来,电视的耳濡目染使孩子丧失了与真实世界接触的愿望、勇气和能力。而中国的电视文化体制还不够成熟,基本上还处于对大众口味一味的抚慰和迎合的阶段,谈不上什么批判精神,所以这方面更值得我们警醒,值得提醒家长们注意的是,孩子在电视机前逗留的时间往往与孩子的智力发展成反比。
何绍伟(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策划):
我认为所谓“性骚扰儿童”的出现很难归结为大众传媒发展的罪过。首先的问题是我们该不该用成人社会的一套逻辑来解释和看待儿童的行为。我们知道,儿童世界里带有性色彩的游戏在社会的各个阶段都在民间广泛存在,我们大概还记得小时我们过家家,“姥姥家唱大戏”的情形,尤其在农村,指腹为婚、从小就知道谁是谁的“媳妇儿”的事儿现在还有,大人往往拿这些逗孩子们,孩子们也会好奇、想象,但毕竟由于生理年龄和社会知识的限制,这些往往于他们安享儿童生活并无妨碍。儿童生活基本上是两小无猜式的。
至于说现在儿童性早熟、甚至所谓“骚扰”现象普遍了,这主要也不是传媒的问题,它折射的是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变化。现在社会风气愈渐开放,成人的生活方式也愈渐自由和多元,孩子对成人世界的观察和摹仿不一定通过电视,比如街上或公园里恋人们相拥相恋的亲昵样子,孩子大概不会看不到,这和保守年代或社会的情形是不同的。至于说电视对儿童的影响是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总的来说,其影响的积极一面是勿庸质疑的,电视开拓了人的视野,它的传播广泛和生动形象的特征都使它成了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了解外界社会的窗口。前面已经提到,电视折射了社会生活的变化,是社会生活的形态决定了电视传播的内容,因此说,给孩子生活带来影响的首先是社会本身的变化。 大众传媒